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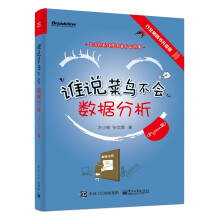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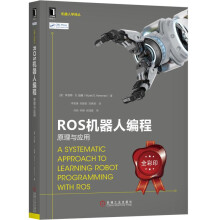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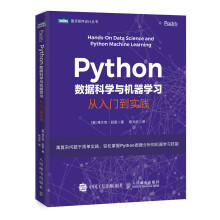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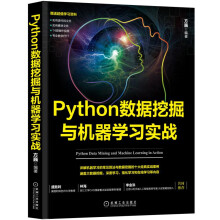


人类文明的灿烂符号
从社会、自然、文化多维度解读陶瓷起源和发展
探究陶瓷古今背后的贸易、经济、艺术史
★视角独特,内容丰富
以日本陶瓷学者的微观视角出发,顺着流光溢彩的陶瓷之路,梳理了陶瓷走向世界的发展历程。有知识的硬货,也有生活的感悟。三杉隆敏通过对中国古代陶瓷销行路线的研究,于1967年首次在著作中使用“海上丝绸之路”一词,这也为之后的文化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题材新颖,故事性强
汇集各类独具风韵的古代陶瓷珍品,关于其缘起与发展的历程妙趣横生,它们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还有一定的文化象征意义。例如,在沙漠中可以保持饮用水清凉爽口的伊朗素烧陶器,由官窑烧制的、供皇家使用的御用瓷,阿拉伯人向中国陶工定制的青花瓷,东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之一的多彩瓷,由中国传入、后在日本发扬光大的天目瓷,等等。
★一部由点、线、面交织而成的陶瓷文化史
作者以实地考察世界上的多个窑址和博物馆为经,以搜寻各地散落的陶瓷碎片和研究各国出土的中国陶瓷为纬,介绍了中国瓷器的销行路线、风格特征、工艺烧造,以及对其他国家陶瓷工艺产生的影响,等等。这些零散的陶瓷细节被联结在了一起,不仅展现了“陶瓷之路”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纽带功能,还呈现了其在全球贸易史、外交史等方面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人们掌握了生火的技能之后,偶然间发现在优质黏土上烧火,黏土会变得坚硬,这就是陶瓷的起源。当火与土相遇,陶瓷艺术就产生了。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陶器开始,人类的窑烧技术在不断失败中进步,也随着人类的足迹不断传播。
在中国,陶瓷的产生已有三千年的历史,经历了由陶到瓷,再到陶瓷并驾的发展历程,其间诞生了青瓷、白瓷、秘色瓷、三彩瓷、五彩瓷、青花瓷等独特的种类。而在西域的伊朗、土耳其、阿富汗等地,也发展出具有异域特色的陶瓷工艺,并风靡一时。通过陆上与海上的贸易通道,中国的瓷器吸收了西域的特质,西方人也为中国陶瓷之美所折服,从此陶瓷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千年来,散落在优选各地港口、海岸的瓷片,连接成有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以景德镇为中心的中国陶瓷,是将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的里程碑。
跨越雨季的“土漠”
从德黑兰往东,穿过沙漠就可以到达马什哈德,然而两地间的路况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我们乘坐的“路虎”牌越野车一路颠簸行进,突然嘎吱一声,车轮陷进了烂泥坑。司机猛踩油门,轮胎顿时呼啸着飞溅泥浆, 车子不但没有前进,反而渐渐失去平衡,开始下沉。司机慌忙熄火,并招呼我们下去帮忙抬车,可是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四下搜寻,想找一些木头或者石头之类的东西来卡住车轮,但却一无所获。这里是一片棕红色的丘陵地带,荒无人烟,远处倒是有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可是太远了,光是走到那儿就得用半天时间。此时正值雨季,整个大自然似乎都变柔软了,当下我们一车人正与它展开一场力量上的较量。
我们先卸下行李,尽量减轻车子的重量,使其稳定下来,然后所有人一边喊着“一二三”的口号,一边推车,同时司机轻踩油门,慢慢启动车子。这是我们从早上开始陷了三次烂泥坑之后总结出的经验。推车的时候,灰色的泥浆溅到了我的衣服上,并开始慢慢渗透,我用手一摸,指纹便清晰地印在了上面。那一刻,我思考的竟然不是车子的事,而是这土的黏性真不错,可以用来制作陶瓷。
这条路现在叫“亚洲高速公路”(Asian Highway),听上去很气派,可是30年前的伊朗哪有那么多水泥路,全是烂泥路。过去,我在伊朗乘坐巴士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陷进泥坑的糟心事。当时司 机试着重新发动车子,但失败了,无奈之下只好让乘客先下车。乘客们自由分工,一些人拉绳子,一些人推车,还有一些人指挥,司机配合着大家喊的“一二三”的口号踩油门。庞大的巴士从泥沼的怀抱里艰难挣脱,之后大家陆续回到车上坐好。对他们来说,巴士陷进泥坑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推车时,有件事让我既感动又羞愧,当时他们向我摆手,说我是外国人,不能被泥浆弄脏了衣服,就不用帮忙推了。于是,我就傻站在一旁看他们推车。
化用一下“沙漠”这个词,这里可以说是伊朗的“土漠”了。
清真寺的墙壁与察伊哈纳的水壶
沿着棕红色的沙漠一路前行,地平线的另一端突然显现出一抹绿色,我以为那是绿洲,心中大喜,走近后才发现是一座清真寺的绿色穹顶。清真寺的穹顶有绿色的、金黄色的,上面还矗立着一座细长的宣礼塔。虽然它不是真正的绿洲,却如绿洲般等待着旅人的来访。
尽管当时我坐在车里,但看到清真寺的瞬间还是感觉一阵心安。以前的人出门远行,要么骑骆驼或马,要么步行,如果能在一片荒漠中看到一座清真寺,那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事啊。夜幕降临,宣礼塔上发出点点光亮,恰似沙漠中的灯塔。此外,清真寺的墙壁非常厚,即便沙漠酷热难耐,里面依然清凉宜人。
靠日晒制成的砖头称不上陶瓷,但用火烧制的砖头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到伊朗后才知道,原来宏伟的清真寺是用瓷砖(烧制的砖头)堆砌起来的。每块砖都被涂上了艳丽的釉药,将它们垒在一起,棕红色的沙漠中就出现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建筑。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马赛克镶嵌砖和瓷砖都是陶瓷。
我原以为陶瓷无非是些锅碗瓢盆,但当我站在伊朗人用烧制的马赛克镶嵌砖和瓷砖砌成的阿拉伯式花纹墙前时,立刻被它的那股魄力震慑到了。多数阿拉伯建筑的穹顶和墙壁的凹陷处都刻有唐草纹或几何纹,当这些花纹出现在清真寺时,便立刻营造出一种意想不到的美。这和我在照片或者书刊上看到那种在晴空下闪闪发光的清真寺时的感觉完全不同,是一种直击心灵的感觉。原来这就是陶瓷的世界啊。
沙漠沿途零零星星地分布着一些泉眼。人们利用一种叫“Qanāt”的地下水道从几十公里外的山上引水至沙漠中央的人群聚居地。这里有一处小小的察伊哈纳,在伊朗、印度和苏联,人们常把茶称作“察伊”“哈纳(或哈尼)”则是小馆子的意思。
中午时分,在气温高达50°C的沙漠中行进,就算是开车也很煎熬,但如果能遇到一家察伊哈纳,喝上一杯红茶,顿时便不觉得热了。客人们有时等不及水烧开,大喊道“先给我来杯水”。这时,店家就会拿着素烧壶过来给客人倒水,那水喝起来清凉爽口。
尽管我早就知道在高温干旱的地区,素烧壶里的水分会慢慢渗到陶壶表面,之后表面上的水分快速蒸发,从而带走热量,使得壶里的水能够保持清凉这一原理,但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体验到壶里的水竟如此清凉。
现今世界上仍有不少地方在用素烧陶器盛水,比如开罗郊外的那些八米多高的窑,一次能烧制出几千个素烧壶。但是自从价廉又不会碎的塑料容器问世之后,陶器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被淘汰。随着文明进程的推进,连一些偏远地区都通了电。如今,随着电冰箱的普及和城市供水系统的发展,“原始的”素烧壶不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
然而在伊朗,直到今天,即便是首都德黑兰这样的城市,素烧壶依然在普通人家的厨房里占据一席之地。素烧陶器跨越了人类几千年的历史,20世纪时依然在烧制。这次伊朗之旅更是加深了我对素烧陶器的喜爱之情。
波斯的陶器文物
我在德黑兰最先结交的不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而是古董商,他们多是伊朗籍犹太人。伊朗革命爆发后,他们分别搬到了日本、伦敦、纽约和洛杉矶等地,其中有几个人到现在还跟我保持联络。
一开始,波斯美术的研究由法国的考古学家主导,后来由美国等国的考古学家接手,再后来日本的学者也参与了进来。尽管波斯疆域辽阔、历史悠久,但考古发掘却没有多大进展,出土的文物几乎全是陶器,而且大多是盗墓贼挖出来的。
初春时分,冰雪消融,伊朗难得有一段雨季,平时坚硬的土壤变得柔软易挖,人们趁着农忙还没开始,抓紧时间大捞一笔。因此,天气变暖之际,也是盗墓活动最猖獗之时。
约30年前,我第一次去伊朗,当时盗墓贼在靠近里海的阿姆拉什附近盗走了大量史前陶器,并把它们卖给了德黑兰的古董商。尤其是瘤牛形和鸟喙形的陶壶,因其造型奇特,颇受欢迎。
可是这些陶器具体是在哪儿挖的?没有人知道。盗贼们对此守口如瓶。当然,全世界的盗墓贼都是一副德行,不光在伊朗,在中国和新大陆安第斯山区也都一样,他们会故意误导他人,明明是在东边挖的,却说是在西边。
在德黑兰时,我遇到过某个地方的村长带着一行人卖文物。 当时我正在一个古董商朋友那里做客,那些人从随身携带的陶器中挑出三四件,开始和我这位朋友谈价钱。我虽然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从语气上能判断出一个想高价卖,一个想低价收。朋友的儿子会说英语,他时不时会告诉我双方谈到了什么地步。但从我观察到的情况来看,这不像是一天能谈成的样子。
村长一行人还拜访了其他古董商和买家。他们之间交涉过程的曲折烦琐,不是我们这些急性子的日本人所能忍受的。我甚至还和这位村长在其他古董店偶遇过。
我第一次考察伊朗是在1963年,而日本的古董商把目光投向德黑兰则是几年之后的事了。那时候,土器和陶器的考古发掘在继续中,甚至挖出了和正仓院藏品一样的雕花玻璃。这一时期,我在当地学到了很多知识,过得很开心。
如果没去伊朗的话,我想我不会对除中国之外的陶瓷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土器、陶器和瓷器虽然都属于陶瓷,但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我会在后文中详述。世界陶瓷史上的两座高峰,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波斯。当时,我虽然对中国有着无限憧憬,却没有机会去实地考察,实在可惜。
阿德比尔神庙的藏品
我在研究伊朗的中国瓷器时,接触最多的就是阿德比尔神庙的藏品。
在里海西岸,距离苏联不远处有一座海拔1500米的高原,上面是阿德比尔的古城,16—18世纪波斯的萨非王朝就发源于这里的萨非教团。城内建有祭祀萨非王朝先祖谢赫·萨非·丁的谢赫萨非丁长老陵园和圣殿建筑群。1611年,萨非王朝历史上的明君阿拔斯一世将宫廷珍藏的1162件中国瓷器捐给了这座圣殿。
阿拉伯人将自己使用的贵重物品供奉给清真寺的习俗称为“巴库夫斯”。阿拔斯一世称其为“巴库纳”,意为“高贵而神圣的奴隶阿拔斯供奉萨非圣殿”,他还让人用阿拉伯语将其刻在了墙上,铭文横宽2厘米,纵深1厘米。
阿德比尔过去属于阿塞拜疆,远离“丝绸之路”的主干道,这在后来竟成了件幸运的事。阿拔斯一世捐出的这1162件瓷器在之后的400年间历经沧桑,除去破损和被盗走的部分,截至20世纪末约有900件被保存了下来,真是奇迹。
这些藏品中绝大部分产自中国景德镇,包括元青花瓷37件,部分明初时期的高品质青花瓷,以及少量明末时期的五彩瓷。其中有一部分是阿拔斯一世于16世纪迁都时运到这里的,还有一部分是从中国进口的。
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的藏品数量高达12000多件,其中有不少古代文物,但收藏的历史背景大多不详。与之相比,阿德比尔神庙有1611年这个明确的时间节点,为我们研究陶瓷的编年史提供了便利条件。
当时,阿拔斯一世的臣下、天文学家阿拉尔·艾丁·穆罕默德·穆纳希姆将每件藏品的明细都记录了下来。此外,神庙的管理员穆罕默德·喀什·别库·萨非于1759年3月 24 日记录“藏品共有1018 件”。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于来访者的记录,如1637年的亚当斯·奥利·阿利乌斯,1810年的詹姆斯·贾斯汀·莫里尔,1910年的费雷德里克·萨勒。尤其是费雷德里克,他非常喜欢中国的瓷器。1930年,伦敦举办“大波斯展”时,他在艺术杂志《阿波罗》(Apollo)上发表文章专门介绍了这批中国瓷器,欧美学者这才认识到阿德比尔神庙藏品的重要性。
伊朗政府担心这些藏品放在边境小镇不安全,于是在1935年把805件瓷器转移到了德黑兰的伊朗国家博物馆。美国人约翰·波普对阿德比尔神庙中的藏品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于1956年出版了著作《阿德比尔神庙里的中国瓷器》(Chinese Porcelain from Ardabil Shrine)。
受此启发,我于1967年对当地进行了为期十个月的实地考察,主要的考察地点是伊朗国家博物馆以及伊斯法罕和大不里士地区的一些藏馆。其间,我有幸被获准进入阿德比尔神庙,得以观赏到那些被封存在里面的藏品,包括82件青花瓷、白瓷、黄釉瓷、五彩瓷及收纳用的木箱,尽管当中有不少已经碎裂。当时我拍了照,还认真做了笔记。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阿德比尔神庙内没留下任何东西。由于神庙位于边境小镇,所以像约翰·波普和大英博物馆的巴泽尔·格雷这样的外国人都不允许进入。但是,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却可以进入调研,这在欧美学术界引起了热议。
序章 沙漠之国伊朗
1 陶瓷文化
2 中国的陶瓷
3 青瓷:对玉石的憧憬
4 白瓷:白色的戏剧
5 青花瓷:灵“西”一闪
6 多彩釉:东西交流的结晶
7 曜变天目:回归黑色
8 陶瓷的美学
后记
参考文献
注释
译名对照表
1.既没有文化上的隔膜,又能洞若观火、体察入微。三杉隆敏的这部小书读来新鲜、亲切,给人启发。
——知名瓷人、景德镇长物居主人@涂睿明
推荐「里程碑文库」作品《陶瓷》
2.这是一部陶瓷的全球史,从中国出发,顺着流光溢彩之路梳理了陶瓷走向世界的历程,有知识的硬货,也有生活的感悟,从哪个角度上来说都是应该读的一本书。
——高校历史学教授、百家讲坛讲师@于赓哲
推荐「里程碑文库」作品《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