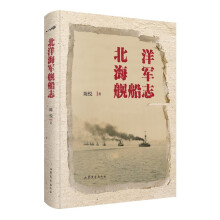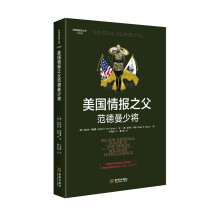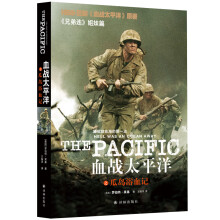第一章 月夜启程
10月,灼热的阳光倾泻在病房的石灰墙上。外面的院子里,茂密的樟树下一片嘈杂,口令声和军号声此起彼伏,踏步扬起的烟尘在原本静滞的空气中打着转儿弥散开来。病房里,消瘦的病人左腿打着石膏,正伸长了脖子去瞧外面的动静。有情况,这是明摆着的,部队有了新动向,但是却没人知会他。一个护士从门前走过,他叫道:“外面怎么了?”
“不晓得,首长。”她答道,一边向外看去。“没人通知我们。”
陈毅嘴里骂了一句,六周前在兴国县他髋部中弹,从前线抬了下来,一直都没痊愈,他的牢骚也就从没停过。骨头碎片老是取不干净,他要求用X光照一下,但是医生总有种种借口:X光机出问题了,没电源,电池的电不够了等等。
陈毅是红军高级指挥员,今年三十三岁,四川人,一向乐天开朗,出了名的风趣幽默,今天却反常地焦躁不安,满腹心事。外面肯定有情况,但具体状况却弄不清楚。他在病床上翻来覆去,为受伤而气闷。几分钟后那个护士又出现了。“有人来看你,首长。”她一边说,一边赶紧把枕头拍平,把床单拉直。在她身后,陈毅见到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周恩来走进了病房。直到后来陈毅还能记得周恩来这次探病的具体日期。1934年10月9日——农历狗年九月初二——那天周恩来告诉了他一个消息,也就是后来的长征。
于都是江西南部一个沉寂的小城,建在于都河两岸,人口还不到一万。这儿向来风平浪静:只有渡船在河上行来驶去,还有个集市。1934年10月,人们在这个地方还是感到安宁的,尽管还有一丝紧张。天气很宜人:白天暖和,夜晚凉爽,几乎不下雨。多数庄稼都已收获,只有晚稻,红薯和部分荞麦还等着收成。整株的黄豆全须全叶地晾在房顶的灰色瓦片上晒着,从房檐上枝枝杈杈地搭拉下来。院墙边立着一排红色的陶土罐儿,里面满满地装着豆酱。墙角堆着青皮红籽的苦瓜,黄澄澄的南瓜,还有一串串晾着的红辣椒。农人们笃定到下一茬庄稼收成之前粮食已经够吃了,但是不安的感觉还是在逼近于都。红军在夏天收了大量的稻米,征兵的数量也远超往常。田里总有干不完的活儿,开耕、插秧、种植、收获,周而复始,永不停歇。今年年景不错,人们好不容易瞅空喘口气,但是情形似乎有些反常。到底为什么却没人弄得清楚。中秋节已经过了,门楣上象征喜气的红纸和面目狰狞的门神像都有些破烂了,但是人们依然希望它们能够把厄运挡在外面。
为了给红军征募新兵,刘英在于都待了几个星期。从事这项工作的还有其他很多年轻妇女。刘英今年二十六岁,小个子,还不到5英尺(约1.52米),身材娇小,像个布娃娃。海伦·斯诺说很难想像刘英在长征时怎么没被大风吹走。后来结婚的时候,刘英的丈夫,党的高级领袖洛甫也用同样的话打趣她。刘英的个子很小,但意志却像精钢一样坚韧,毛泽东也曾把她置于自己的翼护之下。有一天他带着警卫员来共青团办事处,悄悄通知她马上离开于都,到江西南部的中央苏区总部瑞金报到,开始一项非常特殊的工作。
“我说自己走不了。”五十年后她回忆说,“我的工作还没结束,我必须完成任务,征集更多的兵员。”
但是毛泽东很坚决。她必须回去。尽管感到疑惑,可刘英还是回了瑞金。40英里(约64公里)的路她徒步走了两天,但跟马上就要开始的征程相比这不过是一次短途散步罢了。
江西省府南昌,正对湖面的一座雄壮的建筑内,穿着讲究的矮个儿光头正独坐在精美的柚木桌旁。他拿起一份《民国日报》——国民党的地方日报,薄薄的嘴唇上玩味着一丝自得的笑意。他的目光扫过关于铁路桥合同签署的重点报道,以及各种壮阳药、妇科秘方和珠宝的广告大杂烩,最后停留在头条社论上。日期是1934年10月10日——双十节——国民党政权建立纪念日。这条社论关注的是时事,它提醒人们警惕自然灾害,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迫近。共匪利用国内困境活动猖獗。因此民众应该守德尚善,停止饮宴、歌舞,为祖国、为中华存续而奋发图强。所幸的是,江西的状况正在迅速好转。共匪将在年底前被肃清。他们已经被团团包围,军队只能用绳子串在一起来杜绝逃兵。“他们溃灭的日子不远了。”
看报纸的人轻轻舔舐着嘴唇。这些文字都是经他本人审核过的。实际上,这些文字就是他口述的。他就是蒋介石,今年四十八岁,特地来南昌指挥自己的国民党部队肃清“赤匪”。进展一直很顺利。没过两天,蒋介石就命令自己的专机准备起飞去陕西、宁夏和四川短期视察。
红三军团驻扎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北面的石城地区。孔宪权二十三岁,结实、干练,后来干了一辈子革命,向来直言不讳。他是三军团侦察小分队的指挥员。部队两周前打了一场硬仗,结果并不理想,正撤下来休整,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这些都是高度机密。孔宪权的同志们只晓得他们很快就会继续前进。(后来,这样的保密工作因为结果适得其反而备受批评)。身为侦察员,孔宪权知道的远不止此,但是却守口如瓶。跟很多同志一样,孔宪权是贫农出身,有四个兄弟,七个姐妹。家里不同意他加入红军。他的父母还是传统的老观念,认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但孔宪权还是从了军。他渴望拥有土地,而红军承诺分田。
孔宪权参加的第一场战斗中红军全歼了国民党第十八师,活捉了师长——苏区恨之入骨的红脸胖子湖南佬张辉瓒。当时的情景即使五十年后依然历历在目: 在山坡上(镇里地方不够大)开公审大会,张辉瓒被押上来,面前站满了农民,贫苦市民,拿着红缨枪的赤卫队青年和愤怒、疲惫的红军战士。张辉瓒头上扣着高帽,双手反绑,站在台上,人群怒吼着要把他杀头。很快就真的砍了脑袋,放在木筏上,顺着赣江漂下去,以此来警告其他的国民党将领。对往事的回忆让孔宪权很激动,情不自禁地念起了当时的打油诗“真高兴,战龙山,斩了狗官张辉瓒”。
红军在10月里行动神秘,苏区根据地和首府瑞金也日益躁动起来,此中内情,温和、文雅的高个儿青年伍修权差不多一清二楚。这个根据地是五年前由毛泽东及其支持者朱德带领的共产党部队建立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密切,农民把他们称做“朱毛”红军。很多人坚信朱毛实际上是一个人。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共产党将领朱德身材高大、慢条斯理、风格朴实。有一次他就解释说朱毛是分不开的。这个词实际上是个独具匠心的双关语,因为朱的同音字是猪,而毛的意思是毛发。
伍修权无所不知或者说近乎无所不知,因为他是李德的翻译。李德是莫斯科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代表。李德在过去一年里都是中国红军的指挥,却屡战屡败。
伍修权当时二十八岁。十九岁的时候他和上百个中国青年一起去了苏联,在那里待了五、六年,学习语言,了解革命,也学习军事科学,如今已经回国三年了。从李德1933年10月到达苏区,伍修权就开始为他做翻译。
现在伍修权手头有个难题——是烹饪问题,不是军事问题。
来苏区的时候人们为了让李德生活舒适而大费周章。他的住所有三个房间,是特地为他修建的,在离红军总部一英里(约1.6公里)的稻田里,和党中央机关部门距离也不算远。房子独处一处,孤零零的,伍修权和其他人称它作“独立房子”,很快独立房子就成了李德的外号。
伍修权的问题出在那片稻田上。他和李德的工作人员在到处是青蛙的稻田里养了一群鸭子。鸭子已经肥了,伍修权无论如何不愿意白白丢掉。所以每天晚饭都有鸭子吃。伍修权直到老都记得1934年10月10日那天吃的最后一只鸭子,烤得香脆,切成肥嫩的肉片上的饭桌。伍修权总把那一天和红军的出发联系在一起,尽管后来一般认为直到1934年10月16日长征才正式开始。
秋日荏苒,党的干部之间在谈话时也开始不再那么遮遮掩掩。对于知道如何从字里行间揣摩意思的有心人来说,从出版物上也可以见到一些有关未来动向的端倪。1934年9月29日,洛甫(张闻天)在党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里面说到为了保卫苏维埃,粉碎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所有高层都知道行动就在眼前,但还不知道去哪里。有人猜湖南,有人猜江西,有人认为是贵州,还有人认为是云南或四川。除了最高层,没人知道究竟。后来为了躲避蒋介石的战斗轰炸机(当时蒋拥有两三百架),总部搬到了瑞金北部的云石山。山区深处,干部们碰头的时候会心照不宣地打招呼说“快出发了”。有时候他们会问“你走不走?”答案是不同的。有的说“走。”其他说“不晓得。”一般来讲,“不晓得”意味着留下来。实际上,蔡孝乾后来回忆说,“消息传来就像在水里投了一块大石头”,引起了很大的不安。名单逐个确定。有些家属带着大包小包回了老家,跟人说“他去别的地方了”,却不说具体哪里。部分伤员也从医院回到了原来的单位。谁走谁留的消息一时众说纷纭。起先说徐老——毛泽东在长沙师范学院的老师徐特立——因为年纪太大,不适合长途跋涉,要留下来。后来又说他会走,而且已经分到了修养连,特地为他找好了马匹,但是还没有配马夫。但是大家却不知道毛泽东已经看到了留守的名单。上面的名字大多属于和他亲近的人:他的弟弟毛泽覃和弟媳贺怡 (也是毛泽东妻子贺子珍的妹妹)夫妇;毛泽东的朋友、湖南老乡,也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何叔衡;已经解除了职务的共产党前总书记瞿秋白(据说因为肺结核很严重,不适合一起走);军事指挥员陈毅;很早即加入共产党的毛派支持者贺昌;毛泽东的另一个拥护者、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刘伯坚,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人。看起来毛泽东推荐的人一个也没有被接受。甚至他恳求一起带上的瞿秋白也没有能够同行。和毛泽东的密切关系就是留在苏区的保票,而留守的陈丕显将军认为,当时留在苏区的只有一成希望活下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