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桦山又对外务卿福岛种臣、新式陆军创始人山县有朋等数十名朝野要员进行了游说,并多次拜见西乡兄弟。
大约也就在此时,日本当局开始在琉球问题上打擦边球,摸起大清国的底牌来。
就在明治五年,明治天皇亲政,强招琉球派使到东京朝贺。十月四日,琉球王子及三司官来到日本。十六日,当他们谒见日本天皇时,被闪电般告知:琉球已被正式册封为日本藩属,等同本土诸侯。国王尚泰列为华族,并在东京赐府第令其居住。三十日又宣布:琉球事务由外务府管理。
对琉球而言,这无疑是晴天霹雳。而日本更关注清国的反应。在看到清国没有反应后,日本军政高层的胆子更大了。
明治六年(1873年,同治十二年),天皇宣布琉球等同本土府县,事务由内务府管理,并废除国王。结果,大清国还是没反应。日本军政高层激动了。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征台派的微妙变化。美国大使加剧中日冲突
正如柳原前光曾经提到的那样,早在日本使节赴华之初,欧美列强便担心中日会否结成东方同盟,共同对付西洋列强。美国驻东京公使德朗尤其害怕出现一个以中日联盟为核心的远东阵线,进而搞对内互通有无、对外排斥欧美商业集团的封闭市场。所以他在1871年7月6日呈递国务院的文件中主张:“日本与中国有所不同,我们应欢迎日本成为-个盟友。当与中国有冲突时,文明诸国应视日本为一伙伴。”
今天的读者不免会觉得这位德朗先生多少有些神经质,中国怎么可能和日本结盟呢?但在当年,却并非全无可能。首先,在日本方面便存在着呼吁和清国结盟的舆论声音。甚至有人声称:“今日之日本,求唇齿之邦于宇内,舍满清殆无有也。”(会泽泊语)所以当年的美国国务院对德朗的担忧也是深以为然,国务卿费雪在8月24日亲自指示:“应把握所有可能机会,设法诱导日本尽可能地远离中国,而与其他强权势力在商业与社会上结合。”
德朗接到这个通知后,即于11月15日诘问日本外务省,中日条约是否不同于日本和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日本答以并无不同。
待到前述《中日修好条规》出台,其第二条声称:
两国既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此文一经公布,果然成为一大外交话题。说起来,《中美条约》第一款说的就是“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大清国与美利坚可算不上“一衣带水”,更称不上“同文之国”,可不也就这样白纸黑字地写下来了嘛。何以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写了类似的话反而成了一大外交话题呢?问题正出在双方的“一衣带水”与“同文同种”,从而造成了西洋列强的猜忌。而当时的日本军政当局正谋求“脱亚入欧”、“文明开化”,适当地借助清国制衡欧美则可,但如被认为是所谓东方集团的一部分,则大违日本的根本利益导向与价值观认同。
日本政府的底牌德朗大使并不清楚,正因为不清楚,所以才越来越担心中日同盟的出现。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得知了琉球漂流民事件,他更知道日本正在谋求将琉球“内化”,并不断声称琉球在日本的主权范围之内。于是,这位德朗大使敏感地意识到,这次事件或可成为瓦解中日联盟的关键转机!
没想到,机会居然主动送上门来。
原来,在北京谈判的柳原前光通过“京报”看到了闽浙总督上奏清朝的有关琉球漂流民遇害事件的报告,当时便意识到是个机会,乃于1872年5月转报时任日本外务卿的福岛种臣说:“琉球人在清国领土台湾被杀害,为鹿儿岛县参考。”并附送该报为参考资料。但并没有引起外务省的充分注意。7月,柳原与英国上海领事会谈时,对方趁机挑唆,称如果是欧美国家遭遇如此事件,即刻就会派遣军舰前往,追求责任并索取赔偿金。柳原更觉机不可失,乃于8月回国后再次向外务省建言,终于引起日本外务省的高度重视。
受此影响,福岛种臣于9月23日约见德朗,讨论台湾问题。
在这次会晤中,德朗提出了三种策略供福岛参考:
第一,是否要立即派遣问罪之师?如按此案行动,等于将生番杀人劫货等同于海盗船事件。
第二,是否要与土著交涉,以订立今后之管理方式,以保障日本人及琉球人抵达时不再被施暴?如按此案行动,等于将此问题当做一法律问题解决。
第三,若承认生番问题属于国家统治权问题,是否要向清政府交涉要求处置?如按此案行动,等于承认中国对台湾生番的主权。
对于这三个提案,福岛并未表态,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德朗带来的大量关于台湾的图文资料,尤其对于番汉界线的存在极感兴趣,并向德朗试探性地询问:“图中……记号界外是清围管辖之地吗?”德朗答道:“虽然是清围管辖,但其政府指令不行,故无法保护人民。”德朗认为,与其与清国交涉,不如直接和番民交涉。并指出了在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之处。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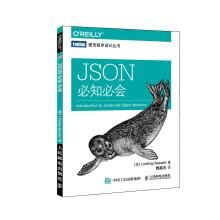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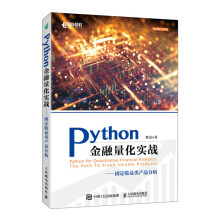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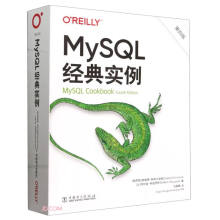
★《李鸿章时代》一书,以世界史的眼光看李鸿章,别有一番滋味,耐读,希望诸君能一阅。
——著名历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
★在近代中国外争国权的斗争史中,李鸿章算是一个非常特殊又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既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又给那个时代留下了深刻的个人印记。而长期以来,国人对他的认识往往迷失在“卖国贼”和“近代第一外交家”的两极之中。事实上,李鸿章和他的时代一样复杂难解。《李鸿章时代》从大战略的高度,重新解析其人其事其时代,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值得开卷一阅。
——国防大学军事专家、空军大校戴旭
★国人好以是非成败论英雄,于颓世中试挽狂澜者,便每每为千夫所指,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这个肇始了中国近代国防、近代教育、近代工业,临去犹忧嘱“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的悲剧英雄,却因甲午之败、辛丑之辱而一度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天下溺而罪一人,这恐怕不只是李鸿章的悲哀。《李鸿章时代》一书,以国际大势为背景,以丰富详实的史料为支撑,重构了李鸿章身处的时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全息的李鸿章。
——《南方都市报》专栏作者、天涯煮酒论史版主 江上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