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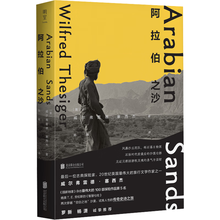

塞巴尔德成名作,中文世界首度引进
柏林文学奖获奖作品
彻底推翻虚构与非虚构之墙
在记忆的深处誊抄苦难
用德语为流散的犹太人谱写安魂曲
抵抗时代对过去的高效率清洗。
所谓移民,即失去礼拜天的灵魂
在大地上寻找更好的人的定义
最后只能以死还乡
本书是塞巴尔德的成名之作,包括四个超长短篇小说:第一篇《亨利·塞尔温大夫》讲述了塞尔温大夫的一生,他从七岁随家离开立陶宛乡村,本想去美国却流落到英国,在晚年一贫如洗;第二篇《保罗·贝雷耶特》讲述了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国民小学教师的一生,因为家族的不幸,他陷入被驱逐者的忧郁和对德国的复杂情感;第三篇《安布罗斯·阿德尔瓦尔特》讲述了移居纽约的舅公带传奇色彩却又悲凉意味十足的一生,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大银行家的管家,但最后住进疗养院,主动接受休克疗法;第四篇《马克斯·费尔贝尔》讲述了画家费尔贝尔的一生,以及费尔贝尔母亲留下的回忆录。这些不同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关于背井离乡的犹太人在原居住地和异国他乡的悲惨遭遇。
亨利·塞尔温大夫
往事岂能如烟
一九七〇年九月底,在我于东英吉利城市诺里奇任职前不久,我同克拉拉一道出城去欣厄姆寻找住所。这条乡村公路穿越旷野,沿灌木丛往前延伸,从枝叶繁茂的橡树下穿过,途经一些星散的居民点,在二十五英里之后,欣厄姆参差不齐的山墙、教堂尖塔和树梢才在平原上依稀可见。大型集市广场被众多寂然无声的房屋门面包围,冷冷清清,但我们并没花多少工夫,就找到了中介机构给我们提供的楼房。这是当地最大几栋楼房当中的一栋,离耸立在绿草如茵、四周环绕有苏格兰五针松和紫杉的公墓的教堂不远,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以一道一人高的围墙和由接骨木同卢西塔尼亚月桂树交错相缠的灌木丛作掩。我们走进大门宽敞的入口,轻松地沿着稍微倾斜的路往下,行经铺着小砾石的楼前广场。在右边,马厩和车库的后面,一棵山毛榉高高挺立,直插明净的秋日蓝天。树上有一些乌鸦窝。现在刚过中午,这些鸟巢孤零零吊在树上,在只是偶尔才会晃动一下的树叶遮盖之下,便成了阴暗的角落。
野葡萄藤爬满这栋正面很宽的古典复兴式楼房的立面墙壁,大门漆成黑色。我们多次拨弄门环——一条黄铜制的弧形鱼,然而屋内没有丝毫动静。我们往后退了一步。那些分成十二格的框格窗户闪闪发亮,恍若由镜子玻璃做成。这可不像是有人居住。这使我想起下夏朗德省的城堡,我曾经从昂古莱姆出发到那里参观过。有两个疯疯癫癫的兄弟,一个是议员,另一个是建筑师,花了几十年工夫来计划和设计,建造起凡尔赛宫的正面。那当然是一道毫无意义的景观,但从远处看却又令人难以忘怀,它的窗户就像现在我们面前这栋楼房的窗户一样,既闪闪发亮,又模模糊糊。如果我们没有匆匆交换一下眼色,相互鼓励,至少要把这座花园观察一遍的话,我们肯定就会一无所获地继续往前走了。我们小心翼翼地围着这栋楼房转。在北边,墙砖已变成绿色,有花斑的常春藤爬满部分围墙。一条长满青苔的道路从仆人入口处和堆放木柴的库房旁经过,穿过一些十分阴暗的地方,最后犹如通向一座舞台一般,通向一个有石制栏杆的大阳台。大阳台下面,是一大片被花坛、灌木丛和绿树环绕的正方形草地。草地对面,放眼西望,景色宜人,是一座公园。公园里有一些挺拔的椴树、榆树和四季常青的橡树。在那后面,便是连绵起伏的耕地,是地平线上白云缭绕的山脉。我们长时间默默地上下观赏这片伸向远方的景色,都以为只有我们待在这儿,直到看见一个一动不动的身影躺在花园西南角一棵挺拔的雪松投在草地的树荫里。是一位老人,他把头靠在弯曲的胳膊上,好像完全沉浸在眼前这片土地的景象中。
我们穿过这片使我们每一步都变得异常轻松愉快的草坪向他走去。然而只是在离他很近时,他才注意到我们,并不无几分尴尬地站起身来。他虽然长得个头儿很大,肩膀很宽,却显得敦实,甚至矮小。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也许是因为他低着头,从金丝老花眼镜上方看人的方式,看来这成了他的习惯,造成了一种屈着身、几乎是祈求的姿势。他把白发往后梳,可是仍有几绺一再落到高高凸起的额头上。我正在数草的叶子。他为自己的心不在焉表示歉意。那是我的一种娱乐。恐怕有些令人不快吧。他把其中一绺白发往后掠,动作笨拙又完美,然后用一种似乎早已不再使用的客套方式,给我们作自我介绍,说他是亨利·塞尔温大夫。我们肯定是为住所而来的。他继续说道。他只能说,住所尚未租出去,但我们不管怎样都得耐心等待,等到塞尔温夫人回来,因为她是这栋房子的主人,而他只不过是这座园林的住户,一种观赏隐士罢了。在这番开场白之后,我们一边交谈,一边沿着把花园同公园空地隔离开来的铁栅栏往前走。我们停了一会儿。在一小片桤木丛附近,有三匹步履沉重的白马打着响鼻小跑着,带起一块块草皮。它们满怀期望地在我们身边排好队。塞尔温大夫从裤兜里掏出饲料来喂它们,用手抚摸它们的鼻孔。他说,它们靠我的施舍过活。
我去年花几个英镑从马匹拍卖会上把它们买了下来,要不然,它们肯定会被人从拍卖会牵进屠宰场。它们分别名叫赫谢尔、汉弗莱和希波路图斯。关于它们的过去我一无所知,不过在我把它们买到手时,它们看起来很糟糕。毛上长满壁虱,两眼无光,马蹄由于在潮湿的地里站得太久,已完全皲裂。这段时期里——塞尔温大夫说——它们的光景有所好转,也许还能再活几年。然后,他便同这些明显对他极有好感的马匹告别,同我们一道朝花园更为偏僻的部分漫步而去,时走时停,话语枝枝节节地蔓开。一条小路穿过草地南边的灌木丛,通向两旁种着欧洲榛子的林荫道。树枝在我们的头顶织成冠盖,灰色的松鼠们在其间嬉闹。地上密密麻麻布满裂开的核桃壳,几缕阳光透过簌簌作响的枯叶洒落,被几百株秋水仙花承接。欧洲榛子大道尽头是个网球场,四周有一道刷白的砖墙。塞尔温大夫说,网球曾是我的挚爱,但现在球场已失修破败,就像这附近其他许多地方。不只是这个菜园——他用手指着已倒了一半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玻璃暖房和已经压得变形的棚架,继续往下说,不只是这个菜园在荒废多年之后会毁掉,他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就连这无人照管的自然风光也在呻吟,在我们强加给它的重担下衰落。这座园子曾经养活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全年都有由精湛技术培育出来的水果和蔬菜从园子端上餐桌,尽管荒废得厉害,如今它还能生产这么多果蔬,远远超过这个家庭无疑正越来越缩减的需要。任这座昔日打理得很好的园子荒芜也有不经意的好处,塞尔温大夫说,无论是原本长的,还是他在这儿那儿随意播种或栽植的,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精致风味。我们从一个疯长着一丛丛齐肩高的芦笋的园地和一排高大的洋蓟亚灌木之间穿过,走向一小片挂着无数红黄色果实的苹果树。塞尔温大夫把一打妙不可言的苹果——它们确实在口感方面超过我迄今尝过的所有苹果——放到大黄茎蔬菜叶上,作为礼物送给克拉拉,而且说明,这个品种的名称和它本身很吻合,叫“巴思美人”。
保罗·贝雷耶特
有些谜团无法解
一九八四年一月, 我得到从S 城传来的消息, 说保罗·贝雷耶特——我在小学听过他的课——于十二月三十日晚上,也就是他七十四岁生日之后的一个星期,结束了生命。就在S 城外的一小段铁路线上,当一辆火车从小柳树丛出来,拐向空旷的原野,他已卧在那里。报纸广告中那则以“哀悼一位受人爱戴的同胞”为标题的讣告也给我寄来了。讣告并未涉及保罗·贝雷耶特是自愿还是迫于自我毁灭的压力自尽,只谈到了这位已故教师的功绩,谈到他对学生的照顾远远超过自己的本分,谈到他对音乐的热忱、思想的丰富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方面。讣告又以近乎旁白的方式补充,而未进一步解释,说在第三帝国时期,保罗·贝雷耶特被阻止从事他所选择的职业。这种支离的论断,这种暴力的死亡方式,导致在后来的若干年间,我在脑海里越来越频繁地想起保罗·贝雷耶特,终于尝试除了搜集我自己对他的钟爱的回忆之外,去探寻他那些我不知道的往事。我进行的这些调查把我带回了S 城。自从中学毕业后,我只是偶尔回到那里,而且间隔一次比一次长。我很快就了解到,保罗·贝雷耶特直到最后,在S 城一栋于一九七〇年建在昔日达戈贝特·莱尔兴米勒艺术与商业园圃地面上的公寓里,有一套自己的住所。但他很少待在那,而是经常外出,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即使拥有多种多样的教育才能,由于这种经常不在城里的情况以及退休前好多年就已开始变得明显的异常举动,怪人的名号还是牢牢地扣在了保罗·贝雷耶特的头上。而就他的死而言,这个名号也确证了S 城居民(他在他们中间长大,除了某些时候,总生活在他们之中)的看法:事情的发生是因为注定要发生。我在S 城同认识保罗·贝雷耶特的人所作
的为数不多的交谈没有给我任何启发,唯一值得注意的也就是,没有人叫他保罗·贝雷耶特或者贝雷耶特老师,相反,每个男士和每个女士往往都只称其为保罗。我从中得到这样的印象:在他的同时代人眼里,他从来就没有真正长大。这使我想起,就连我们在学校里也只叫他保罗,并没有不敬的成分,而是像谈到一个作为表率的兄长,就好像他同我们是一伙,或者说我们同他是一伙。现在我明白了,这当然是一种幻觉,因为尽管这个保罗认识我们,了解我们,可我们当中却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的内心是什么样子。而我也是如此迟才试图去缝合这段空白、给他涂上色彩,去想象他住在莱尔兴米勒老房子顶楼那套大住所的情景。这座老宅过去所在的位置现在成了一个住宅区,环绕四周的是绿色的菜畦和彩色的花圃,那时保罗经常下午在园圃里帮忙。我看见夏夜他躺在户外阳台上入睡,群星如行军般在他的脸庞上方架起穹顶;我看见冬日他独自一人在莫斯巴赫鱼塘滑冰,看见他伸开四肢躺在轨道上。在我的想象中,他把眼镜摘下,放到一旁的碎石里。那闪闪发光的钢轨、枕木的横梁、老城山间小道旁的小云杉树林以及他如此熟悉的山峦,在这双近视眼里变得模糊起来,在集涌的暮色中消逝不见。最后,当火车搏动的轰隆声越来越近,他只看见一片墨绿色,克拉茨山、特雷塔赫河和希梅尔斯施罗芬山的雪白后象在其中清晰可辨。可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些想象尝试并没有使我对保罗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充其量不过是暂时的某种感情泛滥而已。我感到感情泛滥是一种冒昧,为了避免这样,我现在记下我所知道的有关保罗·贝雷耶特的那些事和我去了解他的情况时所听到的一切。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我家从W 村迁到十九公里外的小城S。在旅行中,我从阿尔卑斯福格尔公共汽车与运输公司紫红色的家具搬运车的驾驶室使劲往外看,看林荫大道两旁无穷无尽的一排排树木。这些树蒙上一层厚厚的白霜,从昏暗的晨雾中露出来,出现在我们眼前。
虽然这次行程最多持续了一个小时,我却觉得像是环绕了半个世界。S 城当时还根本谈不上一座真正的城市,不过是有大约九千居民、条件较好、可进行集市贸易的集镇罢了。最后,当我们的车经过阿赫大桥,向S 城驶去时,我心中充满十分清晰的感觉,那就是我们将在这里开始一种新的、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我以为涂上蓝色瓷釉的城市路标、老火车站大楼前的大钟,以及依我看是极其雄伟的维特尔斯巴赫酒店立面,都可视为这种生活明白无误的征兆。不过让我特别觉得兆头好的是把一排排房屋间隔开来的、矗立着断壁残垣的小块废墟,
因为自从去过慕尼黑后,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瓦砾堆、防火墙和可以看见空无一物的天空的窗洞那样,明确地同“城市”这个词联系起来。
我们到达那天下午,气温急剧下降,大雪开始纷飞,直到夜里,才逐渐平静。当我第二天早上第一次在S 城上学,雪已积了那么厚,我惊讶万分,感到像过节一样高兴。我上三年级,这个年级由保罗·贝雷耶特负责。我穿着我那件有跳鹿图案的深绿色套头羊毛衫,站在五十一个与我年龄相仿、极其好奇地盯着我的同学面前,听着保罗好像从远处传来的说话声。他说我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他昨天刚讲过跳鹿的传说,现在正好可以把我套衫上的跳鹿图画到黑板上去。他要我脱下套衫,暂时坐到最后一条长凳上,挨着弗里茨·宾斯汪格尔,然后借助这个图案给我们示范,该怎样将一幅画拆散成极其细微的部分——小十字形、正方形或点——或者将这些细微部分组成一幅画。很快我就在弗里茨旁边埋头于我的学生练习本,模仿黑板上的跳鹿图,往我的方格纸上画起来。很快我就发现,重读三年级的弗里茨很明显也在尽心尽力完成自己的作业,可这项工作在他那里进展得极其缓慢。甚至当那些迟到的同学都早已做完这个作业,他的方格纸上也只画了十几个小十字形。在悄悄交换了一下眼色后,我手脚麻利地做完了他没有完成的作业。从这一天开始,我们还挨在一起坐了差不多两年。
在此期间,我帮他做了好大一部分算术、书写和绘画作业。这事很容易做到,而且几乎可以说做得天衣无缝。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保罗一再摇头说弗里茨和我完全一样,都无可救药,写的字乱七八糟,唯一的区别是:弗里茨无法写得利索,我无法写得慢。保罗丝毫没有指摘我们的合作;相反,为了继续鼓励我们,他把装着一半高泥土、镶上褐色框架的金龟子玻璃箱挂到我们长凳旁的墙上。在玻璃箱里,除了一对用聚特林字体标明为Melolontha vulgaris的金龟子外,泥土下面还可以看到一窝蛋、一只蛹和一只幼虫,在更上边可以看到三只金龟子,一只正在孵化,一只正飞着,一只正在吃苹果树叶。这个展示金龟子神秘蜕变的玻璃箱,在初夏激励着弗里茨和我去对整个金龟子类昆虫进行极其深入的钻研。这种钻研包括解剖学研究,最后在烹饪并喝完捣成糊状的金龟子的汤时,达到顶峰。事实上,出生在施瓦岑巴赫一个食指众多的小农家庭、就人们所知没有亲生父亲的弗里茨,最大的兴趣便是所有与食品、食品烹饪和食品配制有关的事。每天他都要极其详尽地论述我带到学校去与他分享的点心的质量。放学回家时,我们往往会站在图拉美食店的橱窗前或者去看艾因西德勒热带水果店的陈列,那里最吸引人的是一个深绿色、冒着透气水泡的鳟鱼玻璃缸。有一次,我们已经在水果店前站了好久——在这个九月天的中午,从店铺阴暗的内部吹来一阵使人感到舒适的凉风——年迈的艾因西德勒出现在门口,送给我们每人一个皇帝梨。这是个真正的奇迹,不仅因为这种水果如此珍贵,主要的还因为艾因西德勒的暴脾气远近闻名,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像对接待他那剩下的、寥寥无几的顾客那样恨之入骨了。在吃皇帝梨时,弗里茨向我透露,他会成为厨师,日后他也确实成了厨师,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厨师。他在苏黎世多尔德尔大饭店和因特拉肯的维多利亚少女峰饭店使自己的厨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此后不管在纽约、马德里还是伦敦都大受欢迎。弗里茨在伦敦时,我们还有过一面之缘,那是一九八四年一个四月天的早晨,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我在那里研究白令海附近阿拉斯加的科学考察史,而弗里茨则在钻研十八世纪的法国食谱。我们好像是故意这样做似的,彼此只隔一条过道,分坐两边。当我们有一次同时离开工作抬起头来,尽管其间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们却立即认出了彼此。然后,我们在自助餐厅里相互讲述自己的往事,也聊了好久关于保罗的情况,其中,弗里茨记忆犹新的主要是,他一次都没有看到过保罗吃东西。
大多数作家,即使优秀的那些,写能够被写出的东西;而非常伟大的那些,写无法被写出的东西,譬如塞巴尔德。
——《纽约时报》
塞巴尔德的杂糅风格的作品,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小说的类型,现在预测可能为时尚早。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自博尔赫斯以来,从根本上抹除和重画小说界限的第一人。
——《纽约客》
塞巴尔德的作品,首先要谈到的是,它们总有一种在作者死后才出版的气质。正如评论家经常说的,他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写作。他是二十世纪晚期zui有创造性的作家。
——英国著名作家 杰夫·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