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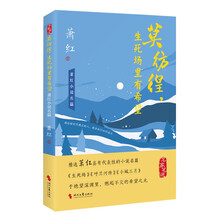

间隔一百多年的两次旅行,无论怎么互相“修补”,都留下了分离的印迹,一如从那时一直贯穿至今的中西对视的“沟壑”,永远填补不了的。
作者怀着一种别样的情绪重走李鸿章的旅法之行,找寻李鸿章留下的足迹。这是两个人的旅行,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活着的人有活着的人的现实,死去的人有死去的人的历史,现实与历史的碰撞让人害怕。
怎么能保证这个世界不与人们对它的叙述混淆在一起?时隔百年的两次旅行能把这一切牵到哪里?
作者怀着一种别样的情绪重走李鸿章的旅法之行,找寻李鸿章留下的足迹。这是两个人的旅行,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活着的人有活着的人的现实,死去的人有死去的人的历史,现实与历史的碰撞让人害怕。怎么能保证这个世界不与人们对它的叙述混淆在一起?时隔百年的两次旅行能把这一切牵到哪里?
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旅行,作者结合一些中国社会的现象和心理,警醒世人。正如作者所言:我们被多少假正义卷裹,让善变成做作和模仿。模仿得*像的民族*先毁灭。
巴黎北站
我常想开始的地方往往不是我们想象的去处,而结束的地方更距我们遥远。但我还是丢不下这个念头,想象第一站非比寻常,那些已与实景脱离干系的地点,是名词加想象的复合体,只需盘踞大脑便自成一种拔地而出的力量。我们一直在寻找停靠传奇火车的地点,又或干脆一个小城的车站,只要有静静的月台、火车启动或抵达时冒出白色的蒸汽,就已经是半个旧梦了。我们情愿过去只是个梦,那么偶尔再飘回来,也无碍。
故事开始的时候总要有一个地点。1896年7月13日,作为大清国的特使,中国方面叫钦差头等大使,李鸿章抵达巴黎的第一站,就是这座1864年才扩建完成的火车站:巴黎北站。这个火车站在1846年建成后不足十年,就已经盛不住飞速扩充的客流量。那是欧洲工业化步伐加快、万丈雄心只相信进步的年代。的确,如果必须回到19世纪,这个基调是逃不了的。从那时到现在,欧洲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几乎将已有的世界砸碎,按自己的意愿又重造了一个。
记得有一次与朋友比尔聊天,他说:“你看看周围,没有一样东西不是造出来的,连脚下的石子都是从别的地方运来,而这一切就是从19世纪开始。”
然后他睁大牛一样的眼睛瞪着我:“你想象得出吗?我们翻天搅地造出了一个原来没有的世界!”
我说:“想象已经远远不够,现在这个钢铁水泥世界是人的孤独杰作,与以往的创造不同,人第一次向自然扭过身去,不再惧怕; 并且第一次把最高统治权从人手里转给了那个非人的玩意儿——钱,从此真正的主人不是国王也不是上帝。这一百多年,地球完成了一次地壳运动,不过不是天然的,而是人工的。人怀揣着拔地而走的可能,并不满意老天给的这颗星球。”
他甩动着半长的栗色头发:“人是疯子!毫无疑问,人是疯子!”
我说:“不如说欧洲人是疯子,我们只是被绑架的人质,忧愁是我们的记忆。”
我挑了个晚上,来到这座后来又扩建过几次的车站。不足两个世纪,在奢华中迅速衰老的欧洲对进步的神奇秘方已产生怀疑。总要尝遍奢靡的各种滋味,才发觉这膘肥毛亮的动物无头无尾。
曾作为进步标志的北站,物转星移,成了负面新闻的释放匣子,有人说这是郊区青年贩毒斗殴的窝点。文明越走越灿烂之痴人说梦,一个半世纪就足以拿出证据。所谓“青年”是精英们秘送给黑人和马格里布人的统称。这个社会布满行为和语言密码,为的是表面看去漫无禁忌。“青年”对掌握密码的人有另一层含义,前面加冠词,知道密码的人便都知道指的是哪一群人。同时密码也是分级的,越到社会上层掌握的密码越多,像一个金字塔,每一层都自觉设界,不让真实下漏。像“青年”这类密码是最低级的,民间都已心照不宣。
但这个必要时耍一耍大戏的玩偶社会堪称小资天堂,因为下里巴人庸俗的延展性和破坏性被降至最低点。金腰带般缠在金字塔塔尖下的小资们被这样的娇宠哄得个个以为怀揣国王卧室的钥匙。小资被强权征服远易于“野蛮人”,他每一个细胞都想取悦于人。被玩于股掌之中的人,偏偏易生自由幻觉,人性就是这么卑贱得掉渣。这聚光舞台上脂粉的狂舞,足以遮蔽死亡之手,让人看不见小资天堂是一个文明被送进陵寝前涂脂抹粉的殡仪馆。
北站位于巴黎东北部穷人区与城中心富人区接壤的地方。再往北圣德尼斯一带,已经远不是我们臆想的巴黎,而是小马里或小摩洛哥,只有那些旧房子还顽固地为现实提供历史苍白的记录。人的迁徙是文明被偷梁换柱最秘而不宣的武器,有时想想便唏嘘不已,那些扯着文明皮囊的人群,肆无忌惮地增删着它的细节,却早已脱了旧血脉,也并不需要什么凭据,就做了主人。不管在哪里,野蛮人都是最后的赢家,旺盛的生命力藤蔓一般寻找最屈辱的去处,悄无声息地繁衍。不需百年,文明城堡的细节便被偷换,只留下个空架子。现代化不过是将隐而不露的流变浓缩了时间、压缩了距离,让人无须掘墓,便一眼看到了。清醒者时常在这种时候想赶在一切尚未结束前遁入黄泉。
北站我是不常来的,往北去远至阿姆斯特丹都可以自己开车。越是生活在一个城市,越是各人有各人的世界。偷生在十五区小资间的我,虽时时意识到终身为钱袋绑架的命运,亦不喜富人世界的规整和气大压人,但对北站以北贫民区的繁杂与亲昵也是逃之不及的。在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个问题上,宽容、慷慨和灵性这些面纱都是撑不住半秒的。
时值九月初,夏天的尾声,气温已经变得随心所欲,像这个橙色、湿热的傍晚,法国人浪漫地称之“印第安夏天”,温度让血管和毛孔舒张到身体兴奋所需的恰到好处的程度。有一首民歌唱北美的印第安夏天,橘黄色的。几句歌词便让我在十数年间为薄暮西下找到了放置想象的词语匣子。
乘四号地铁可以直入北站的腹部,这就让车站外墙一尊尊华美的雕塑失去悦人的目的,历史剩余的奢华为最后的眼睛顽强地坚守着那几条旧花边。在拉丁区换乘四号地铁,扑面而来的已是肤色的深度,那个渐变的过程默然不语然而却是神速的,让你即刻惊觉贫贱剪不断理还乱的生命力,以及在肤色的覆盖交替中,文明暗流的角斗和征服。进了北站,这幕堪称“弱者的报复”的景象更加触目,在走进车站旧大厅之前,那些向旅人兜售小商品的店铺满堂堂的摆设、物品浓重的气味、惨白的照明,提醒你人生下水道之密如血管。直到走近月台,这种“贱民”呼啸而来的报复才一点点退去。
我们在旧电影里看到的飘动着白气和车头“扑哧扑哧”喘气的月台,已被进步永远留在了明信片上。新的尖头高速火车减速进站,几乎没有摩擦铁轨的声音,只听见自动门扑的一声开启,人水一般泄出,在下一班火车启动的宣告声中,沉着脸缄默无言的人群在各个出入口消失。只在这种聚散地人群流逝的速度里,现代人无主的人生,以及被极度扩张的自由幻觉,才像针一样刺过来。在活着等同消费的时代,被抛出历史轨道的他们来不及抽泣就已被品牌同化。他们多半是轻装的,被商品同化的大军,远行已不用带上半个家。何况这里的人走到哪里都没有带礼品之累,这个自我围墙建得极高的民族,因为小气而设计出了另一种虚伪,绝少物与物交手传递的直白,为人的自我提供了躲避追索的空间。
想到李鸿章从这北站下车,居然带了活鸡,装在一个柳条编的笼子里,怕巴黎没有新鲜鸡蛋吃。那后来在旅行中简直是累赘的上百个行李箱里也不知装了多少礼品,但东边的宝贝西边可能一钱不值,送礼的两头常是这么一冷一热。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入宫谨见乾隆,带去天文仪,乾隆说是雕虫小技;乾隆赠马特使一绿一白两个玉如意,那帮眼里只有透明宝石的英国佬,对这两块混浊的石头也是大眼瞪小眼。东西在人眼里价值的飞升和坠落,是对人的贪婪本性开的最大的玩笑!
……
巴黎北站
拉法耶特街
大饭店
7月14日上午的频繁奔波
阅兵式和暗杀
雨果广场与奥什大街
埃菲尔铁塔上的午餐
礼品清单与克雷西的奥恩河
总统府晚宴与“天朝的塔列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