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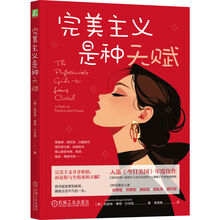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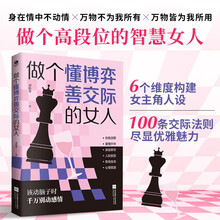
没有女人天生是母亲。
洞幽察微的生育记录 道出女人的焦虑与煎熬。
感谢时代,生育终于也和婚姻一样成为了可讨论的问题。
怀孕生子不仅区分了男人和女人,也区分了女人和女人。怀孕生产后,女人对于存在的意义的理解发生了巨变。她体内存在另一个人,孩子出生后便受她的意识所管辖。孩子在身边时,她做不了自己;孩子不在时她也做不了自己。人类的每一位成员都会经历从出生到独立这一异常艰辛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必须征用某个女人的一段生命。
《成为母亲》忠实地呈现了这段生命。它是一种寻常生活从不可见、不可感,向激烈的热情、爱与奴役转变的过程,它还是一种束缚,一种妥协。
身为女人,成为母亲是什么感受?照顾一个幼小的婴儿又是什么感觉?而当孩子长大,有了自己的意识,母亲又作何感想?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记下了自己那一年包含多重面向的的经历:个人自由、睡眠和时间的终结,对人性和艰苦工作的重新认识,追寻爱的真谛,游走在疯狂和死亡之间,对婴幼儿的情感体验,对母乳喂养的思考……
四十周
在泳池的更衣室里能看见很多女性的身体。如同洞穴壁画一般,裸露的身体有一种叙事特质;这一特质会因衣着与环境而沉默,它只会在此,这个潮湿的公共场所出现,在这里,我们依据性别进行匿名分组。虽然我也是女儿身,更衣室的这一幕依旧短暂地让我产生了一种孩童才有的恐惧,看到这些乳房、腹部和臀部,我反感且敬畏;这些非理想化的、原始的肉体忘却了自己的魅力,似乎纯粹为生殖而存在。吹风机在歌唱,储物柜门因为开合而发出巨响,淋浴房那铺着瓷砖的地板满是药膏与泡沫。青筋暴露、肌肉发达的大腿来回阔步,赤裸的手臂整理着纠缠的头发,用毛巾擦着颤得厉害的皮肤。乳房、腹部和臀部各式各样,有的有痣和疤痕,皮肤或皱或光滑,有的如同刻了神秘符号,有的则空白一片,像刚成形的大理石:是陈述,也是物料,它们作为物体而存在,单靠外形去传达信息。有时更衣室里有小孩,我发现他们凝视的样子与我过去一样,我现在还有点想这样做:他们对于成人的外形,其中明显突起的部分,身上的绒毛,以及饱经风霜的样子所暗含的信息表现出过分的惊讶与恐惧,这一切揭示了愉悦和痛苦,与交媾、怀孕以及生产相关的未曾透露过的秘密。如同恐怖电影的预告片一样,成人的身体明显地暗示着想象力范围内那些一直让人心绪不宁的存在,直到法定年龄,你才会完全明了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小时候,从对生孩子的后果有所了解的那一刻起,我便担心起这件事来。当时,我对生孩子的了解不含脚注,也无条款表明你不一定非得要孩子,更别说你也许就无法生育:如同生活中所有的事实一样,生孩子这件事没法儿讨价还价。看着我那休息不足的瘦小身体,我只知道,终有一天,另一个身体会出自其中,即便我不清楚它会如何、从何处出来。就我所理解,我不会在以后装配某种提取装置。这具躯体极有可能在未来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如同装满糖果的墨西哥皮纳塔娃娃。有些人留着这些娃娃,甚至在最急迫、最难以抑制的欲望的刺激下也无法让悲剧——娃娃的使命所在——在它们身上上演。大多数人不会留着这些娃娃。我在加利福尼亚长大,在当地孩子们的派对上,我们曾用棍子击打那些娃娃,直到它们炸开,随后交出宝贵的糖果。无须真知灼见就能知晓生孩子会异常痛苦。我很快便借鉴早年间的疼痛经历来理解这一痛苦。于我而言,忍受身体上的不适是我是女人这一事实的必要附属品;每当我切到或擦伤自己,摔倒或去看牙医,我总是既感到痛苦,又因此感到恐惧,同时我也恐惧,自己明明注定会在未来感受到生孩子所带来的神秘剧痛却还是记得这点儿小伤。
上学时,有人给我们放了一部讲述一个女人生孩子的影片。那女人裸着身子,胳膊和双腿瘦而有力,动来动去,她腹部有个巨大突起,这让她饱受折磨;她头发很长,乱蓬蓬的。她没被禁锢在床上,没被一圈站着的穿白大褂而闪着白光的医生和护士围着。事实上,银幕上的她压根儿就不在医院。她独自一人站在一个小房间里,那里除了一把放在中间的矮凳子外什么都没有。看到那把凳子,我有点分心。对于即将到来的猛攻,这把凳子似乎不是合适的防御工事。镜头很暗淡,在夜间拍摄;观众观看时,就像是通过墙上一个孔窥视某种糟糕且隐秘的事物,某种我们注定无法理解也无意观看的事物。那女人一边呻吟,一边咆哮,在房间里踱步,如同疯人一般,又像是关在笼中的动物。她时不时在墙上靠几分钟,双手抱头,然后大喊着朝对面的墙上撞去。仿佛她正在同某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在她的一系列反应所造成的噪音及破坏的映衬下,她的孤独显得很奇怪。这时,我注意到她其实并非独自一人;另一个衣着完整的女人正安静地坐在角落。那女人偶尔会小声说话,几乎听不见她在说些什么,这声音虽然微弱,也帮不上什么忙,但的确是一种鼓励。她的存在让分娩过程变得颇为正式,可她帮不上忙,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这很残忍,也让人难以理解。那裸体女人用力撕扯自己乱糟糟的头发,咆哮了起来。突然,她跌跌撞撞地走到了房间中间,坐在凳子上,一条腿弯曲着,另一条腿有力地伸向一旁;她的双手紧紧抱在胸前,仿佛准备唱歌似的。她的同伴起身跪在她身前。摄影机是固定的,我们看不到事态发生转折时的特写镜头。事实上,画面似乎越来越暗,越来越不清晰,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一时间,两个女人一动不动,看起来像是在亲密交流,两人的身影也混在了一起;突然间,穿着衣服的女人身子向前倾,伸出双手,然后一个不断扭动小身体的宝宝便落在了那双手里。裸体女人发出了最后的痛苦的叫声,这声音如长笛般,音调越来越高,最终变为愉悦的约德尔式唱腔。
“娜塔莎在1813年的早春结婚,”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处描绘年轻的女主角时如是写道,“1820年时已有1了三个女儿,此外还有一个儿子,她渴望生儿子,眼下正在照料她儿子。她变得愈发结实,肩也变宽了,于是很难在如今这个健壮且充满母性的女人身上辨认出昔日那个苗条且活泼的娜塔莎的影子。她的容貌更加轮廓分明,表情冷静、柔和而且安详。她脸上没了不断发光的勃勃生气,那股生气曾在她脸上燃烧,让那张脸充满魅力。如今,别人往往只能看到她的脸和身体,而看不到她的灵魂。映入人们眼帘的她,只是一个强壮、模样俊俏且能生孩子的女人。”
怀孕时,肉体与心灵的生活不再努力区分彼此,而是不可避免、历史性地交织在一起。若将人生比作一套书,描写年轻、美貌和独立的那一卷完结后,接着便是描写为人母的那一卷,比起前一卷来,这本书从第一页起便呈现出更长且更难读的迹象:故事讲述了托尔斯泰的娜塔莎如何从声音稚嫩、喜爱打扮的万人迷变为谜一样的一家之主,也讲述了女儿如何变成家长,女主角如何变得同浪漫情节势不两立。托尔斯泰并未写出这么一卷,而是写了《安娜·卡列尼娜》来发掘母亲这一角色中依然存在的女性形象,并展示其破坏力。要知道,每个人做起母亲来都差不多,任何花招都无法以和平方式将人从这种职业中解放出来;怀孕则是学习成为人母的新兵训练营。
序章
四十周
莉莉·芭特的宝宝
肠绞痛与其他故事
爱,别离
妈妈宝宝
额外的狐狸
地狱厨房
帮手
请别忘了大声叫
和睡眠说再见
呼吸
妒火
译后记
这是本可以煽动叛乱的书。我常被它逗笑,同时痛苦地认可它所说的。
——艾莎·弗洛伊德,英国小说家
书中的每一行都有一种凶猛的警觉性智慧,并成功地将自怜转化为某种实用的信息。知识女性还是要生孩子的,这本书是为那些感觉当妈妈并非全是甜蜜与光明的人准备的。
——《卫报》
跟惊悚小说一样引人入胜。没有一个母亲会对它无动于衷。
——《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