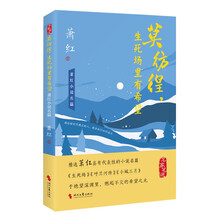《给青年小说家的信》:
可是,这样泛泛的思考让我们有些脱离了您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是回到具体问题上来吧。您在内心深处已经感觉到了这一文学倾向的存在,并且已经把献身文学置于高于一切的坚定不移的行动之中了。那现在呢?
您把文学爱好当作前途的决定,有可能会变成奴役,不折不扣的奴隶制。为了用一种形象的方式说明这一点,我要告诉您,您的这一决定显然与十九世纪某些贵夫人的做法如出一辙:她们因为害怕腰身变粗,为了恢复美女一样的身材就吞吃一条绦虫。您曾经看到过什么人肠胃里养着这种寄生虫吗?我是看到过的。我敢肯定地对您说:这些夫人都是了不起的女杰,是为美丽而牺牲的烈士。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名叫何塞·马利亚,一个西班牙青年,画家和电影工作者,他就患上了这种病。绦虫一旦钻进他身体的某个器官,就安家落户了:吸收他的营养,同他一道成长,用他的血肉壮大自己,很难、很难把这条绦虫驱逐出境,因为它已经牢牢地建立了殖民地。何塞·马利亚日渐消瘦,尽管他为了这个扎根于他肠胃的小虫子不得不整天吃喝不停(尤其要喝牛奶),因为不这样的话,它就烦得你无法忍受。可何塞吃喝下去的都不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快感和食欲,而是让那条绦虫高兴。有一天,我们正在蒙巴拿斯的一家小酒吧里聊天,他说出一席坦率的话让我吃了一惊:“咱们一道做了许多事情,看电影,看展览,逛书店,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谈论政治、图书、影片和共同朋友的情况。你以为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和你一样的吗?因为做这些事情会让你快活,那你可就错了。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它,为这条绦虫。我现在的感觉就是:现在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着我肠胃里的这个生物,我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奴隶而已。”
从那时起,我总喜欢把作家的地位与何塞·马利亚肠胃里有了绦虫以后的处境相比。文学抱负不是消遣,不是体育,不是茶余饭后玩乐的高雅游戏。它是一种专心致志、具有排他性的献身,是一件压倒一切的大事,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奴隶制一一让它的牺牲者(心甘情愿的牺牲者)变成奴隶。如同我那位在巴黎的朋友一样,文学变成了一项长期的活动,成为某种占据了生存的东西。它除了超出用于写作的时间之外,还渗透到其他所有事情之中,因为文学抱负是以作家的生命为营养的,正如侵入人体的长长的绦虫一样。福楼拜曾经说过:“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换句话说,谁把这个美好而耗费精力的才能掌握到手,他就不是为生活而写作,而是为了写作而生活。”
这个把作家的抱负比作绦虫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新意。通过阅读托马斯·沃尔夫(福克纳的老师,两部巨著《时间与河流》和《天使望故乡》的作者)的作品,我刚刚发现这个想法,他把自己的才能描写成在心中安家落户的蠕虫:“于是,那梦想永远地破灭了,那童年时期感人、模糊、甜蜜和忘却的梦想。这蠕虫在这之前就钻进我的心中,它蜷曲在那里,用我的大脑、精神和记忆做食粮。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