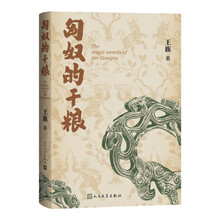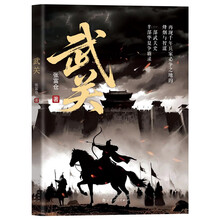第一章命运机巧,结婚给吕雉搭起一个台
一、算卦风波
踩稳矮木桩,踮起脚尖挂妥招牌,吕文站定,瞅了瞅还算周正,双手将“吕氏断相”布幡下摆抻展,背后有人道:“博士好雅兴!”
吕文回望,一个男人穿了件织锦玄色曲裾,宽袖厚襟,自知他是个体面人,忙拱手作揖道:“虚玄之学,承君抬爱。”吕文谦恭地弯腰示请,掀开帐帘,二人入帐内,对坐在软榻上。有人掀帘探望,吕文摆手谢绝。
来人倒不客气,冷不丁就把胖脸朝吕文凑过来,鼻尖抵近,问道:“吕公赐教,鄙人面相如何?”
吕文细观,来人鼻挺眉浓,脸肥腮满,满脸挂着富贵。可双目闪烁,额头青晦,心中念叨“不问富贵问命运”口诀,便知道断无好事,捻须道:“请教公所问何事?”
“单就面相看,先生可知我福祸?”
见他不肯道出心中所隐,吕文揣测他是想试探自己一把,便先放出一句开场白:“公自是富贵无边,家财何止万千?”
那人偏冷冷“哼”一声,说:“真正是穷无一物。”这里明显是说反话。
吕文猜到他一定在刻意隐瞒什么,又拱手一揖:“若真如公所言,我当奉送一百钱,自毁卦摊。”这是硬话。江湖名相,行走诸国,凭的就是一双毒眼。突兀上来问祸福,定是糟事缠身,吕文故意激将,逼他就范。
果然,那人叹一口气,哀求道:“先生救我。”
“稳住。”吕文不慌不忙递过一杯热浆。那人双手接住,盯着氤氲的热雾,目光游离。
卦摊帐篷内,东西向放置一张榆木矮案,占据大半的位置。案上数卷解卦竹简和一把拂尘。靠北边一个笤帚,南边一个小灶台,灶上的瓦甑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煮着浓浓羊乳。
这人说,他前天回家,正遇上夫人和一个男人在做肮脏事情,暴怒之下,将那男人打将出去。可这两天对方家人找上门来,纠缠不休,闹得神鬼不安,所以,“请问先生,可有解忧招数?”
吕文见此人说话时,神情呆滞,目光不是盯笤帚就是瞅灶台,天上地下胡乱飘,无处着落。心里知道刚才一句话逼迫的还不够狠,冷冷一笑,说:“藏着掖着,毫无信任,如何帮汝?”
“就这点事,说得清清楚楚。”这人弹指起誓,“但求吕公指点迷津。”
果然不是肤浅之人。若是不露几手,怕他断无道破之意。吕文略一沉吟,道:“观你相貌,是个‘三白眼’,尤其容不下感情不专。料汝绝不只是厮打那人,吾断定你有血光妄灾。”“血光”二字一出口,仿若真有股鲜红的血柱“嗞”地一声喷射而出,那人眨几下眼,摸了一把右腮,像在堵伤口。
“吕公,鄙人……”这人闻听吕文一针挑透,顿时左顾右盼、支支吾吾,“既然先生已经看出来,瞒是瞒不住了。我杀了……他。”天无风,心疯狂。凡事知道的越多越危险。吕文暗暗吸一口冷气,后悔不该一早接这触霉头的卦。
吕文家中,置有粮店等铺面,家底亦颇殷实,平日里游走富商贵族,相面酬金本已不薄。子女们都劝其不必在县城摆摊,挣那几个丢面子的糟钱。吕文却不这么看,干一行敬一行,若是只顾富贵人家,不理穷家,不但埋汰了平生所学,也是自毁阴德。因此常在闲暇时于这县城北门口固定位置设下卦帐。
虽已料定必有大事,可乍听他说出人命官司,吕文额头一皱,双眉紧锁。
若仅是打死一人,对于面前这个人不是大问题—穿得起锦蚕服饰的,非富即贵。掏钱是可以买通官司的。而且他直接就说出了“杀人”,恐怕这只是个引子。想到这里,吕文后背冷汗直冒。苦习面相多年,可不敢一着不慎,半世清誉毁在此人手中。
此时正是公元前218年八月十三。他们这是在单父(今山东单县)县城北大街,毕竟不敢高声。单父本属鲁国,后被西面的魏国兼并,秦始皇又在前221年一统六国,虽礼崩乐坏,可秦律严苛,若是“杀人”之后还有连环案,此事太大,非相面师傅所能拆解。且对方已经找上门来,县衙岂不早已知晓?
想到这里,吕文内心潮涨潮落,却怕一言不慎,激怒来人,只得先稳住情绪,轻轻咳嗽一声,道:“伤人抵罪,杀人偿命,这是官家的事。吕某一个相面的,爱莫能助。”明知他隐瞒了实情,故意遮遮掩掩,吕文示弱地想推托。
“可还有拆解或迟延的办法?”那人神情颓唐,揪住深衣,边缘的一朵金丝绣牡丹早被揉得面目全非。
“倒有一法,只怕你不肯。”
“快说,只要不抵命,万般都肯。”
见来人不肯离去,死死纠缠,吕文心说,知一已罪,何妨知二。遂掀起帘角,扫一眼帐前穿梭的行人,伸直脖子,四目相对,叩齿相闻,低声说:“仔细将实情说与我听。”
“我把亭长也打伤了。”说完这句,那人蹙眉沉吟,再不言语。双手作揖,哆嗦不止。
吕文学识渊博,游走多国,识破万人面相,自然极通人情法理,越听越害怕,明白此事绝非如此简单,轻嘬一口浆,先稳住神,又宽慰他说:“回家之后,你且说,亭长与你家夫人有染,正行龌龊之事,邻人撞见不愤,奋力扭斗,互伤性命。大大方方告官,自会消灾。”这已经不是拆解卦相,属门人谋士之策。
扔下一串绳钱,足有一百,来人心满意足地站起身,弯腰作揖致谢。
吕文摆摆手,示意他蹲下,又低声嘱咐:“你的灾,见不得日光,需过一晚才能禀告官府。切记切记。”此种神秘,相面师一出口,玄机深奥,是人就信。
翘首见已看不见来人背影了,吕文长舒一口气,急急忙忙研墨运笔,写好一个九片竹简,用红布包裹好,出帐抬头看,日头毒辣晃眼,吕文揉一把太阳穴,安定情绪,将竹简交给临近一个卖梨的少年货郎,说:“送到县衙,不敢耽误。”说话间递给货郎十个铜钱,算是酬劳。
不理招牌,连帐篷也顾不上收,吕文步履匆匆地空手赶回家中,一进门就对大儿子吕泽说:“速去找两辆安车、一驾辎车,不论贵贱,只要是快车就好。”安车多是四匹马拉,有低矮的车篷。辎车则一匹或两匹马拉,有车厢。
又叫过二儿子吕释之、长女吕雉、次女吕媭和妻子吕媪(ǎo),吕文吩咐道:“速速收拾,我们这就走!”
“去哪里?”三个女人都疑惑,好好的,干吗要走?
吕释之见父亲表情凝重,不便多问,追问一句:“此刻便走?”
“去沛县!”吕文用右手捏一捏白净的额头,“细软就不要多收拾了。回头路上跟你们解释。”
这必定是遇到塌天大祸,一家人从未见过著名的相面先生吕文如此慌张过。吕媪焦急地问:“好几桩买卖,也不要了?”心疼一摊子生意丢了可惜。
吕雉见父亲面色凛然,拉一拉母亲和妹妹的衣袂,快言快语地说:“父亲的话自有道理,别误了事。不要惊慌,不要吵闹。勿引起邻居怀疑。”
吕文冷冷地说:“生意日后再派人来妥善料理,今日只管拿随身物件。只怕迟了,走不脱,连命也保不住了。”
“穷家值万贯。”何况吕文这样的殷实人家。件件收拾妥帖,装车完毕,已近黄昏。叮叮当当地摆了很长一溜。邻居们也有问询的,一律以访亲敷衍。
吕泽的两个儿子吕台、吕产和吕释之儿子吕禄等几个小孩,不知道这是躲灾,见人多热闹,反而“人来疯”,穿梭在人群中片刻不得安宁。
两辆大安车,专为让吕媪、吕媭等女眷以及小孩儿乘坐。吕泽弟兄俩骑两匹壮硕骡子随行,三五个家奴皆乘自家常备的轺车同行。
吕文站在安车旁,伸出手来,抚摸着马屁股上棕色的毛,来回拨捋着,抠掉一粒粘在棕毛上的小泥疙瘩,轻拍一下,沧桑地说:“走吧……”一转身,心头酸雨倾盆。年近六十,却要抛家舍业离乡背井,何其心碎!
看着几辆马车逶迤地朝着东南远去,吕文感慨道:“可惜了这四进的院落。”安排了一个老家奴,一再叮嘱,“你守在这里,见我的手迹就将院子交给他。缘分一场,我自然不肯亏待你。”
说完这句,吕文牵起吕雉的手说:“跟我去个地方。别一别再走。”
路上才听父亲低声说起,那人是个鲁国落魄贵族,观他“印堂有纹”,杀机很重。偏又是个“三白眼”,这种人动辄会起杀心。料定他已经杀了亭长。况且已将他的事明知了官府。他不动刀杀吕家,岂肯罢休,所以前往沛县投奔县令故交。
“‘三白眼’?如何说?”吕雉请教。
“黑眼珠靠上,左右下三面全能看到白眼球,即是‘三白眼’。遇到这人,千万要当心。”吕文对这个女儿,极其钟爱,凡问必复。
马车虽小,拉车的却是匹蒙古马,发力猛、劲头足,一溜小跑。车夫也很卖力,稳稳妥妥地驾着辎车朝着县城西南的山上奔去。
“雉儿,可还记得父亲跟你说过的‘命’、‘运’?”
“记得,‘命是船,运是雇来的艄公’。”吕雉掀开棉布轿帘朝外看。云蒸霞蔚,金黄一天。
面朝车外,吕文出神地望着远处,吕雉挽住父亲的手臂,不解地问:“我们今日要住山上?”
单父城西南,有一个馒头土山,叫作栖霞山,又名“老山堤顶”。爬到山顶,正看到单父八景之一的“栖霞晚照”。台上余辉铺陈,缤纷如锦,人也被染了一层金黄。
山顶茂林深处,有一不大的草庐,叫“栖霞居”。门口一副墨宝:
来时云作伴
去路雾锁尘
父女携手走进栖霞居,小徒见是吕公,笑脸恭迎,一路巴结引到静坐堂,奉茶安坐。
室内陈设极为简朴。西边是土炕。迎门一张茶几,两边各置矮枰一张,东边安坐一个硕大的布坐垫。
“吕公今日好兴致。”口中诵念,智言老者慈笑着走进门来,“想起来来看老友。”
吕雉急忙站起身立在父亲身边行个礼,智言微微点头回礼。
吕文慨叹一声,说:“特来与大师一别。”
“去往何处?”
“沛县。县令是我故旧相识。”
“吕公可是惹上了什么官司?”智言问道。
“鄙人素来安稳,哪会糊涂犯事?”吕文与智言坐到茶几前,愁眉不展,“是吾多嘴,将一个人的荒唐命案告知了官府。这是结下了生死仇家,不走不行。”
智言轻轻颔首,问:“可是久住不回了?”
“短也是三五年。唯一的憾事,就是不能常与大师对弈了。”吕文茫然落寞地说罢,手搓眉眼,不住叹气。
“这倒不必伤感。”智言见他怅然若失的模样,宽慰道,“下得一手好棋,何愁找不到知音。吕公放心去吧。鄙人观你女儿面相非凡,临行前送她四句话:“拦腰刀好躲,绣花针难防,人心十六两,金刀卯时响。”
吕文叮嘱吕雉牢牢记住。枯坐半晌,站起身来,拉住智言的手,久久无语,一时唏嘘,落下几滴清泪来。智言送到门口,挥手作别,也有几分感伤。素友分离,免不得心酸。
走了几步,吕文急急折回,索来笔墨,写了一个竹牌,对智言说:“寒舍就捐给恩师吧,也算半件功德。”这才猛然回头,一去不回。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