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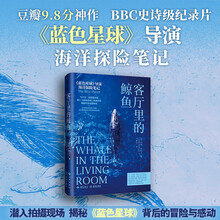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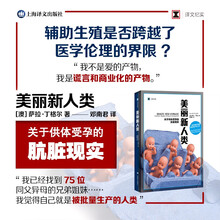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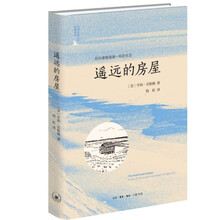

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真实经历
一位被迫为党卫队拍照的波兰摄影师,一个在邪恶之地为人性而战的人
徐贲导读推荐,书中收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珍贵照片
他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的集中营照片,让那些大屠杀的受害者不再是一串统计数据,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奥斯维辛的摄影师》讲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威廉˙布拉塞(1917-2012)在纳粹集中营的真实经历。
威廉˙布拉塞,一位波兰摄影师,于1940年8月31日被纳粹逮捕,随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编号3444。自1941年2月15日起,他被调入鉴定科,被迫为党卫队拍摄照片,不仅包括犯人的档案照,而且还记录下臭名昭著的“医学试验”。透过取景器,他看到的是瘦得皮包骨头的犹太儿童、用于“人种研究”的赤裸着身子的犹太少女、用于“医学试验”的双胞胎……是一双双充满恐惧的眼,一张张去日无多的脸,而他能做的太少。
1945年,当苏联军队逼近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布拉塞被要求销毁所有照片,但他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大量底片,如今成为见证奥斯维辛历史的珍贵资料。但布拉塞却再也无法端起照相机,因为那些恐惧的面孔总出现在取景器中,挥之不去。
10 “布拉塞,我很担心你”
随着时间流逝,威廉˙布拉塞和他的上司,党卫队二级小队长贝恩哈特˙瓦尔特相处得越来越好,如果可以把一名党卫队和一名犯人之间的关系称为正面关系的话。但对于威廉˙布拉塞来说,他的境遇绝对算是愉快的了。贝恩哈特˙瓦尔特不是那种会对他吼叫或打他的人。他也不是那种只叫他的犯人编号的上司,至少他们单独在一起时,还会聊天。瓦尔特叫他的姓:布拉塞。
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瓦尔特就和布拉塞一块儿说说话。布拉塞教他一些摄影技巧,因为瓦尔特对此有兴趣。作为鉴定科的头儿,他也经常被委派去拍摄运送犯人的场面。在奥斯维辛-比尔克瑙的斜坡上,他拍摄了很多照片记录犯人被淘汰、筛选的过程,还有那些刚到集中营就被送往毒气室的犯人的“最后一程”。从与瓦尔特的谈话中,布拉塞得知了他来自拜仁州的菲尔特,曾是制作石膏花饰的粉刷技工,在担任奥斯维辛集中营鉴定科的头儿之前,他曾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管理人员。他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给党卫队队员们放映过电影。
“布拉塞,我很担心你。”他说过好几次,或者是“布拉塞,你带给我们耻辱。你是我们的耻辱”!
威廉˙布拉塞无法理解他的上司说这些是想告诉他什么,而且瓦尔特也没有解释过他的话。他总是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后又重复这些话。
1943年的某一天,威廉˙布拉塞被传唤到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汉斯˙奥梅尔的办公室。布拉塞认得他,因为他到过几次鉴定科,视察鉴定科的工作过程。在他和贝恩哈特˙瓦尔特的谈话中间,他也和犯人布拉塞说过几句。他不是询问布拉塞的个人情况就是表扬布拉塞的工作。这种情况布拉塞在一些党卫队军官那儿也遇到过。他不再感到惊讶,而只是单纯地觉得奇怪,一个人如何能在一个每天决定大批人生死的位置上,还能进行表面上十分正常的谈话。
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和布拉塞说话完全是另一种语气。官腔,短句。
“家里人在做什么?”
布拉塞如何能知道家里人在做什么,他和家人又没有联系。同时他也觉得这问题并不是认真的。因为根本没有等他回答的迹象,下一个问题又随即而来。
“如果我们现在把您放了,您会做什么?”
布拉塞知道这名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问这个问题是想得到什么。不,布拉塞不想上他的当。他肯定是希望布拉塞即刻加入德意志国防军,和他们一起对抗敌人。
但是布拉塞没有给出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想要的回答:“我有一份好工作,被释放的话我还想继续工作。”
然而他还是再一次说明了给布拉塞的条件:只要他在德意志民族登记簿(Volksliste)中登记并签字承认自己是德国人,他立即就会被释放。
布拉塞一刻都没有迟疑就拒绝了。他已经两次拒绝了这样的条件。这一次他还是忠于自己的决定。
后来他得知,他的一些同胞选择屈服并在登记簿上签了字。出了集中营他们就立刻被遣入德意志国防军,并被送往前线。
19 切斯拉娃˙瓦佳
这女孩的模样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纠缠着威廉˙布拉塞。有很多照片触动过他,在他的脑海里扎下根,可这个女孩的影像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深知,自己不能够对他必须拍照的那些人存有感情。可是他忍不住。
1942年12月13日,切斯拉娃˙瓦佳同母亲一起被运送到了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她们来自波兰东南边的一个村庄。
像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的大多数犯人一样,切斯拉娃也必须在奥斯维辛主营的鉴定科拍照。一名女卡波带着一队妇女和女孩来到摄影棚。她们挨个儿被叫到编号,以便让威廉˙布拉塞拍照。
当叫到切斯拉娃˙瓦佳的编号时,她听不懂卡波在对她说什么。因为卡波说的是德语,而她只会波兰语。正当切斯拉娃毫无反应之际,那名女卡波用一根木棍打向了她的脸。眼泪混合着鲜血从切斯拉娃的脸上滴了下来,她的嘴唇被打破了。
威廉˙布拉塞端详着她。她还那么年轻,看上去是那么惊慌失措,那么无辜。
在拍照之前,他给了切斯拉娃机会让她能够擦干脸上的眼泪,抹去嘴唇上的血。
他很乐意再为她多做些什么,可是他不能。那名女卡波非常严厉,布拉塞没法判断她到底为人怎样。一次失言很可能就会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他感到打在切斯拉娃脸上的那一棒就如同打在了他自己的脸上。
1943年3月12日,切斯拉娃˙瓦佳死在了奥斯维辛-比尔克瑙,她母亲则死于数周前。
22 约瑟夫˙门格勒博士
在给约瑟夫˙门格勒拍照两周后,来自比尔克瑙的一队十五名犹太少女来到了集中营主营鉴定科。陪同这队少女来的有一名女看守、一名女卡波和两名波兰籍护士。
威廉˙布拉塞特别喜欢这两位年轻波兰姑娘中的一位,她在集中营里被错叫成巴思佳˙史蒂芬斯佳,他们第一次见面布拉塞就爱上了她。他觉察到巴思佳也有所回应,没有旁人的时候,她长时间深情地注视着他的双眼。可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在集中营里根本不可能去经历一场爱情。尽管如此,对于他和巴思佳来说,当他们碰面时能够一起聊聊天,相互靠近温存,也算是他们集中营生活中极其宝贵的调剂。
显而易见,巴思佳一口流利的德语和护士的出身是她能在约瑟夫˙门格勒身边当秘书的原因。
布拉塞被命令给这十五名犹太少女拍照。她们必须分成几人一小组,裸体站在相机前,分别从正面、背面及侧面被拍摄三次。
被迫在摄影师和他的上司面前脱光衣服让女孩们感到羞耻极了。就算对布拉塞来说也是非常不习惯的情况。他很没把握,他从来没有拍过裸体照。他唯一能做到的是让她们稍微好受一些。他把摄影棚里的一面通常只用来给党卫队官兵拍照使用的移动墙挪了出来,让女孩们可以在墙后面脱衣服。
拍照时他请陪同的两位护士帮助安排站位,让他在灯光不足以拍摄集体照的情况下能拍出比较好的照片。他绝不想离她们太近或是触碰到她们的身体。
女孩们悲哀的目光让布拉塞难以忍受。他预感到她们身上将会发生什么,而巴思佳在一次拜访中证实了他的猜测。
这些女孩还被测量了身高、体重,被记录了她们的外貌,一切记录完毕后,她们被带去了比尔克瑙的毒气室。
接下来的几周里,门格勒总是打发一队接一队的犹太少女和年轻女人来主营鉴定科拍照。正常情况下本该是会在意发型、衣着的少女和年轻女人,却被剃光了头发甚至耻毛,消瘦、憔悴,还被迫裸体站在照相机前。
布拉塞估算他几周内至少给两百五十名女性按照正、反、侧三面的规定拍了照片。两百五十双眼睛注视过他,他也必须注视两百五十双眼睛,眼里除了恐惧他读不出任何其他感情。而这两百五十双眼睛,短短几周后就会消失不见。
从他的女友巴思佳˙史蒂芬斯佳口中,布拉塞得知了门格勒的“人种研究”。难以想象,一个人会以怎样的研究方
法来确定某个人种是什么样的。他认为这简直就是狗屁。研究狗或研究马,这他还能设想一下,却没法设想怎么用
人来做研究。
“主要都是些女人,”巴思佳给他解释道,“他先让她们拍照,然后让她们站上秤,当然是裸体。肉眼都能看出来,她们瘦得就只剩了皮包骨!”
巴思佳实在难以抑制对门格勒的怒火。布拉塞打断她,让她小点儿声,以免声音传到房间外面。
巴思佳点点头,继续说道:“他之前肯定就知道面前站的都是谁。可是他不,他还额外侮辱这些人。他在一个表单里记录她们的发色和眼睛的颜色,从上到下地打量,就好像能发现什么病一样,他不过只是想确认她们的肤色而已,有那么多好看的吗?!”
巴思佳眼里噙着泪。
“他之前就知道,这些人统统都不属于他眼中心爱的雅利安人种。为什么他还要在把她们送去毒气室之前再欺辱她们?”
她的泪珠滚下了面颊,布拉塞把她抱进怀里。
布拉塞得知,门格勒医生应该还给她们做了手术。但是他没有线索得知到底都是些什么类型的手术,他也不想知道。作为摄影师,他从医生那儿听到看到的,已经足够了。他不需要知道更多残忍之事。
在他给女孩们拍照之后一阵子,门格勒又打发了一组在比尔克瑙关押的发育不良的人到鉴定科拍照。他们也得裸体被拍摄正、反、侧面三组照片。一次布拉塞有机会和其中的三个人攀谈,他从谈话中得知,这三人——两姐一弟是亲兄妹,姓奥维茨,来自布达佩斯,患有发育不良的家族遗传病。他们的德语极好,所以布拉塞能和他们很好地交流。他们三人都非常有音乐天赋,两个姐姐一人会拉小提琴,另一人会弹吉他,而弟弟有副很美妙的歌喉,他们靠在游艺演出中表演为生。
不久之后,门格勒医生打发比尔克瑙“吉卜赛集中营”中患有坏疽性口炎*的病人到鉴定科。
1943年夏天在比尔克瑙的“吉卜赛集中营”中爆发了这种疾病,患者多为儿童和青少年。
门格勒让人转告摄影师不必害怕被传染。这病只对深色人种有威胁,比如吉卜赛人,但对白人就不会。
布拉塞从没见过这样的情景:被带到他面前的人,脸上有开放性的伤口,皮肉的碎片挂在下面,而他能看见伤口里面白森森的下颚骨。
威廉˙布拉塞得给这些病人拍照。医生要的可不是人像照,而是开放性伤口的准确特写照。后来他得知,医生还在集中营里寻找美术工作人员,让他们把伤口画下来。
一些报告显示,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疾病,门格勒医生还做了试验。他取了患病儿童口腔黏膜的分泌物,然后注射到健康儿童体内,而后这些健康儿童很快患病并死亡。
布拉塞不得不为门格勒拍摄这些让病人深受侮辱的照片。
“这个人的脑袋里装的都是些什么疯狂的点子?”一次他在结束了一系列拍摄之后,破口大骂。这次,被医生打发来拍照的是一对同卵双胞胎和一对异卵双胞胎。
随后他又听说了一些更加让他摇头的事情。巴思佳都和他说了。
门格勒医生非常偏爱在比尔克瑙的斜坡上进行犯人的筛选。他就站在斜坡中间,向右或是向左动动拇指就决定了刚运送来的犯人的生死。每次被运送来的犯人中只有极少数能在自己因熬不过重体力劳动而死去或者是被以某种方式杀害之前存活一阵。除此之外的大多数犯人都会立即被他送去毒气室。
筛选犯人时,他有时还会笑或是吹吹口哨。这些都是巴思佳在她的上司不在时和一些犯人聊天时听到的。
有次被运送到比尔克瑙的犯人中有很多来自立陶宛的儿童。门格勒让人做了一个高一米四的框放在斜坡上。他命令儿童们挨个儿穿过那个框,所有没有撞到框而通过的儿童都要被立即送去毒气室杀死。
这个让威廉˙布拉塞难以捉摸的门格勒医生,对他却颇为亲切,时不时就出现在鉴定科和他聊天。
“您在您的领域真是位出类拔萃的行家!”门格勒对他说道,“我已经好多次根据您拍的照片确认这一点了!”
门格勒从不像其他党卫队官兵那样喊布拉塞的犯人编号。他也不和布拉塞以你我相称。他总是称呼“布拉塞先生”和“您”。他对待摄影师布拉塞从来都是彬彬有礼而且很友好,就像一位有教养的绅士那样。但是他也是一个双面人,对几十万犹太人的大屠杀负有责任。
布拉塞拍摄的那些集中营照片是对一个邪恶时代的重要记忆载体。……因为这些老照片,人们对布拉塞这个摄影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出版社邀请恩格尔曼写布拉塞的传记,恩格尔曼愿意做这件事,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些老照片的重要意义:它们能让今天的人们从新的视角来见证二战和纳粹的反人类罪行。
——徐贲
布拉塞给我们留下了强有力的图像遗产,因为这些图像,我们看大屠杀的受害者,不再是统计数据,而是人类。这些照片的摄影者是一个在不可想象的邪恶之地为捍卫人性而战的人。
——费格尔·凯恩(Fergal Keane),英国作家、BBC记者
布拉塞*伟大的行动之一,就是当他被要求销毁所有照片时,他保存了上万张。这些照片成为见证奥斯维辛残酷历史的永jiu的证据。
——朱迪思·科恩(Judith Cohen),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照片档案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