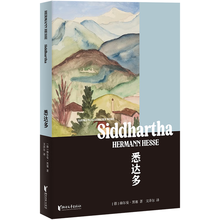《晴子情歌(上下)》:
或者他们自身原本就是时间的一部分,彰之想。他们为老乡的到来而欣喜,但看上去好像根本不认识那个正被欣喜包围的自己。这不是西蒙娜·韦伊所说的“深入到骨肉和灵魂的”劳动的无能,也不是资本主义所强加的机械化大生产和人性缺失的关系,而与乌贼捕捞船和港口一样,只流淌着单纯的时间罢了。那时间,既是彰之十几岁时,每年寒暑假都同渔夫和工厂的女工一起度过时,沁入他心脾的既非幸福也非不幸的平衡;也是因过于单纯而无法分割的,仿佛浑身器官融为一体似的呼吸的时间。
劳动,远比福泽公子和自己在受读书感化时代所思考的单纯。此刻,高级船员站在船首凝视航海图,捕捞长用无线电接听着愈来愈近的渔场的信息,足立和自己则无所事事地等待着什么,仿佛在等停开的公共汽车一样。一旦开始工作,足立和自己都将忘记等待公共汽车的此种感觉,迅速奔赴各自的岗位;工作一旦结束,他们就将重新回到无事可干的状态。对于海上生活,他最多只有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如果听见自己评说劳动如此这般的话,福泽公子肯定会千方百计寻找合适的词语与自己争论。彰之不知不觉地等待着公子清脆的声音,其间,头上传来了北幸号发出的两声短促的汽笛声,可能此刻刚好与其他船只擦身而过吧。只见足立从昏睡中醒来,突然说道:“对了,松田说以前在哪儿见过你。”
“我?”彰之反问道。
足立点上香烟,悠闲地接连抽了两根。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