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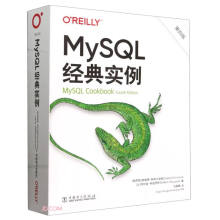
原来西方也曾“山寨”中国!!!
《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中所言的中国风既非单纯的中国制造,也非西方对中国艺术的简单模仿,而是中国元素与西方人中国想象的有趣结合、中国情调与西方品味的有趣结合;它的盛行一时昭示了中国作为历史上曾经强大的国家对西方巨大的影响力——中国艺术和工艺品被看做是一个强大帝国的产物,并且充满了神秘浪漫的东方情调,是那个时代西方人心目中有国际范的奢chi品,拥有它们是个人品味和地位的彰显。而中国元素也成为那个时代西方受追捧的时尚元素,在由不便利的交通所导致的中国进口商品昂贵的价格把大多数渴望追赶时尚的人群阻隔在外以后,精明的商家选择了对中国元素的利用、复制和改造,“山寨”蔚然成风。
《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中的400多幅彩色插图可以让读者遍览席卷西方近一个世纪的中国风所创造的奇幻景观,直观西方“山寨”中国产品的独特视觉形象和美学意蕴,品之令人趣味盎然;而本书作者,英国皇家文学院和不列颠学院院士、当代著名艺术史家休·昂纳更以其典雅的文笔、独到的考查和细腻的分析为读者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段的中国风所表征的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形象的历史变迁,以及其后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可观、可品、可思,这是本书带给读者非常好的阅读体验。
从17世纪始,欧洲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风”。这场中国风发端于11世纪,得到了马可·波罗、圣鄂多立克等曾旅行中国的冒险家们、传教士们的有力助推,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后,从17世纪开始全面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商贾乡绅,都对所谓的中国风尚趋之若鹜;中国风更直接形塑了西方时尚史上著名的洛可可风格。这场中国风在18世纪中叶时达到ding峰,直到19世纪才逐渐消退。华托、布歇、皮耶芒、齐彭代尔、钱伯斯、瑞普顿等著名的艺术家、设计大师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设计师、工匠所创造出的众多中式建筑、艺术品和工艺品为后人记录和保存了它席卷欧洲大陆的深刻痕迹。
作者以史学家的严谨、文学家的细腻笔触和艺术家的敏感梳理了西方文化中中国风的兴起、兴盛及其衰落、流变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诚如作者所言,在19世纪以前的大部分西方人心目中,神州并非真实的场景,而仅仅是一个幻境;虽然不乏中国元素,但像哥特风一样,中国风归根结底仍是一种欧洲风格,它表明的是欧洲人对一个在距离上遥远、心理上神秘的古老国度的理想化的认识和理解,而非某些汉学家所言,仅仅是对中国艺术的拙劣模仿。
《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恢弘的气势、严谨的考察和细腻的分析使其成为西方为数众多的中国风相关著述中的经典之作,至今无出其右。
路易十四宫廷中的中国风
当路易十四决定为他最宠爱的情妇莫内斯潘夫人(Mme de
Montespan)修建一座楼阁的时候,他独出心裁,要采用中式设计。这个小小的开心屋叫作特列安农瓷屋(Trianon de porcelaine),是由宫廷建筑师路易·勒·沃(Louis Le Vau)设计的,于1670至1671年间的冬季在凡尔赛的园林中修建而成。它很快就拔地而起,快得就像是春天的花儿一样从土里冒了出来,而花丛中的它看来就像是一座魔宫。在众多装点欧洲公园、雅致但昙花一现的建筑中,特列安农为其先河。在它的引领下,在欧洲的每一个角落,从皇后岛(Drottningholm)到巴勒莫,从辛特拉到察尔斯科-泽洛(Tsarskoe-Selo),都出现了一大批中式宝塔、网格样式的茶馆、亭子和“儒家式的”庙宇。
1698年出版了一部奇怪的寓言式传奇故事《不是故事的故事:“举世无双”和“仙女的王后”》(Contes moinscontes que les autres: Sans Paragon et la reine desfees )。对于特列安农的构思,它的见解是很奇怪的。笼统而言,该书能让我们了解法国宫廷如何看待中国;具体而言,它能让我们了解法国宫廷如何看待这个建筑。故事讲述的是“举世无双”(路易十四)和“光荣美人”(Belle Gloire,莫内斯潘夫人),一位中国公主。她“是世上无可争议的最美丽也最高傲的公主”。有一次他陪伴“光荣美人”在他园林的一条运河上乘船游览,“举世无双”问她如何看待他奢华的领地。公主冷冷地回答说,在中华帝国,财富是寻常之物,以至于她的父皇总是偏爱朴素、洁净的房舍,而不是富丽堂皇的宫殿。行至运河终点的时候,因为一直想取悦公主,“举世无双”便跃上河岸,用他的权杖在地上敲击了三下。眨眼间便出现了一座陶瓷城堡,苗圃环绕其间,茉莉花香四溢,小型喷泉流光溢彩。“整个建筑”,这个无名作家断言道,“产生了能够见到的最为令人心旷神怡的效果”。
虽然说起来特列安农瓷屋好像是从巍峨的南京陶瓷宝塔中汲取了灵感,但它却只有一层楼高,外部涂层为彩釉色,而不是陶瓷,瓷砖是在代夫特、纳韦尔、鲁昂和利雪(Lisieux)的陶器场里制作的。这种容易渗水的材料无法承受冬季的冰霜以及后来证明高得惊人的维修成本。部分是出于这个原因,部分是因为(我们也可以猜测)曼特农夫人接替莫内斯潘夫人(该建筑就是为她修建的)成为国王的新宠,特列安农便在1687年被拆除了,这距离它变戏法似的出现也仅仅只有17年的时间。不过,关于它的模样,我们还是可以从同时代的描述和版画中获得一点印象。
据费利比安(Félibien)对凡尔赛的描述,特列安农是“一个建筑精美的小宫殿”。它由一个大的和四个小的环绕庭院的平房构成,全部都用彩釉色装饰而成,吸引着每一个游客的目光。“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歌舞升平的宫殿吧”,诗人丹尼斯这样写道:“你可看见它上面堆满了彩陶,各种瓷罐和各式花瓶,这让它光耀寰宇。”檐口和主体建筑的转角处都是使用陶瓷瓷砖点缀的饰板。上横梁上有栏杆,上面摆放着花瓶,房顶用彩色瓦片进行装饰,表现的是各种各样的场景——爱神追逐动物,一个个花瓶,还有各种鸟儿,它们全部“都以自然的方式呈现出来”。室内,全是蓝白两色,这是当时认为赏心悦目的中国式色调。大多数的墙壁都铺的是极为光滑的白色石膏,上面的装饰物都用蓝色挑色处理,中央沙龙的檐口和屋顶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装饰的。“全部都是用源自中国的装饰风格完成的”,再引一次费利比安的原话吧。这个爱巢是完全用中国风格装饰而成的,座椅上面都罩着蓝白相间或者金银相间的布料。卧室被不太相称地叫作“戴安娜的卧室”。床本身装饰的是欧洲风格的爱神,但是幔帐使用了带有蓝色、亚麻灰色、金黄色和银色条纹的白色塔夫绸,而桌子和摆设用的小圆桌则被涂成蓝白相间的瓷器式样。财产目录清单显示,最后一件带有异国情调的东西是中式的花朵绣品,可能它们让原本有些冷冰冰的装饰格调增加了一丝欢快和温暖。
费利比安说,对中国的迷恋在这一时期的法国宫廷风靡一时,而这座建筑正是受到了这种迷恋的启发。也有人暗示,说亭阁的布局模仿了北京皇宫的中央庭院。
特列安农瓷屋能够说明17世纪晚期法国宫廷盛行的对中国艺术的态度。17世纪90年代,当李明神父(Père Louis le Comte)从北京发回报道的时候,他无疑是在为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代言。他说:“中国人对于所有艺术的见解都是有缺陷的,这在他们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中暴露无遗。”虽然他发现中国的建筑物都华丽而俗气地装饰着真漆、大理石、瓷器和黄金,但他断言说:“房间设计不妥,装饰品凌乱无序,整体上缺乏我们的宫殿表现出的融美与方便为一体的那种一致性。一言以蔽之,可以说其缺陷是整体性的,这导致中国的建筑物让外国人看不顺眼,也必定会让任何一个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建筑有一点点认识的人感到不悦。”这种缺陷决不允许出现在特列安农瓷屋上,它就像彩釉色瓷砖、青花图案以及刺绣幔帐所能产生的效
果那样,华丽而富有异国情调。
在关于中国风格和中国样式的参考文献中,可以看到大量的17世纪的财产目录清单以及对法国皇宫所做的描写。因此在多卷本的《财产目录总清单》中,才有了柜子、桌子、屏风、椅子、摆设用的小圆桌、幔帐以及室内装潢等的描述。不幸的是,还没听说这些中国风的东西有哪一件遗存了下来。要说明它们怎么消失的还是有一点困难,因为不太可能做出一种假设,说所有的皇宫中中国样式的家具和纺织品都因事故而毁,在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或者因为后来鉴赏情趣的变化而遭到抛弃。
不容置疑的是,国王和他的大臣们都是中国的和其他地域的东方物件热情的收藏家——刺绣的丝绸幔帐、真漆柜子、金丝细工饰品(这尤为国王和他的母亲所喜爱)以及青花陶瓷瓶。的的确确,这一时期的财产目录清单和文献表明,在17世纪70年代初,宫廷受到了那阵中国热的严重影响。要解释这个风尚就要提出好几个理由。
首先,始终都存在一种对富丽堂皇、异国情调的渴望,而这在东方的物件中得到了满足。这是因为,即便凡尔赛宫的陶瓷瓶使用了厚重的白银或者铜锌锡合金底座,即便真漆柜子放在了炫耀富裕的镀金的古典架子上(其中一个甚至装饰着赫尔克里斯丰功伟绩的白银浮雕),但是它们仍然显得无比奇特。它们也给原本可能太过严肃的装饰格调带来一丝明快,并给阿波罗神般的国王路易那香火弥漫的房间带来了一阵愉快的幻想。除此之外,它们还具有联想的价值,而刚好宫廷又酷爱寓言,并且借象征主义缔造了繁荣景象,因此这一联想价值很容易为宫廷所赏识。因为,不管有多么奇特,多么反古典,中国艺术都被看做是一个强大帝国的产物。而在每一幅油画和几乎每一种装饰手段上都夸耀路易十四如何伟大的凡尔赛宫,整个布置大气磅礴,设计精巧,包括在其中的东方物件兴许就是要暗示这位君主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当他盖着印度被子卧于床榻上的时候,或者当他用镶嵌精美的青瓷碗小口小口地品尝肉汤的时候,或者是当他在皇家药房用青花罐服药的时候,抑或是当他为晚上的化装舞会穿上东方服饰的时候,这位太阳王(le Roi Soleil)兴许也把天子看成了阿波罗或者亚历山大之外的另一个角色。
然而东方物件绝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产生的联想才让法国宫廷着迷的。它们在路易十四和他的朝臣中之所以受到喜爱,是因为还存在一个经济原因:虽然价格对于私人收藏家来说高得离谱,但是国王还是可以通过印度公司得到相对廉价、上等的东方漆器。恐怕下面的事情并不是巧合:当凡尔赛宫厚重的银质家具进入熔化炉、用以支付奥格斯堡盟国之战的时候,真漆家具的供货量却增加了。另外,国王可以命令全欧洲技艺最为精湛的工匠(哥白林厂的那些工匠)生产出跟东方进口的家具同样富丽堂皇、同样奢华并且(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具有同样联想价值的家具。因此就有了数量巨大的东方样式和中国样式的室内陈设品,以及其他那些17世纪末在凡尔赛宫和其他法国宫殿里看到的物件。
从宫廷开始,中国风的时尚传播到都市和外省。早在1673年,仅仅是特列安农瓷屋完工两年后,《风流信使》(Mercure gallant)就报道说,大臣们纷纷仿效国王,甚至于各地中产阶级也把小木屋改造成了开心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个时尚就传到了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但不幸的是,这些17世纪的特列安农瓷屋没有一个留存下来,有关它们的版画、图画或者描写也没有一样流传到今天。因而,它们在中国风历史上的作用依然是模糊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