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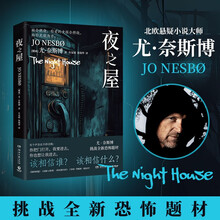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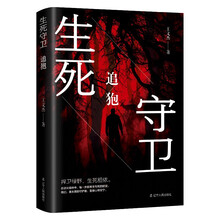




人心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可怕,生命比我们以为的还要脆弱。
一个狱警殴打罪犯,沦为阶下之囚。
一个辅警壮烈殉职,没有得到功勋。
师徒案、哭坟案、拉拉案、硫酸案、耳坠案、韭菜案、盗尸案,通过一本卦书,起底暗数杀人事件。
暗数,即犯罪暗数,又称刑事隐案,是指该“罪行”已经发生,但因各种原因,隐匿在官方正式的犯罪统计之外。
蒋鹏年幼丧父,考刑警没过,做了狱警,办案中因过失被停职。他在狱中无意中获得一个笔记本,里面写满了服刑人员未供认过的暗数,恰好有一个人名是蒋鹏小时候就听过的,而且跟自己父亲的牺牲有关。
为找到父亲死亡真相、打击刑事隐案,蒋鹏走上了“挖罪”之路,可笔记本中深埋的罪恶,已远超他的想象。
父亲背后的秘密,是他通往死亡的大门。——师徒案
她爱自己灵魂里的他,却让另一个他走上了连环杀手之路。——拉拉案
下岗之时工友交恶,尘封往事浮出水面,其中暗藏命案玄机。——硫酸案
一副耳坠,五条人命,只因为私欲的贪婪和亲情的恶意。——耳坠案
2012年冬天,我进了江浦监狱,一待就是两年。
别误会,我没犯事,是去工作。或者说,是去实现梦想——我想成为一名作家。
有些朋友乍一听不太相信,他们觉得监狱里大概只有两种人——罪犯和狱警。其实,还有很多职工岗。比如我,岗位是新闻编辑。每个月,监狱文教楼的演播厅都会播一期半小时的视频新闻,片子由我来审核剪辑。
我大学在鲁迅美院读油画专业,原本要做画家,临毕业那年,读了几本犯罪小说,就魔怔了似的,自己也想动手写。
毕业后,我无心画画,蹲家里半年码了三十万字,编了个长江沙霸江湖的故事,签给一个无良网文平台,只拿到六百块稿费。后来,书名和署名也被平台改了。
我创作冲动依然旺盛,整天闷在屋里酝酿下一部作品。换在父母眼里,我却是彻底废了,要带我去看心理医生。一天晚上,父亲拍桌子发完火后,突然生出了一种情绪。他说,不指望你有大出息,但得有个稳定的工作。你去那儿干轻巧活儿,没事想写什么还能写什么。
那儿,指的就是江浦监狱演播厅。
父亲在监狱管理局有熟人。他看不下我整天在家闲逛,说二十五六不工作的男人都是“腌菜”。他宁愿坏了一辈子的清廉,替我打听了这份工作,也不希望自己儿子变成“无事佬”。
我一听急了,这是送我蹲监啊。转念一想,又立马答应。不管父亲是让我收心,还是送我个铁饭碗,这差事对我的写作都是好事——能进“监狱”,必定能见识到“风云”。
只是未曾想到,我在演播厅无所事事了十几个月,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犯人的监管区都没机会进去过。
直到2014年秋天,我遇到二监区的一个重刑犯。
那天,警官学院入监做警示教育,专门找了些曾是公职人员的犯人演讲。教改科来了一个科员跟拍,叫李爱国。他人细长精瘦,一身警服像挂在两根筷子上,扛着索尼摄像机到处走。
李爱国到演播厅借板凳,我正闲着无聊,帮他接过机器搁桌上,跟他请教摄像技巧。一聊才知道,我平时审播的狱内新闻,都是他采编的。我问他:“平时拍摄方便带上我吗?我帮你扛摄像机。”李爱国摇摇头,左右手交叉,捏了捏自己的肩膀,“是驼了,这一大块。”
我绕到他身后,惊呼道:“再不换人扛机器,以后出毛病了,工伤都算不上。我有一亲戚,跟你一样,脖颈后面拱出来一块肉,后来压迫神经,做手术花了好几万。”
他立刻笑着拿起摄像机塞到我怀里,“警示教育马上开始,你帮我扛一会儿,我教你一些厉害的拍摄技巧。”
我扛起摄像机,和他去了三楼会场。一百多平米的会场,坐满了警校学员,我扛着摄像机站在过道中间。讲台长条桌中间坐着七八个领导,右侧放了一根话筒架。一个驼背的中年囚犯站台上,正对着话筒发言,讲得声泪俱下。听他自述,曾是某县级市的政法委书记。
中年囚犯正讲着,有个青蛙眼狱警领着个犯人站到了我身后。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犯人体型健壮,个子比我高点,一米七八的样子,神似反町隆史。狱警递他一张纸,说:“稿子你不愿意写,我帮你写好了,给个面子,上去读一下。”
那犯人拉着脸,很不情愿的样子,回道:“我喉咙发炎,扁桃体还肿着,没法发言。”
我听着觉得奇怪,哪有犯人敢推诿狱警交办的事。
狱警又劝他:“这是监狱领导交代的,看我们以前同事一场的分上,别给我添乱好不好?别觉得这事丢人,你读一下,算你认罪悔罪态度不错,后面给你申请加分,能多减几天刑。”
这个犯人不说话了,举着纸看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纸面,“就说这一件事。”
大约十分钟后,台上的中年犯人鞠躬退场,“反町隆史”上去了。我往后退了几步,扛着机器保持正向姿势,头歪过去问青蛙眼狱警:“这犯人以前是警察?”狱警扫我一眼,“嗯”了一声。我忍不住又问:“他犯了什么事?”青蛙眼没说话,专注看着台上。
我赶紧回头,把摄像机对准“反町隆史”。
“我叫蒋鹏,生于1990年,是警官学院2012届的毕业生,在江浦监狱当过实习狱警,工作期间因与犯人约架被解聘。我奉劝各位在座的警校学子,不要跟我一样鲁莽冲动……”
后面就是一串反省的套话。他一口气念完,台下的警校生却冒出一片嘘声,很多人交头接耳。有男生小声嘀咕:“明显避重就轻,他弄死人的事不提,只说打犯人的小事。”
两个女生扭着脸反驳:“什么叫弄死人那么难听,那是意外事件好不好?蒋鹏学长已经很惨了,你别再落井下石了。”
台上的领导抓住话筒咳了几声,底下安静了。校方领导想让犯人再讲一会儿,教改科科长看了看时间,回绝了。众人散场,李爱国拿回摄像机,看了看我拍摄的视频,说:“还挺不错的,很有天赋啊。”
我问他:“那事答不答应?”李爱国摆着手走远,说以后再聊。
没过两天,李爱国又来了。
监狱搞“创建”,领导点名批评狱内新闻没新意,太形式化,创新任务交给了李爱国。我拉他坐下,闻见一阵虎皮膏药味,故意拍拍他肩膀,说需要帮忙,尽管招呼。
李爱国扭了扭脖子,耸了耸肩,说走一步看一步,敷衍敷衍,能对付就对付。我见缝插针,问他还记得上回那个蒋鹏吗,那个当过狱警的犯人——采访他啊,现成的创新节目。
我提出这个建议,事先是打过主意的。上回在警示教育会场,蒋鹏一开口,我就预感到,我要的“风云”来了。
李爱国想了一会儿,说不行,他那事儿敏感吧。我说咱这儿又不是电视台,你想不想创新吧?李爱国说也是,教改科本来就有权采访——他咧嘴一笑,看着我,“想不想学点更深入的拍摄技巧?”
12月底,李爱国领着我去了二监区。
当天气温很低,路面结冰,他穿着冬装警服,两张黑色毛领紧紧包裹着细长的脖子。我扛着摄像机小心翼翼跟在后面,胸口挂一张教改科特批的采访证。
二监区在监狱东面,一栋四层白楼,新建了院子,大门安装了指纹门禁系统。李爱国走到门口,掏出对讲机呼道:“二监区值班民警,二监区值班民警,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几秒钟后,对讲机回话,立刻有狱警打开了门禁。狱警不是别人,就是上次见过的青蛙眼。李爱国出示了采访批准条,我们进了监区。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监管区域。
监区走廊很长,水磨石地面,青蛙眼走在前面引路。右手边是监舍,二十几间监舍里挤满了囚犯,人挨人站床边。他们穿着蓝色冬装囚袄,剃光头。出工哨一响,囚犯挨个报数,排着队走出监区。
到了监区大厅,青蛙眼指着西南角一个棕色木质警务台,让我们在那儿等着。出工队伍排成长龙,囚犯们陆续从我眼前经过。他们大多数人缩着脖子,双手插在衣袖里,宽大的囚袄是七八十年代军大衣样式。蒋鹏排在队列里,等他走到大厅中间时,青蛙眼冲他喊道:
“115,出列。”
蒋鹏站姿笔直,双手紧贴裤缝,大喊一声“到”,朝我们走来。走到距青蛙眼一米开外的位置,他停下来,双手扶膝,左腿后撤,蹲了下去,后背打得挺直,胸肌快要撑开棉袄,一看就是练过的。
按狱规,犯人与警官交谈,必须蹲姿并保持一米距离。
青蛙眼清清喉咙,故意放大声调说道:“蒋鹏,教改科准备给你做个节目,配合好了,后面对你改造的方方面面都有好处。”
“报告干部,我拒绝采访!”蒋鹏声音浑厚,大厅连响两次回音。
李爱国瞪着眼睛,脸色铁青。青蛙眼朝我们走过来,面露难色,让我们先回去,“我再给他做做思想工作,要是他确实不接受采访,那也没辙。”
回到演播厅,李爱国略显沮丧。我问他,你刚才看出猫腻没?他耸耸肩,问什么猫腻。
“那青蛙眼和蒋鹏演戏呢。”
他点点头,又耸耸肩,说那也没办法,人家不肯配合,也没法强求。我说不能就这样算了,蒋鹏不让采访,咱们可以先采访青蛙眼。
监狱食堂旁边有个小饭馆,晚餐时间,我定了一桌菜,点了几瓶啤酒,李爱国去食堂门口堵青蛙眼。菜还没上齐,李爱国拽着青蛙眼进了饭馆,两人互相恭维,李爱国喊青蛙眼“张队长”,青蛙眼喊李爱国“李科长”。
我立刻迎上去,跟着恭维几声。等入了座,菜上齐,走了三四杯酒,客套话都说腻了,李爱国举起酒杯说:“张队长,这么突然请你吃顿饭,还是那事,务必帮忙做做那个犯人的思想工作。”
青蛙眼给李爱国敬酒,两人干了一杯,说:“李科长,蒋鹏性格很倔的。他不想做的事,软硬都没用。”
我问:“张队长和蒋鹏原来是同事是吧?”
青蛙眼点点头,“他原来是警校的优等生,搏击冠军。板上钉钉考刑警,结果当了狱警。冠军脾气,把一个刺头犯揍了,断两根肋骨,狱警也当不成了。”
我敬了青蛙眼一杯酒,说打个架也不至于脱了警服换囚服啊——是不是还有戏?
青蛙眼酒量不行,几杯酒下肚,脸色通红润亮,开始说车轱辘话,有戏,有戏。不过不是戏剧,是戏弄,戏弄呀。
青蛙眼已经一副不能再喝的样子,我捅了捅李爱国。李爱国搭着青蛙眼的肩膀,“老弟,上上心,试试看,成不成再说。”
青蛙眼摇摇手,蒋鹏不想别人知道他爸的事,所以,没用。
我说这样,请张队长明天给我们看看蒋鹏的判决书,我们深入了解了解,回头再找他聊一次,实在不行就算了。
青蛙眼较劲似地点头,说:“行行行,你们不信我没关系,我能配合的尽量配合。”
第二天下午,李爱国夹着几页A4纸来了演播厅。他把纸递我,说:“上面都是一带而过,你看看。”
我翻看纸页,判决书上写蒋鹏因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脱逃罪,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6至8年,鉴于其有重大立功表现,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我仔细地把判决书上蒋鹏的犯罪事由看了一遍,激动地看着李爱国。
“太有戏了,绝对创新。你在科室工作,能不能查到他当狱警时打犯人那事。”
李爱国说:“蒋鹏是2012年入职的,我在单位待了十三年了,上上下下,小年轻老干部谁不认识,唯独对他毫无印象。我一早就去狱政科翻档案,他总共没实习几天,就被解聘了。我找他当时监区的教导员问了,他打的犯人叫苏小杰,你猜他是谁?”
我摇摇头。
李爱国伸着脖子问我,1999年的“9•21”持枪抢劫案听过没。
我还是摇头。
李爱国缩回脖子,“也是,你当年还小。那案子真是轰动全省,出事后,我家楼下的银行,好多天没人敢取钱。”
1999年9月21日到2000年元旦,四个云南文山人从云南一路抢到江浙沪地区,专抢取完款刚出银行的储户,每次只开一枪,打头,不留活口。四人人手一把54式手枪,一共作案11起,枪杀10人,重伤1人,涉案金额9万7000余元。
警方抓捕那天跟四人发生枪战,当场击毙了三个,有一个送去医院后救活了——就是苏小杰。
李爱国说,苏小杰是四个案犯里最小的,当年未满十八周岁,没吃枪子,判了无期。
我问他,苏小杰在哪个监区服刑。
李爱国迟疑片刻,说也在二监区,那里都是重刑犯。
下午两点多,李爱国带我去二监区找苏小杰。犯人们都在操场上除冰,副教导员是个面善的小胖子,他把苏小杰喊到我面前,自己和李爱国聊球赛去了。
苏小杰高个,额头短,眉毛粗,厚嘟嘟的嘴唇干裂了,翘着皮。他很健壮,穿着蓝色囚袄,敞着胸襟,手上拿着一把铁锹。乍一看,有股邪劲。
我往后退了退,副教导员回过头,指着他说道:“苏小杰,把劳动工具放回原处,蹲下说话。”我找来两个小木凳,递给苏小杰,问他今年多大。
他接过凳子,愣了一会儿,说:“过三十了。”
我问他:“记得蒋鹏吧,跟你打架的那个狱警。”
他搁下凳子坐下,使劲点点头,说“当然记得,他那不是打架,是要弄死我”。
序 章
第一案 师徒案
第二案 哭坟案
第三案 拉拉案
第四案 硫酸案
第五案 耳坠案
第六案 韭菜案
第七案 盗尸案
大结局 暗数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