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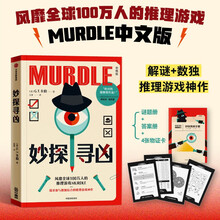



《一朵桔梗花》获推理作家协会奖
《情书》获直木奖
《宵待草夜情》获吉川英治文学奖
《变调二人羽织》获幻影城新人奖
东京世田谷一家医院的院长被一通电话叫出了门,再出现时已是一具尸体。院长被利器刺中,脖子上绕着两圈铁丝,死状凄惨。更让警方疑惑的是,死者身上穿着一件医用白大褂,而且应是死后凶手特意套上的。
凶手为何在行凶后还费事地为尸体套上白大褂呢?就在警方展开调查的同时,又一名医生失踪了……
本书包含九个短篇,展现出连城三纪彦笔下美丽却又残酷的世界。
两张面孔
电话铃似乎响了。
我拧紧水龙头,让水声停下,仔细确认声响。尽管浴室门紧闭,声音很轻,但的确是电话铃声。
现在应该已经过了半夜两点--这时候会是谁打来的呢……
在鸦雀无声的深夜一隅,那金属铃声听着就像一种未知生物的痛苦喘息。
我用毛巾擦擦沾湿的手,走出浴室。隔着客厅门传来的铃声在昏暗的走廊回荡。这栋屋子的二楼卧室与一楼客厅都装了电话,卧室的电话只有弟弟和十分亲密的朋友才知道号码,是完全私人用的。想不出谁会打到客厅的电话上去。
电话不依不饶地继续响着。我犹豫了一小会儿,还是提起了听筒。铃声戛然而止,取代它的是一个男人低沉的嗓音。
"是真木老师家吗?画家……真木祐介老师家吗?"
是个陌生的嗓音。
"我是新宿S署的人。您是真木老师吗?"
"是的……"
"深夜突然来电很抱歉,是有关您太太的事情……太太的名字是不是念'qi'子呢?是'契约'的'契'字吗?"
"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警察居然在深更半夜打电话来问契子的事。更惊人的是,我显得格外冷静。身处夜间的凉气之中,连心态也变得冷淡了。
"您太太现在是否外出了呢?"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于是用近似反问的含糊语气回应他:"唔嗯……"
"您知道她去哪里了吗?"
"嗯,我没问她具体要去哪儿。"
刑警的声音在听筒深处消失了片刻,之后再度响起。
"是这样的,新宿三丁目一家旅馆发生了杀人案,我是从案发现场打电话给您,被杀死的女子似乎是您的太太。"
"契子她?这不可能!"
我不由得怒吼般地大喝一声。
"因为被杀害的女子手上有一封要寄给您的信件……读过内容之后,看上去是您妻子写的……您太太出门时是不是穿着深蓝色结城绸①的和服呢?腰带是灰色的,上面有黑色四叶草的图案,只有一片叶子是粉红色的……"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她确实是有一条那种图案的腰带……可是……"
听筒深处传来男人的沉吟声:"看来是您太太没有错了。很抱歉,能请您火速赶到这里来吗?"
我已经不记得是何时挂了电话。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用震颤的双手按着听筒,像是惧怕那男人留下的余音。也许是因为过于惊愕,意识融入黑暗中,变得稀薄,思绪也变成原地打转。那个自称警察的男人最后匆忙说出的话语中,我只记得"从新宿御苑大门前数起的第三条路"这句,还有"帕德"这个闻所未闻的旅馆名。"帕德"的发音怎么都听不清楚,我还反复问了好几次。
我本想这也许是个骚扰电话,但他的说话声背后的确传来了警笛与匆忙的脚步声,似乎飘荡着命案现场的气息。
但这是不可能的--契子在新宿的旅馆里被人杀害,肯定是哪里搞错了。总之还是去现场看看为妙,这么一来就能轻松化开这个无聊的误解。
然而,身体却不肯随我的想法而行动。我瘫在沙发中,任身体下陷,只是迷茫地望着墙上的画。是一个女人的肖像画。妻子契子--刑警方才宣称死亡的女人,她的脸在一片幽暗中如幻象般浮现。说是脸,其实看上去更像是渗入墙壁的一摊污渍。我全身发颤。为了让手上的痉挛停止,我用全力握紧一只花瓶,朝肖像画扔了过去。花瓶重重砸在画中女子的脸上,又掉落到地板摔碎了。
听到响声,我才回过神来。玻璃花瓶摔得粉碎,而画中女人的脸庞却毫无变化,只有被水打湿的头发像活人似的扭曲起来。但那张脸依旧纹丝不动。
不会有错,这个女人是绝对不会死的--
在突如其来的刺激之下,所有记忆都回到了空荡荡的脑海中,我就像个初愈的失忆患者一样恢复了神志。我将视线从画中女人的脸上移开,来到走廊。
走廊尽头的浴室还亮着灯。我为该去浴室还是去二楼犹豫了一瞬间,双腿擅自选择了上楼梯。
这是今晚我第四次爬上这段楼梯。爬上楼梯的第一扇门就是卧室,我也是第四次打开这扇门。
卧室里很暗。门旁的开关一周前坏了,还没修好。我从裤兜里掏出火柴点上。指尖的光芒让暗夜微微泛白,微弱的火苗照出乱糟糟的床铺和塞进壁橱的地毯上那熟悉的几何图样。明明早已再熟悉不过,这奇妙的形状却让我辨别不出是几边形。
"不可能……"
我用不似自己的声音低声念叨。
契子在新宿一家我都没听说过名字的旅馆里被杀,这种事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契子刚才还躺在这块地毯上呢。是我杀的。是我在这间卧室里亲手杀死了她。而电话铃声响起时,我才刚刚将尸骸埋在后院,正在浴室清洗沾满泥巴的双手。
拿着火柴、融化在黑暗中的这只手上,还残留着掐住脖子时,妻子--契子身上最后的体温。
1
四小时后--
隆冬的黎明,我驾车疾驰在冻出一层白霜的高速公路上。我正从新宿的案发现场赶往另一个现场,也就是位于国立市的家中。晨光渐渐给周遭的景物描上一层轮廓,脑海中的混乱思绪反而愈加纠缠,成了一团暗影。
或许是同名同姓,又或许是持有妻子要寄给我的那封信的女人偶然被杀了--四小时前,我怀着这种乐观的心态从家里出发。
到达新宿时已经过了凌晨三点。红色的霓虹灯管组成了英文店名"帕德",那过分鲜亮的色彩反倒让旅馆整体显得昏暗。这也是门口唯一的色彩,一眼就明白是那种旅馆。
一旁停着警车,大门口被媒体记者挤得水泄不通。被誉为给战后绘画史涂上一抹独特色彩的知名画家之妻,在这种偏僻又淫靡的地方被杀,的确称得上是大丑闻。闪光灯朝着我连连闪烁,麦克风蜂拥而至。
似乎是打来电话的那名刑警将我从旋涡中救出,领我去了现场。
现场位于旅馆四楼的四○二室。
从踏入那房间的第一步起,我就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混乱。房间的整体印象与我自家的卧室--也就是我真正杀死妻子的现场堪称酷似。尽管没有壁橱,但从床的位置、房间面积、窗户大小,到窗帘与地毯的颜色,全都一样。就算细节处有所差异,但当它映入我的眼帘时,真就仿佛是把我杀妻的卧室直接搬到了新宿后巷的旅馆中。
产生这种错觉可能是因为看到横陈在床上的雪白裸体的女子尸骸。她的脖子上缠绕着束带绳①,床脚边丢着一把沾有新鲜血迹的扳手。刑警解释说,凶手是用束带绳勒死女子之后,再用那把扳手将其面部砸烂了。
当白布从尸体脸上掀开时,我不禁想吐,用手捂住了嘴巴。并非是形如碎土的那张脸令人作呕,而是异乎寻常的相似感让我感到晕眩。一切的一切,都昭示着我在当晚的所作所为。我在一小时前才刚刚用后院的泥土隐藏起来的罪行,居然在眼前得以重现。我也是用束带绳勒死契子后,用扳手砸烂了她的脸。
"脸已经成了这样子……请问,能通过其他部分来判断吗?"
我只能回答她是我妻子。身体的整体印象与头发的长度都与契子一致,脱在床脚边的和服与漆面手提包我也确实记得。
"这枚戒指是?"
尸体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翡翠戒指,底座是少见的十字形状,吸引了刑警的目光。
"是四年前结婚时我买给她的。是我亲自设计,特地请人定做的。"
刑警想把它摘下来,可戒指牢牢嵌在肉里,只是稍稍移动了一点。指根处留下了鲜明的痕迹,说明死去的女子戴这枚戒指已经有些年头了。
于是乎,这个女人毋庸置疑就是契子。
完全搞不明白。我走出家门,在深夜的高速公路上驱车疾驰,可不知不觉又回到了自己作案的犯罪现场。几小时前那场令脑海中充斥着腥臭味的犯罪,像是被一面不可思议的镜子映照,我又站在了另一边的杀人现场。
"您看看这封信。"
刑警用戴着白手套的手递来一个信封。正面写有国立市的住址和我的名字,而背面只写了"契子"两个字。透过笔迹也仿佛能看到契子的面容。
两张面孔
来自往昔的声音
化石钥匙
奇妙的委托
鼠之夜
二重生活
替身
魂断湾岸城
敞开幽闭之门
这是一本必须读的短篇杰作集。
--绫辻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