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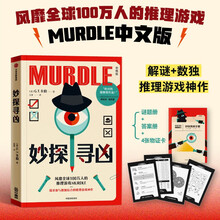



疲惫硬撑时,靠什么抚慰和驱动自己?韩寒「ONE · 一个」重磅心理悬疑小说,TVB学霸演员吴沚默力作,72万次高赞阅读。女性实现独立,得克服多少障碍和恶意?《生吞》郑执,王祖蓝、郑丹瑞一致推荐
【编辑推荐】
◆ 多声部成长故事,给心理悬疑注入新活力:女性之间的亲情与爱,有着令人心惊的坦诚与真实
三代女性的人生,女性群体命运的缩影
人人极力赞美母爱和友谊,于是你拒绝相信光亮下的阴暗与复杂……
◆ TVB学霸演员、香港浸会大学高材生吴沚默,集灵性感悟与理性思考的跃进之作
28岁,身边的姑娘不是嫁人,就是已经有了很好的事业发展,或者至少在静好岁月中自得其乐。我都不是。我想思考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 吴沚默
◆ 用港漂经历审视自身,映照女性人生阶段性的彷徨
成熟和稚气,不必二选一。二十八九岁,睡不够,粘不好假睫毛,买的股票总在跌……没关系,只要不再逃避和放弃,就能从每一次沮丧的原地跳出去。
◆ 《生吞》作者郑执,香港艺人王祖蓝、郑丹瑞一致好评力荐
◆ 韩寒监制「ONE · 一个」高赞心理悬疑小说,阅读累积72万次(2020年4月)
◆ 那些叫“往事”的东西为何持久?每一次疲惫硬撑时,要靠什么抚慰和驱动自己?
我叫辜心洁,29岁,是个女演员。没有代表作,半年没开工。正想找人分担房租时,一个叫小陆的女孩不请自来。小陆热情,在“博慈之舟”精神康复院做社工。相处不到一个月,我发现:我的事情她都知道。而我记忆里的家族旧事——母亲出轨、父亲死亡——也因为她,拼凑出了完全陌生的版本。
在“博慈之舟”,我见到一个叫丁思辰的疯女人。她在福利院长大,17岁时考上卫校,并在那里遇到我的父亲辜清礼,二人常常在河边私会……18年前,丁姨本可以出院,但那天下午我母亲去看过她……
“你送的不是客人,是亲人。最早是外公,然后是爸爸,现在是外婆,还有一个人……”
《风暴来的那一天》精彩书摘
夜晚终于降临。
那是一条河,碧绿悠长,如同很多电影里出现过的乡愁一般,在她梦里流向雾气隐藏着的远方。
河边的少女解开她的头发,走入河水中间,衣服散落河面,如同五色莲花。她走了很长很长的路,赤足走过田野阡陌、浓密得没有缝隙的森林,才走到这里。她忘记了疼痛,也忘记了血管里流淌着的液体正在等待一个出口喷薄而出,她的身体苍白得像一条冷血的鱼,内里却沸腾着。
水猴子什么时候来?
很久很久以前,照顾过她一段时间的老人曾讲过这样的传说,为了不要让小孩子跑到水边。老人说水里有一种水猴子,会把人扯入水底,从此沦为它的同伴,永远待在阴冷的水下。
此刻,她在等待着幽深的水底,有这样一双光滑冰冷的手,轻轻触到她赤裸的背部,然后两只手一起,捉住她的腰,用力扯向无可穿透的大河深处。
这是她最快乐的时光。
------------------------
自从租了这个海边郊区的两房小户型,我就没有接到任何工作。
对一个女演员来说,半年的假期的确有点太多,但我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甚至连银行户头里还剩下多少钱都忘了。每天睡到中午,打开冰箱胡乱煮食,下午去附近的海边公园游荡,坐在凳子上看一本翻过很多次的小说,然后在日落的时候去超市买食物。
晚上我会上网到很晚,有时困到直接趴在桌子上睡着。手机里堆积了两屏以上的未读短信,对那些不靠谱的试镜邀请,已经懒得去分辨筛选。经纪人似乎已经放弃了我,从她半年没有给我发任何通告就能看出来。
作为一个 29 岁仍然没有代表作的女演员,我基本上也没有了什么走红的可能。我放弃了自己,我知道。但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不卖身,没有对不起当年读戏剧社表演训练班时看好我的那个女老师。我其实只是想好好地活着而已。但直到有一天,我从桌子上醒来,看见前一晚电脑的浏览记录里,净是些“如何无痛自杀”什么的,确实有点被吓到。我不想被人发现残缺腐臭的尸体,因此成为一则社会新闻,虽然这也可能是我演艺生涯开始以来唯一一则新闻,呵。
想想都觉得丧。
此时的我坐在街区公园的椅子上,读着那本读过十几遍的《红楼梦》。这整个阅读动作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那些文字也是。书里古代的女士们和我一样,百无聊赖地生活在巨大的园子里。但这样的生活毕竟有期限,因为总有一天她们会长大嫁人,之后的日子可谓忙而热闹,运气不好的就会难产而死。命运自然有惊心动魄的安排,我羡慕起书里的人,因为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我还要持续多久。好在胡思乱想结束之后,天通常也就暗了。
抬头看见海好丑,就算搅拌了夕阳也那么丑。就这样抱着书走回家。路过一家尚未关门的地产公司,走了进去。
我想出租我家其中一个房间。
我这么想,大概是为了在我万一真的死了的时候,至少有个人能快点发现,让尸体不用发臭吧。但也许,我只是为了找个人来分担一下房租。地产公司的小姐只是笑了笑,抱歉地说,我们没有办法哦,我们只能做整套房产的业务。
于是打道回府,泡了个面当晚餐。有了昨晚的经历我不敢再上网了,在昏暗的客厅里吃泡面,也没有打算开灯开电视。就在外面的黑暗要吞没一切时,手机铃声响起。
记不清有多久没有接过电话,又掐断了多少电话。总之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巨大尖锐的声音,经过短暂的(也可能是很长时间的)茫然,我最终拿起电话。
电话那头是个女声,尖尖奶奶的,听起来像是中学生。
你好,请问你是租房吗?
我愣了一下,印象里没有在网上挂出任何信息,就连这个念头也不过是我数个小时之前才突然升起的。 是……吧……
那你方便让我今晚来看看房间吗?你住翠园 2 期 5 栋 603 ?
我又愣了一下:对。
你今晚在家对吧? 是……当然,半年来其实我每晚都在家。
那我们等会儿见,bye !她果断地挂了电话。
一个小时后,她出现在门口。短发蘑菇头,小小一只,不仅声音像初中生,样子也像。
Hi !我站在门口和她打招呼。很久没有和超市收银员之外的人说过话,这让我听起来可能有点过分热情。
想起应该请她进家门,于是热情地一把将她拉过来,岂料她实在太轻了,我的力道有点过猛,一下把她拉到怀里,两个人都有点尴尬。当她扭头向周围看时,发出了惊叹。
哇,你家好……空旷……
她大概不知道现在小区的垃圾房,几乎已被我刚刚丢掉的垃圾塞满了吧?此刻的我像一个生活在雪洞里的禁欲系女强人,可一个小时前,我还是一个在黑暗发臭的垃圾堆里胡乱吃着泡面的死宅干物女。这是演员的自我修养。
她如同一只敏捷的小猎狗一样迅速参观完了两个房间连同卫生间、小露台和开放厨房。然后跑回我面前,抬起头问我,请问房租多少?
6000。
啊……她低下了头。
一人 3000,我赶快解释。
她扬起头来对我笑了笑,露出小虎牙 : 早说嘛!
她在那个大双肩包里翻找了很久,拿出两张手写的合约要我签上,大概就是房子租给她了就不能租给别人,然后从包里翻出一沓钱递给我。
干吗?我有些惊恐。
定金啊,不是三个月房租吗?
不用不用,我摇手。
不用定金?她盯着我看,然后点点头,宣布似的大声说:
那我明天搬过来吧,先走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就跟我握握手,一溜烟消失在楼道。
就这样,在她离开之后很久,我还在原地发愣:我究竟干了什么?我是交不起租金了,还是无聊到发神经了,为什么会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室友……对了,她叫什么名字?
看了看手中粗糙的手写合约,好吧,我完全看不清她的破英文签名,只看到一个“Lu”。
小陆搬进来的时候,动静大到左邻右舍都开门出来望一眼。当他们看见一架移动的巨大钢琴后面那个身形娇小的女生时,都不可思议地张大了嘴巴。
大爷你好,我叫小陆,以后住 603,多多指教!
阿姨你好,我以后住 603,有什么帮忙的尽管出声!
小妹你好,姐姐住 603,以后欢迎来姐姐家玩!
狗子你好……
就这样,我精心营造的疏离高冷邻里氛围,在三分钟内被彻底打破。
这晚,小陆邀请了很多人来家里打边炉,她说她带了家乡的火锅底料。我有点被夜晚客厅里出现的盛大邻里派对景象吓到,并生气地在沉默中吃了三碗牛百叶,直到那只还没被阉割的小泰迪在我腿上不停蹭怎么也踢不开为止。
洗碗的时候我还在生气,因为碗柜里被很多陌生的碗筷塞满。天知道她一个那么小的人为什么会搬来那么多碗筷。看着那些厨具上面小狗小猫的弱智图案,我真的很想发一下脾气,可是牛百叶也真的很好吃,算了。
小陆又开始捣鼓新的东西。她在客厅里拼拼拆拆,一开始只是细细碎碎的声响,最后,客厅突然陷入一片黑暗。
就在那个瞬间,我感觉自己捉不住任何物件,就像被什么淹没,是冰凉黑暗的河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我包围。
碗砸在我的脚上,疼痛让我尖叫起来。
怎么了怎么了?小陆跑过来把我扶到沙发上,我眼中的泪水大概诠释了痛感,她跪了下来,捧起了我的脚,放在怀里揉了起来。我茫然地看着地上的小陆,她在干什么?她为什么在这里?
小陆指着客厅中央的一个小盒子说,你看,我弄了个投影仪,以后我们可以一起看电影。
你要看什么?她用一只手滑着手机屏幕,弄部好笑的给你看。滑了一会儿,她放弃地说,就看这个吧。
空旷的白墙上,出现了大概五六年前的一期《康熙来了》。
恍然坐在沙发上,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杯热水,小陆在厨房继续洗碗,不时发出弱智般的笑声。瞬间的晕眩再次占领我的脑海。
我想死……我说。
你说什么?小陆一边看着节目一边大笑着。
我没有再说话,撑起自己的身体,一步一步走进自己的房间,把房门锁了起来。我想我已经开始后悔把她请进家门了。
------------------------
必须强大起来。
在孤儿院里,丁思辰对自己说。
从小就被人说像个男生,不爱哭,吃饭总是最快的那个,喜欢爬树游泳,爱说话,不爱好好睡觉,却对那些欺负女孩的男孩毫不手软,即使他们躲进了男厕,她也会冲进去把他们拽出来,一顿胖揍。
丁思辰有想要保护的人,那是一个她没有见过的人。
自从在院子里种凌霄花的栏杆下发现第一封信,她就开始了这个没有人知道的游戏。参与者只有两个人,她和另一个人。
需要保守秘密,一辈子都要守住这个秘密。她不知道那人是谁,甚至不知道是男是女,他们在信件里没有互相称呼或自称的名字,只是随意地写一些日记和感受。
那时的丁思辰,仍然不太清楚自己是谁。一开始也只是乱写一些问候的话,但大概从第七八封信开始,他们为这小小的秘密发明了第一个暗号,比如那天夜晚如果偷溜出房间去玩,就在信纸上画一个月亮的形状,遇见了不开心的事画一把叉,开心则是一朵花,流泪是一个水滴,流泪整晚是一个巨大的水滴。还有疼痛,是一把匕首。
她常常收到画满匕首的信。
对丁思辰来说,保护一个没有见过的人,是这个未知世界里她能做到的最强大的事。目之所及所有的孤独,对她来说都不那么重要,她是一个记忆短暂的人,看明天,从不看过去,因此她不太记得 3 岁以前的经历,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那长满橘红色凌霄花的高高栏杆外,是怎么样的世界,这才重要。
17 岁那年,丁思辰考上了市里的卫生学校,那也是她第一次遇见辜清礼。
她印证了世界如她的想象,甚至绚烂过想象。
辜清礼,卫生学校检验专业的学长,他高大的身材和流露出来的气质有些不太贴合,也许是那种纯粹的男性气息根本与他身处的环境格格不入。每当她经过实验室,看见他低着头,戴着手套和细边眼镜,专心地为器械消毒、检测时,一种未知的热情就会包围她全部的身心。就像那些夏天孤儿院生长着的橘红色凌霄花儿,铺天盖地,亮烈而强大。
这种热烈会让人生理上有头晕目眩的感觉,仿佛受到巨大的撞击,或是闻到了什么致命的气体。丁思辰必须跑到无人的角落,慢慢平息自己的心跳,才能恢复正常回到课室里上课。
但是,女老师的课堂上永远不允许任何走神。每当丁思辰偷偷望向窗外寻找他一掠而过的身影,就会被女老师点名起来回答问题,这种“过分关心”令她非常不习惯。从小在孤儿院就自由惯了,只要不被饿死冻死,没有人管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这样很好,对丁思辰来说,可以任由自己的思绪翻山越岭。
那天轮到丁思辰做值日,去负责一个谁也不愿意打扫的角落。那角落因为有两棵花树,每到春季只要有微风,便会吹下一大片花瓣,扫完又落,让值日生苦不堪言。丁思辰却乐得如此,她喜欢机械的工作,这样可以尽情想象许多遥远的事物。
直到有颗篮球远远地飞过来,直直打到她的小腿。抬起头见到一个身影跑过来。
辜清礼,他像一个腾云驾雾的神话英雄。
那神话英雄跪了下来,用手捧住她套着的确良长裤的小腿。一截少女光洁的小腿裸露在阳光下,局部皮肤被篮球撞得微微发红。
明天可能会青一块,我去拿药油来搽,他说。
丁思辰没有力气做出任何拒绝,于是他在众人的起哄声中跑开,不一会儿又跑回来。他的手指接触到她的皮肤,以辛辣的药油为介质,触感变得更为强烈。铺天盖地的凌霄花再次包围而来,她头昏目眩,全身颤抖,最后所有的花枝藤蔓一起涌上,让她再也不能呼吸。最后,她低下头,呕吐了起来。
虽然场面很糟糕,但被送去医疗站的过程中,她很开心,很想在秘密的通信上画满代表欢喜的花朵,然而这个秘密的游戏已经很久没有进行了。
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收到栏杆下的信件了。
而悄悄跟踪辜清礼,是新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