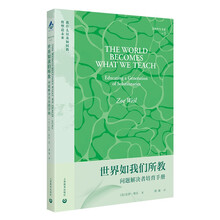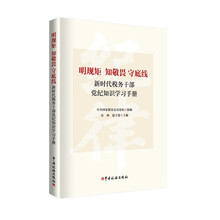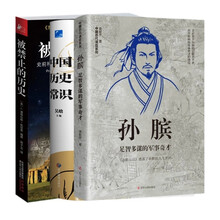《夏志清与沪江大学》:
初见张爱玲 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 一九四二年六月大学毕业后,到一九四五年十月离沪驶往台北去当一名小公务员,那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只参与过两个像样的文艺集会: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里见到了钱锺书、杨绛夫妇和其他上海的文艺名流;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在沪江英文系低班同学家里见到了张爱玲和不少沪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是仰慕张爱玲而来的。此外我并未参加过一个文艺集会,说出来不会有人相信,但实情确是如此。
毕业后我读书更为专心,只同老同学来往,常见面的四位:陆文渊、吴新民和张心沧、丁念庄这对伉俪——至今尚健在,我想另写一文回忆他们。另两位英文系同班同学王楚良、王玉书,同我也有来往。王楚良思想比较“前进”,一九四九年后他在中国外交部工作,曾出差加拿大多年。王玉书来自福建,可能家庭环境比我还要清寒,毕业后即结了婚,且考进了邮政局,抱住了一个铁饭碗。一九四八年我进耶鲁研究院后,给他一封信,他回信对我极表钦羡。假如他终身在邮政局服务,我想即在六七十年代王玉书也未曾受到过多少苦难。赴美前我到他家里去辞别,见到他们小夫妻十分恩爱,而我自己在上海竞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对他们的处境也颇为羡慕。
大三那年,张心沧接任为学生自办的英文《沪江旁观报》(The shanghai spectatot)的主编,我当文艺编辑。心沧同我一样是个不爱搞课外活动的纯学者,到了大四那年,他辞掉《旁观报》主编之职,只好由我接任,另请一位大三学生当文艺编辑。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变,翌晨星期一我照旧乘公共汽车、电车到校,才知道上海也有了个大变动。我刚编好的一期《旁观报》,原该星期一分发给老师、同学的,不料承印该报的英文《大美晚报》社已被封锁,该期也就从未见过天日。对我来说,时局大变之后,整个春季学期我不必再费神去编报,倒是个大解放。
连学校都将改称为“沪江学院”,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当然更无兴致去编印一本毕业纪念册了。少了这本留下每人学士装小照的书,原先不熟的同届毕业生也就更容易忘怀了。不过,上列六位同系同学之外,沪江熟朋友我倒还是有几个的。其中一位名叫王弘之,高一上学期我在江湾沪江附中住读时即同他很熟了。我在《读·写·研究三部曲》此文末段,提到“毕业后两年,有一天沪江政治系同学王君来访”,借走了我的孤本学士论文,这位同学即是王弘之。引文见《难窗集》五十九页。九歌出版社刚把此书重印了一次,市面上应该买得到。
沪江学生要对自己的主修学科、两门副修学科修满了多少学分,才能毕业。一不小心,副修课程学分不够,就有留级之虞。我想王弘之就是这样给拖延一年的。到了一九四三年,上海局势已比较稳定,沪江的大四学生又要出一本毕业纪念册了。王弘之想必参与其事,知道我英文写得好,就向我来拉稿。我反正在家里读书,为他写了两篇,并亲约张心沧写了一篇,对纪念册的编排方面我也出了不少主意。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回到上海老家,才知道所有我的藏书玉瑛妹交给政府后并未发还,想都给毁了。那本毕业纪念册如尚在,我能看到自己的少作同所有一九四三年毕业生的个别照片,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