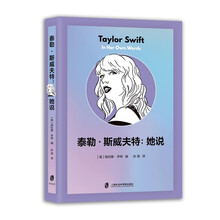童言无忌
七十多年前,一个大年初一,在天津。
在法租界区一条繁华的街道的北侧,一座豪华的宅院。古典式的朱漆大门两旁,蹲着两只雄伟高大的石狮子,巍峨地傲视着。这座宅院昔日通亮的光彩已经黯淡,颜色稍显斑驳,似乎有些过时,然而依然显示着高门贵族式的气势,门前站着巡警把守。一条林荫道由大门进去,直达花木丛中的欧式洋楼前,楼前有喷泉,有花坛,鹅卵石铺成图案的道路连接着洋楼的前后,偌大的院落寂静无声。
大年初一清早的鞭炮声在院外的天空中噼噼啪啪地炸响,一串一串的鞭炮声夹杂着各色焰火,热烈地欢迎着新的一年。在周围热烈的响声中,院内更显得寂静,静得冷清,静得沉郁,那是死一般无生气的寂静。洋楼的主人,一个皮肤黝黑而瘦削的老人,穿着一件青布长袍,斜靠在藤椅里,一手抽着大烟管,一手握一卷旧得发黄的线装书,有气无力地吟哦着混浊得听不清的诗句,窗外依然是热闹的鞭炮声,但这仿佛一点也不能影响到他似的,其实他只有三四十岁,那神情却是六十多岁人的。雕刻着花纹的旧式铜床,柜里布置的古董,墙上的已略变黄的旧字画,满屋浓温的烟雾,都显示着这家主人的身份。
日上竿头,鞭炮渐稀,“咚咚”、“啪啪”,一声疏似一声。
楼上,一个小女孩在梦里被惊醒,翻身一看,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哭:
“热闹已经过去了,没有我的份啦,哇——”
佣人们赶快抱她起来,女佣何干把新衣给她穿上,“小烘子不哭,快穿上新鞋出去玩”。
“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又是大哭,倒在床上哭,不肯起来。
童言无忌——是的,“繁华已经过去,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这句话被她不幸说中了,这个名叫张烘的小女孩,就是张爱玲。李鸿章的曾外孙女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两岁时随家搬到天津。
张爱玲三岁就会背唐诗了,坐在父亲的身旁,依旧是一炉温火,满室烟香,四壁书画,她静静地坐着,想起女佣晚上在床上教她背的唐诗来,便站在父亲膝下背给父亲听——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她不知为什么父亲默默无语,黯然神伤,两行浊泪落在腮边。多年后张爱玲历经沧桑才了解这人世的含义。
这个大家庭败落了。然而当初是何等的荣光,何等的辉煌。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朝末年的大名士。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二十二岁即中同治辛未科进士,授编修,光绪元年(1875)朝廷大考,考得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侍讲,又晋升为日讲起居注官,伴随光绪皇帝左右。少年金榜题名,青云直上,这是张家从未有过的荣耀。这位张大才子在京做官,年少气盛,负一世之誉,抱有壮志雄心,与李鸿藻、张之洞、陈宝箴等京官名流正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道,对曾国藩、李鸿章的定国大计颇为不满,慷慨激昂批评时政,是清流派的主力。张佩纶为官清廉,虽然做着翰林院侍讲,但仍是稀粥白饭,对那些轻裘肥马、锦衣玉食、华屋高堂、拥姬挟妾的达官贵人,不管是朝中清贵还是封疆大吏,只要一有劣迹落在他手,一本参奏就直递皇帝,笔下来得快,语言又犀利,条分缕析,耸人听闻,颇得光绪“嘉许”。因此,他愈发敢言,一个接着一个参奏,参了抚督参藩司,劾罢六部劾九卿,半年时间,不知多少个红翎顶戴被他这一枝利笔拔掉,弄得朝野人士没有一个不怕他的,连后来做了他岳父的李鸿章也差一点被劾。
张佩纶是清流派的中坚。他满腹经纶,评议朝政,对外交力主抵抗。当时法国人侵越南,把攻占越南作为入侵我南疆的基地,张佩纶连向光绪皇帝上十数次奏疏,献抗法策略,不仅赢得满朝清誉,更博得光绪皇帝的赏识,1884一年被钦差福建办海防事宜。他踌躇满志,要在这里一展雄才,可是书生大言,纸上谈兵,碰到实际却一筹莫展。一夜之间,被法军统领孤拔打个大败,身为主帅的张佩纶临阵脱逃,被朝廷革职充军,流放东北,声名扫地。行到塞外时他有一首写得很好的诗《居庸》说:
落日黄沙古堠台,清时词客几人来?八陉列戍风雨阔,重驿通商锁钥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