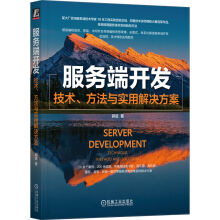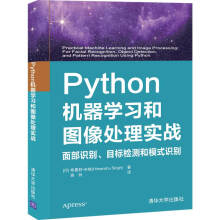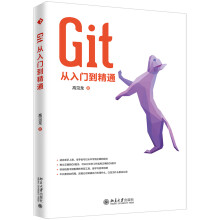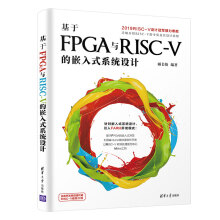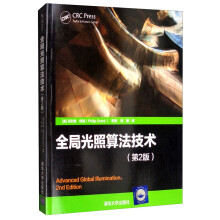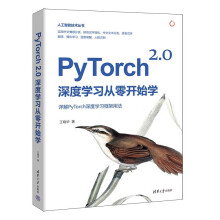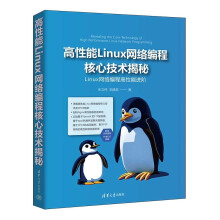清华附中的史铁生中学时代的史铁生在好友中的印象是这样的。胸背略微向前倾,走路有点外八字;眼睛小小的,目光沉稳;圆而大的鼻头实实在在端坐在脸庞中央,威风八面;上唇两撇淡黑色的胡须给面孔增添了几分老成,举手投足间透露着稳重、潇洒和自信。孙立哲——史铁生的挚友,他在《想念史铁生》中是那样描述史铁生的,并且还提到很多自己和史铁生一起在清华附中读书的日子。
史铁生家与清华有缘份。史铁生在奶奶家长大。
奶奶带着史铁生的父亲和两个弟兄三家人合住一个四合院——北京草厂胡同39号,三世同堂。史铁生的大爷史耀增,1951年1月从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全家庆贺;史铁生正好在这个月出生,双喜临门。孩子们吃、喝、玩、念书都在一起。堂兄妹之间,按一家人实行大排行,史铁生是父母所生老大,大排行老三。
史铁生的父亲史耀琛排行老二,没考上清华,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林学系,毕业后曾去东北,辗转回北京。
史铁生的母亲在北京林学院工作。林学院和清华隔一条马路,对面的清华大学收藏着父母的梦。
史铁生自幼记事早,他在《记忆与印象》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我记事早的一个标记,是斯大林的死。
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奶奶抱着我走近看,说:‘斯大林死了。’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儿,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涿州口音中,‘斯’读三声。我心想,既如此还有什么好说,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1953年,那年我两岁。”这段幼稚的对话显示出作家超强的记忆能力。
1964年8月29日是清华大学附中新生注册日,史铁生分在初中64—3班。史铁生是住校生。清华附中专门组织排子车,到清华门外的公共汽车站接远道而来的住校生,这些新生大多来自城里,也有少数海外归侨。史铁生住校的宿舍是一座四层的砖楼,第一至三层是男生宿舍,第四层是女生宿舍,一律筒子楼格局。楼层中间贯穿一条黑幽幽的甬道,两边各是一溜寝室,每间房里支着4个上下铺架子床,睡8个学生。
室内中央吊着一个白炽灯泡。室内没有桌椅和其他家具,读书学习一律在教室和床上进行。每层楼有个公共漱洗室。史铁生在这宿舍楼里住了大约3个年头。
开学不久,教语文的董老师让史铁生在课堂上朗诵了自己的作文,写他小学一位老师,不但文笔好,而且朗读时声情并茂,全班听了一起感动。课后同学们反响很大,好评如潮。当时清华附中语文教学方法之一是选出优秀的学生作文,让学生们自己在课堂上读,促进师生互动,这是清华附中精英式语文教学的一大特色。史铁生早年把直接与间接的经验用丰富的语言形成结构,在中学先声夺人,引起回响。
史铁生有语言天赋,我们可以从《合欢树》中看出:“10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里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10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可见史铁生可能是遗传了母亲这一优点。
史铁生中学时期的两位老师董玉英和王玉田是一对残疾人夫妇。“残疾”和“死亡”这两个词不仅仅是概念,它们以鲜活而残酷的面孔早早地走进史铁生的人生词典。董玉英老师从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是史铁生的语文老师,董老师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跛行;王玉田老师是史铁生的音乐老师,王老师有更深重的残疾,先天性心脏病,左右两个心室之间有多个孔洞,无法手术修补。平时嘴唇呈微紫色,只能走路,不能跑,不然就喘不上气。更惊人的消息是:医院的专家判定王老师活不过30岁!学生们对老师充满敬意,王老师最后在学生们为他组织的专场音乐会的舞台边倒下,史铁生那时正举着鲜花要献给他。几米的距离,死神在意想不到的时刻现身,分秒之间天人永隔,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史铁生在文章《纪念我的老师王玉田》中写道,“我最终从事文学创作,肯定与我的班主任是个艺术家分不开,与他的夫人——我的语文老师分不开。在我双腿瘫痪后,我常常想起我的老师是怎样对待疾病的。”“恰似我们当年。纯洁、高尚、爱和奉献,是他的音乐永恒的主题;海浪、白帆、美和创造,是我们从小由他那儿得来的憧憬;祖国、责任、不屈和信心,是他留给我们永远的遗产。”中学时期正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的形成期。而中学阶段的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史铁生读初中的时候,就遇到了一对残疾夫妇老师,但身残志坚的两位老师却又那么地才华横溢,正如他在《纪念我的老师王玉田》一文中所说,王玉田是“我”初中两年的班主任,“那时他才二十八九岁,才华初露,已有一些音乐作品问世。”“他的夫人我们的语文老师董玉英,那时可能还要年轻些,快乐、奔放,而且非常漂亮(她的腿有一点残疾,常令大家觉得上帝也有一些错误)”。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