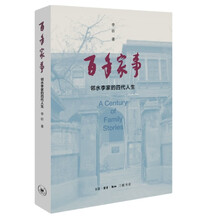《自由的真谛 杰斐逊自传》:
第一章 家族故事
七十七岁之年,我开始想写回忆录,陈述生平所经历的事情,以便日后家族参考,留档。
我的家族来自威尔士,祖先曾生活在靠近斯诺登山的地方,斯诺登是英国的最高山峰。我曾在威尔士的一份法律文件上看到了杰斐逊这个姓氏,另一个同样的名字则来自弗吉尼亚公司的秘书。在英国看到杰斐逊这个姓氏,仅此两次。在早期的记录当中我找到了佐证,但是我的祖先当中却没有人在弗吉尼亚公司做秘书,倒是有人在该公司工作过。他在1619年乘博纳诺瓦号到达弗吉尼亚。
我的祖父生活在切斯特菲尔德一个叫奥兹波尔的地方,并拥有该教区的土地。他有三个儿子,托马斯,少年夭折;菲尔德在罗诺克河边安了家并有无数个后代;还有我的父亲皮特,在沙德韦尔成家,至今我还拥有着那片土地,与我现在住的房子相毗邻。我的父亲出生在1707或1709年的2月29日,1739年,他与十九岁的简·伦道夫——艾沙姆·伦道夫(Isham Randolph)的女儿结为夫妻。他们的家族能够追溯到英格兰和苏格兰,其后人顺应了他选择的信仰和美德。
我的父亲从未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个人意志坚定,富有判断力,对知识又充满渴望。因为读了很多书,他得到了极大的自我提升,也因此,约书亚·弗里(Joshua Fry)雇用我的父亲来为他绘制弗吉尼亚和北加利福尼亚之间的边界线。这一项目是由科洛·伯德(Colo Byrd)发起的,随后弗里先生再次雇用我的父亲和他一起制作弗吉尼亚的第一张地图,毕竟,史密斯上尉绘制的弗吉尼亚地图也只是推测出来的草图。他们为那片蓝色山脊下富饶的物产而感到着迷;那时候,山脊上面还鲜有人探索过。约1739年,我的父亲是第三或第四个移居到我居住的村庄的人。
他于1757年8月17日去世,之后,我的母亲一直寡居,直到1776年离世为止。他们抚育了六个女儿,两个儿子,我则是家里的长子。父亲将詹姆士河边的一处房产留给了弟弟,为了纪念家族发源的地方,父亲将其命名为斯诺登小屋。而留给我的则是我出生和居住的那片土地。我五岁的时候,他把我送到了英语学校学习,九岁时送到了拉丁语学校,直到父亲去世。
我的老师,道格拉斯先生(Mr.Douglas),是一位来自苏格兰的牧师。他略懂拉丁语和希腊语,除了教我以上两门语言的基础知识之外,他还教我法语,一直到我父亲去世,我都是他的学生。之后,我向毛里牧师(Mr.Maury)求学,他是一个纯正的古典学派学者,在他门下经过两年的教育之后,也就是1760年春天,我继续到威廉一玛丽学院学习,那两年的学习是我整个人生的一笔财富,甚至确定了我人生发展的轨迹。
威廉·斯莫尔博士(Dr.Wm.Small)当时是数学教授,他精通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视野开阔,充满风度,且善于与人交往。让我开心的是,不久之后,斯莫尔教授便十分喜欢我,并时常在课余时间让我陪伴他左右。从他的谈话当中,我开始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科学、体系和一切。幸运的是,很快哲学教席便有了空缺,因此校方任命斯莫尔教授任职,于是,他成了学校第一个上伦理学、修辞学和纯文学的常任教职人员。1762年,他回到了欧洲,在他回去之前,他尽最大的努力帮我铺好了后路。他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挚友乔治·韦瑟(George Wythest),之后我便师从韦瑟学习法律。除此之外,斯莫尔还把我引荐给法奎尔总督(Governor Fauquier)和他的朋友们。法奎尔总督在历届总督当中最德高望重。法奎尔总督、斯莫尔博士和韦瑟先生以及我,我们四个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四人集团”,时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我从谈话中受益匪浅。在我的青年时期,韦瑟先生一直是我可靠的朋友,崇敬的恩师,他是我一生当中最亲密的朋友。1767年,韦瑟先生带我进入了大法院进行律师实践,直到革命爆发,法院被迫关闭为止。
1769年,我被州内选为州议会的成员,履职直到革命爆发,议院被强迫关闭为止。此间,我曾提出解放奴隶这一议题,但被否决了。确实,在当时王室的统治下,任何自由主义的想法都是不可能被允许的。我们的想法都被习以为常的观念束缚着,我们坚信在政府统治方面,我们应该无条件服从我们的母国,我们的努力应该是符合大不列颠帝国的利益的,甚至,我们固执地排斥除了帝国的宗教之外的宗教信条。
我们的议员提出的异议并不是出自思考和信念,而是出于习惯和绝望。很快,实践证明,一旦要求他们思考,他们的注意力首先便会放在权利上。在国王议会(相当于另一个立法院),议员们完全服从于国王的意志。就连拥有终身任命的否决权的总督也是如此,甚至他表现出的忠诚更甚。因此,国王拥有的否决权堵上了改良希望的最后一扇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