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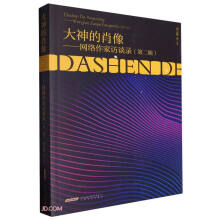


观察名人大家喜怒哀乐,倾听名人大家情感历程。本书为文汇报品牌栏目《近距离》十年精选集。传承深厚的历史文脉,通过近距离观察,近距离倾听,深层次挖掘,这些美文凸现了当代文化名流大师的情感历程、思想魅力及广泛影响,真实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近距离:与22位文化名人的亲密接触》为文汇报品牌栏目《近距离》十年精选集。传承深厚的历史文脉,通过近距离观察,近距离倾听,深层次挖掘,这些美文凸现了当代文化名流大师的情感历程、思想魅力及广泛影响,真实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本报驻京记者李扬
题记
他早年学经济,干金融,跑过纽约、伦敦等“大码头”,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却在49岁痛快地“改行”,开始了一段“字母之路”的跋涉。
此后“半路出家”的他令人刮目——让世界最通用的26个字母为汉字服务,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自1958年起推行全国,至今已50周年;有著作《汉字改革概论》等20多部,还是最早《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
他生于晚清,自嘲“被上帝遗忘”,却依然站在时代潮头:83岁“换笔”用电脑,百岁高龄仍有新作问世,现在每天还在读书写作,每周发表一篇随笔。
他,就是103岁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读书看报写作自嘲“无业游民”
(一)
朝阳门内后柺棒胡同里有一幢普通的灰色住宅楼,这里是国家语委的家属楼,周有光先生的家便在3层的一个单元里。
因为周老有午睡习惯,记者与周老相约下午3时见面。进门后,保姆推开左手书房的门,只见老人早已端坐在书桌前,安静地等候着,看我走近,周老热情地伸出双手迎接我的到来。
虽早已闻先生居家简朴,但走进这间9平米的小书房,仍惊讶于陈设的朴素——小书桌只有两个普通抽屉的宽度,桌面上主人伏案的那部分早已磨得斑驳;3个高低不等的书架贴墙站立,小书房内还有一个能坐两个人的小沙发,以及书桌对面的两只凳子。一切都素朴到极点,甚至有些简陋。当我后来翻看先生的一本书,见到一张1994年先生和老伴张允和在这间小书房的生活照,才恍然明白,原来这里的一桌一凳,甚至窗帘,都是十几年如一日陪伴着主人读书写作。
把两只助听器塞进耳朵,周老笑着对我说,“耳朵不好,书房小正可以拢音。”
周老看起来比照片上略显清瘦,但精神十分矍铄,说话嗓门豁亮,笑起来中气十足,近距离看,老人家头发虽然稀疏却并未全白,牙齿仍是“原装”的,皮肤细腻而透亮,额头宽阔而光洁,好一个童颜鹤发!难怪会闹出如此笑话:97岁时周老到医院体检,医生见了二话没说就把年龄改作了79。
周老说:“我就是耳朵不灵啦,别的都很好。”而在我看来,周老的耳朵并没有那么不灵,访谈的2个小时里,我只需提高声调,学着周老的豁亮嗓门说话即可。只有两次他听不太明白我的话,让我用笔写,可还不等我写好,他在桌子对面反着看我的字就明白了。
周老爱笑,爱讲趣事,也爱幽自己一默,这让小屋里时常笑声连连。当我叹道“您的记忆力太好了”,他马上谦虚道:“现在我的记忆像个接触不良的电器,一会儿记得了,一会儿又忘掉了,靠不住的。”周老拿出新书《汉语拼音,文化津梁》送给我,挥笔写下赠言,手不偏不抖,签名后面又署上“时年103”,笑着道:“倚老卖老。”
(二)
周老身边放着一个用碎花布包裹的打字机,这里面就是他每天写文章的“笔”:“现在没几个人会用这种打字机了,可我用习惯了,电脑屏幕太大,它的小屏幕正合适我。”
“我85岁离开了办公室,就离开了专业工作,开始随便看东西,随便一看呢,我发现专业之外有一个知识的大海洋啊,我是文盲,自己呢就要自我扫盲。”先生笑呵呵地自嘲。
说话间,周老会随时扭转身子从背后的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或伸出左手在一大摞资料里取一份剪报给我看,像个变魔术的老人,能迅速从纸堆里抽出他要找的东西。
周老说自己是“无业游民”,所以每天只好做这些事“打发”时间——
读书。周老日常要阅读大量的书,这两天刚刚看完两大厚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他赞道:“编的人很有水平,资料很翔实,两大本我都看完了,从早到晚看。”周老还喜欢读世界文化,主要看外国的,会“随便记点笔记”,留作写文章用。
看报。每天看的报首先是《参考消息》,从头到尾全看完。然后是香港朋友每个礼拜寄来的外国杂志,“这个NEWSWEEK,每一期我都看,还有其他的东西,我看了就扔掉了,因为我的房间太小了放不下。”
写作。每个礼拜发表一篇随笔,大都刊在《群言》杂志上。“这个杂志是20多年前民盟办的,胡愈之是领导,他找22个能写文章的人,做杂志编委,从那时起我每个月都给他写,写了二十几年,这22个人大部分都死了,还剩下两三个,他们都不会写文章了,已经老了,我说我还没老。”说到这,周老孩子般地笑了起来。
现在周老看的最多的是人类历史、人类文化的东西,还会把他看到的前沿新知写成文章,“我写东西很通俗,太学术的都改掉,目标就是让初中生看懂,以前写给大学生的教科书,也很通俗,我一直是这样,我说我是搞科普工作的。”
说着,周老递给我他近日的新发现:一则题为《光绪死因百年后破解》的新闻。这段长长的报道被单独剪了下来,显然周老对此兴趣极大,一字不漏地看过,每行文字上都标有一杠蓝色水笔印迹,空白处还写了减法公式计算光绪的继位年龄。
看我拿着剪报端详,周老说:“你留着吧,我已经抄下来啦。”随即,他打开近身的一个抽屉,我凑前看,里面竟是一大抽屉的3。5寸软盘,粉的、蓝的、绿的,整整齐齐排放着!这些软盘里正存着周老用打字机抄录的剪报。
就是这样的点滴积累,周老写了很多充满时代气息的杂文、小品文,思想开朗,用笔精湛,连年轻人看了都自叹弗如。
周老的老同事、相交30年的好朋友方世增先生告诉我,在他看来周老最“厉害”的不仅是知识渊博,还有一点是记忆力超强,“我没有见过第二个记忆力像他这样好的人,他能做大量的‘资源整合’,会从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知识里发现规律,发现新东西。如果记忆力差一点,是做不来的。”方先生说,这恐怕正是周老能在语言文字学领域做出杰出成就的原因。
漫长的语文现代化之路
拼音是“文化桥梁”
今天,世界最通用的26个字母在为汉字服务。
可是起初,这一点曾经备受争议,最为响亮的质疑是:中国泱泱几亿人口,为什么不自创一套字母让外国人来学我们?1950年代的中国许多人都这么想,周有光平静地解释道:采用世界最通用的字母,是人类文字发展史的必然趋势,不是个人好恶问题。字母为任何人服务,善于利用,它是无价之宝,不能利用,它就一文不值。
今年9月,台湾开始采用汉语拼音方案,我问周老:“听说此事是否感到高兴?”老人呵呵地笑了:“台湾搞了个通用拼音,结果呢,通用拼音不通用,而且无意中对台湾产生自我封闭影响。字母是一个文化问题,学术问题,不要和政治混在一起。现在台湾用汉语拼音,彼此一致,大家方便,是件好事。”
“语文现代化”这5个字,在语言学家周有光看来,是条“不简单”的路:“中国的语文现代化从清朝开始,开头很困难。现在学普通话没人反对了,20年前还有人反对哩。白话文没人反对了,以前也反对得很厉害。汉字简化,也曾有人反对。汉语拼音以前有人反对,现在没有了,手机帮了拼音的忙,大家发短信都用拼音了。”
在一个文化基础深厚的民族里,产生一个新的拼音方案殊为不易。从20世纪初开始,先后有人倡导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皆未普及开,直至建国后,汉语拼音方案从1400多种方案里脱颖而出,方才尘埃落定。
从《汉语拼音方案》推广之日起,争议与质疑就不曾停歇,有人说:“如果秦始皇采用拼音,中国早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了。”还有人指责方案“毁灭华夏文化”、“数典忘祖”。时至今日,这种观点依然存在。周先生却十分理解:“这是传统文化面对外来挑战时必然表现出来的自卫本能”。
“汉字是中国的传统,根深蒂固,不可替代。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帮助汉字,做很多汉字不能做的工作,不是代替汉字的。”周老强调说。
那么汉语拼音是完美的方案吗?周老认为: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改掉一个缺点,往往会产生另一个。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
50年了,时间最终证明了拼音这座“文化桥梁”的科学性、实用性。今天,不仅中国需要拼音,外国也需要拼音,拼音属于世界,这架“穿梭机”往来东西,沟通中外。
“文明古国要想成为文明‘今’国,不能不进行现代化的改造,现代化必须以教育现代化为基础,教育现代化必须做好语文现代化的准备,比如在规范化上我们的语言文字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周老说。
我们不会时刻意识到汉语拼音的存在,正因为它的作用无处不在——
它是扫盲的“钥匙”,它方便外国人学习汉语,它是护照上汉语姓名的拼写法,它是马路上的指路牌,它是电脑、手机中最主要的中文输入法,它在检索、编制盲文和手语、编制工农业产品代号等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它被国际标准化组织和联合国秘书处确定为拼写中国地名、人名和中文的标准……假如把拼音从我们生活中抽走一天,文化交流的桥梁就会坍塌。
“半路出家”成专家
虽然49岁才“改行”从事语言学研究,实际上18岁时周有光就对字母产生兴趣了。
1923年,初到上海圣约翰大学,他发现什么都用英文,连门房讲话都用英语,写文章用打字机了,不用手写了,而英文很方便打字,中文不方便。因为一直对语文有兴趣,上世纪30年代,周有光参加了“方言拉丁化运动”,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鼓励周有光在拉丁化运动刊物里写文章,“他把我的文章集成一本书,给我写了一篇序。现在看起来那些文章都是很幼稚的,不过他给了我鼓励。”讲到这第一本“专著”,周老有点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后来直至解放前,周有光一直学经济、从事金融工作,并在美国工作生活了两年多。解放后,周有光回国在复旦大学教书。
“一解放,就要建设现代化国家,但是遇到一个问题,80%是文盲,怎么办呢?”于是,1955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有光参加了。
“开完会,我要赶快回上海,因为我是复旦大学教授,还是新华银行秘书长,还是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业务处的处长。胡愈之找我来说:“领导决定把你调到‘文改会’来,你不要回去了。我说不行,语文我是业余搞的,是外行。他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为此周总理亲自给上海打电话,让周有光留在北京。
当时,由于长久没有统一的注音符号,56个民族有80多种语言和地区方言,使人们的交流困难重重。制订一套汉语拼音方案迫在眉睫。
“我对语文的兴趣是很大的,当时我觉得能在语文上做点工作也很好,就改行了。”1955年起,周有光正式“改行”,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语言学家。而如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同时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和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著作。
文字改革委员会机构规模不大,可级别很高,国务院直接领导,“优待得不得了,我们要什么资料就有什么,当时非常看重语文改革。有两个研究室,一个研究拼音化,一个研究汉字简化。我呢,主管拼音化研究室。”周有光说。
1958年2月11日,历经3年研究起草的《汉语拼音方案》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正式推广全国。
百年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人们惊叹于周有光的健康长寿,常会不约而同来请教“秘诀”。
老人的答案简单:气量大。
……
冯骥才 把书桌搬到田野
周汝昌“解味道人”
铁凝 作家要营养灵魂
柏杨 不变的中国心
陈丹青 退可退,非常退
杨丽萍 民族舞蹈的朝圣者
韩美林 艺术生命刚刚开始
冯其庸 文化这部大书,怎么也读不完
周有光“汉语拼音之父”
刘诗昆 扛住人生的“地震”
何占豪/陈钢 50年“一醉”为《梁祝》
麦家 守望常道
巢峰 不辞长做《辞海》人
阎肃 不老的歌
李泽厚 思想之河汩汩向前
靳尚谊 尽精微,致广大
宗璞 希望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
方成 锐笔漫画世间百态
朱清时 几度春秋南科大
汪品先 中国版“老人与海”
饶宗颐 所谓大师,是要讲机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