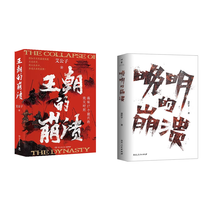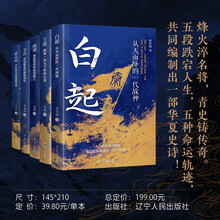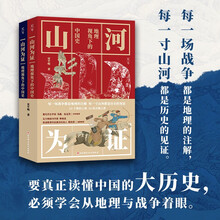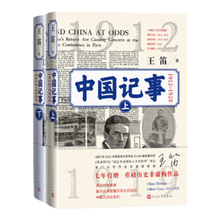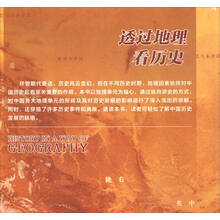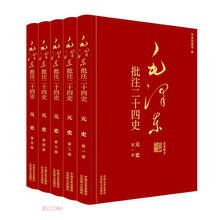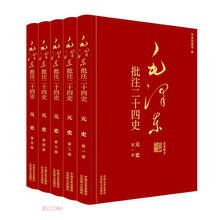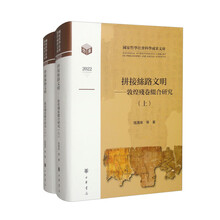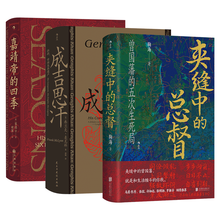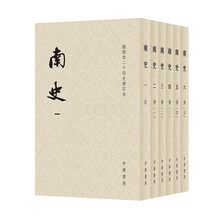征和四年,桑弘羊约同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商丘给汉武帝上书,建议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继续对匈奴取进攻态势。桑弘羊认为,轮台一带是汉朝与西方交通的必经之地,又是匈奴经常出没的地区,在那里屯田,可以有供开垦的水浇地五千多亩。屯田搞好了,就在那里站稳了脚跟,不但可以解决戍边将士的粮草,还可以建成对匈奴作战的前线阵地。
轮台屯田建议其实是桑弘羊一贯思维的延续:早在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桑弘羊为了巩固对匈奴战争的成果,建立稳定的边防,从根本上解决边防军的粮食供应,借鉴汉文帝时晁错提出的“募民实边”的措施。建议汉武帝募民十万屯守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元狩四年(前119)又徙关东贫民七十多万至今甘肃边防。桑弘羊任大农丞后,更为积极地贯彻这一方针,元鼎六年(前111)先派吏卒五六万到今甘肃永登一带屯戍,接着扩大到上郡(今陕西绥德东南)、西河(今甘肃东胜县)及新建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均在今甘肃境内)四郡,人数增加到六十万。从当时看,对于发展西北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就地解决戍边将士的粮食供应,显然是行之有效的好方式。
但这仅是从统治者角度的考虑。从众多的边塞诗中,我们了解了轮台一带的恶劣生存环境:岑参在《走马川》-诗中,这样描绘了走马川(即轮台地区):“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血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中,还写下这样的诗句:“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在桓宽的《盐铁论》-书中,记载了贤良文学与桑弘羊之间关于对匈奴和战问题的激烈争论。贤良文学认为,对待匈奴,用战争的形式不如用和亲的形式,只要用仁义引导感化他们,就能避免匈奴的骚扰,维持北方和平的局面。他们主张“罢关梁,除障塞,偃兵休士,厚币和亲”。桑弘羊则强调了汉初对匈奴“和亲政策”的失败。“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高适诗句),匈奴反复无信,百约百叛,经过连年战争,匈奴已然挫折远遁,现在正应趁热打铁“宜将剩勇追穷寇”,彻底征服匈奴的大好时机,万不可功亏一篑半途而废留下隐患遗恨无穷。
正是在此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的情形下,汉武帝颁布了“轮台诏”,这被后世称之为是汉武帝的“罪己诏”:
“以前主管大臣奏请增加百姓税赋,让每人多交三十文钱充作军费,这无疑是加重老弱孤独的困苦!今又奏请屯戍轮台;轮台在姑师以西一千多里,从前发兵攻打姑师,虽然得胜,但因路途遥远,沿途死了数千人,何况如今要到姑师以西更远的地方!当年军士死亡,离散悲痛,朕常常挂念在心。今若派人到轮台筑垒垦田,岂不又要扰乱天下、苦害百姓吗?朕实不忍闻!当今最要紧的是,废止残暴的刑罚,减轻百姓的赋税,鼓励农夫努力耕种,让养马者得免劳役。只要国家开支不缺乏,边防宁备不放松,这也就可以了。”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吾皇圣明,对于下面庸臣出的馊主意,明辨秋毫。面对一片非议声,汉武帝对桑弘羊由支持转而“嫁祸于人”。汉武帝的轮台诏,与其说是“罪己诏”,还不如说是为自己写的一份“辩护书”。
汉武帝还进行了一番“作秀”表演:汉武帝让大臣准备好农具,自己亲自下地耕种,以示重视农耕。这就是著名的汉武帝“亲耕礼”。还颁诏让全国官员劝导农民好好耕种,求得丰衣足食。他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做了不少悖礼之事,使天下人愁苦,如今追悔不及,从今以后,凡伤害百姓之事,全都应当罢废,不得再行。”
吾皇幡然悔悟,而桑弘羊却不懂“与时俱进”,还沉浸于陶醉于自己昔日的经济才能之中。从汉武帝的“轮台诏”中,其实已透露出汉武帝此一时彼一时的倾向性。这也就昭示着“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桑弘羊将成为“替罪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