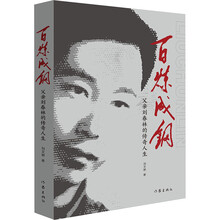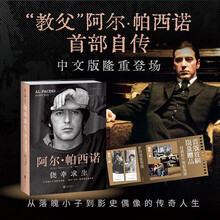游子回家
1967年,“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轰轰烈烈,我自觉无藏身之地,于是我和之昭、十弟以及一班朋友就离家出走。17年后,我真的想不到有回头之日,铁树真的开花了。大门紧闭了几十年,现在像西关老屋的三重门,终于开了。1984年夏天,红日炎炎,我第一次带着一家三口,远渡重洋,回到对我来说不堪回首的香港岛。在贤妻的表姑姐安排下,我们住进了香港希晨道的利园五星大酒店。
香港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这里挣扎了三年。那时,我是最下层的蚁民。蹲人跨下,忍辱偷生。今非昔比,现在我能挺起腰来说话,站起来走路了。并不是我突然拥有家财万贯,傲气凌人,而是我的十年奋斗,使得我终如愿以偿。这次回来,我心情起伏,特别兴奋。人日:触景生情。我云:触情生景,正如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次回来,我看维多利亚港特别美。我重游香港山顶,站在“老衬亭”遥望下去,依山伴水,大厦林立,白云漫漂,蓝天绿水,帆船起伏。美!
我有意取道珠江,坐渡船回乡。因为17年前,我们几经周折经水路从广州到达香港。我是“督卒”过河,偷渡出去的。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大串联”,串了去香港。我不串则已,我一串就串了几十年,而且我越串越远,好像迷途不知返,我串到地球的另一边。
那天是1984年5月21日,我们特别早起,收拾大批行李,其中绝大多数是手信。我打开窗帷,外面风和日丽,但我心情喜忧交杂:喜者,将要见到离别17年的亲友父老;忧者,偷渡客还乡,总是有些心怯。
“庆利(Henry),起床!起床!”庆利是我的儿子,他才三岁,天真烂漫,朱唇乳齿,唾液流涎,熟睡不醒,我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他后来可把我累坏了,从家里出发路经夏威夷到达香港,这家伙诡计多端,借口地下太脏,从未下地走过半步。我一直抱着他,我的右肩关节因此而隐痛三个多月。我也拿他没办法,谁惯坏了他,不好说。他是婆婆(外婆)的宝贝,更甭提他妈妈了。我嘛,对他外刚内柔。
我们归心似箭,草率吃完早餐,便赶路去了。我左手提着行李,右手抱着庆利,打车直奔码头。我早有心理准备,每分每秒我都铭记:一定要小心翼翼,循规蹈矩,不能出丝毫差错!我外弛内张,但还未至于“冷汗横流”的程度。我没有做贼,但我的心实在是虚呀!说句掏心窝的话,我离家出走后的17年,仍然噩梦频频,半夜惊醒!那些往事铭刻在心底实在太深太深!
我们到了码头,排队过关,那小家伙没有添乱。我们寸步移行,我手里紧握护照,瞻前顾后,看看是否被人注意。好不容易排到前面,看到海关人员穿的是香港制服,我真的犯糊涂!如梦初醒,原来我是出香港海关而不是人大陆海关。如释重负,我的心率、血压恢复正常。我把神态放松,慢条斯理地下船去了。我找了个靠近窗门的佳位,希望能沿途观望珠江两岸的景色,也能回忆及对比17年前逃走的旧水路。待旅客上齐,渡船“扑扑扑”地离开码头,乘风破浪向广州而去。那些柴油味熏染船舱,真害怕小儿哮喘复发,只能望菩萨保佑这小家伙安然无恙。
把妻儿及行李安置下来,回首仰望,大厦林立的香港岛好像平台一样浮在维多利亚港上,从我们渡船的后边慢慢离去,远远地消失。转头直望,看不出什么所以然,因为珠江口太宽了。久而,货船鱼船穿梭左右,互鸣互应;久之,目中无船,一片茫茫。除了令人讨厌的引擎声外,仍是引擎声,闷得发慌。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渡船引擎转慢,最后停在河中。我以为机器有故障。“扑扑扑”的不同频率的引擎声从远处传来,我举目外望,发现一艘飘有五星红旗的快艇向渡船开来,我竞有些不知所措。
待两船相接,有两个穿着绿色军装、手握冲锋枪的军人登上渡船。“生死有命,来就来吧!”我绷紧脸,咬紧牙关去面对“大祸临头”!那个20岁出头的边防军人,人高马大,方面毛脸,眉粗眼大,面无表情,严肃可畏,向我迎面而来。我面有改容,非白则红,我的心率血压又回升了。他由上至下打量我一番,然后慢慢地擦肩而过。说句真心话,我确实有点紧张。“我不是贼,不要怕!”我自我安慰。后来,我发现他们不是冲我来的我才如卸千斤。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