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他们
1976年11月的一天,菲利普·罗斯来到艾萨克·辛格在曼哈顿的寓所,向他打听一个人。“也许我不该说出来,”辛格有些犹豫,“他比卡夫卡棒,因为在他的一些故事中,表现出更高的水平”。
十几年后,同样在纽约,在另外一场谈话中,达尼洛·基什激动地告诉厄普代克:“舒尔茨是我的上帝。”而后者同样是舒尔茨的粉丝,他认为:“世界在舒尔茨的笔下完成了伟大的变形。”
就像黑暗中兴起的一支秘密教派,信徒的队伍在迂回中发展壮大:哈罗德·布鲁姆、库切、辛西娅·欧芝克、大卫·格罗斯曼、余华……粉丝阵营强大到令人咋舌。
据拉塞尔· 布朗在《神话与源流》(1991)一书中爆料:当年,詹姆斯·乔伊斯为了读懂舒尔茨,曾经一度想学习波兰语。可是,波兰语哪是那么好学的?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复杂的语言之一。比如,它有五种性别结构,七种变格……
辛格对这个比自己整整大一轮的犹太老乡用波兰语写作多有不满,因为那意味着被同化。他自己坚持用意地绪语─一种濒临消亡的古老的犹太语言写作。“他们不懂意第绪语,我们不懂波兰语。”辛格说。他强调自己“讲任何语言都带有口音”,菲利普·罗斯则安慰他说:“你讲意第绪语没有口音,因为我修过意第绪语。”
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人,不太容易理解这些意味着什么。这种民族、宗教、语言的超级复杂生态,会孕育出怎样一颗斑驳的灵魂?面对舒尔茨不可思议的写作,中国作家余华给出了一种解释:“犹太民族隐藏着某些难以言传的品质,只有他们自己可以去议论。”
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中,卡夫卡和普鲁斯特的地位有如神祇。今天当读者看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同两位神祇并排摆放在一起时,第一反应只能是:怎么可能?特别是,当这个人被认为“轻而易举地达到了普鲁斯特和卡夫卡未曾达到的深度”时,读者的反应已经不仅仅是怀疑,而是茫然和不知所以。然而在舒尔茨的粉丝们眼里,这有什么呢?
舒尔茨在艺术圈里的影响,丝毫不逊于文学圈。他迥异于常人的精神思维与绚烂奇崛的极致风格,向来深获先锋艺术家们的钟爱,取材于其作品的电影、舞剧、音乐剧屡见不鲜。甚至早在舒尔茨的小说中译本问世前两年,以色列现代舞团已经来中国演出了他们的经典舞剧《大买卖》。这部舞剧其实就取材于布鲁诺·舒尔茨的《肉桂铺子》、《鳄鱼街》、《盛季之夜》等小说。
远在1973年,波兰大导演沃伊采克·哈斯拍摄了超现实主义影片《沙漏疗养院》,并获得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这部取自舒尔茨同名小说的电影,将舒尔茨很多小说里的内容及其本人的生平经历融为一体。
英国的奎氏兄弟后来受舒尔茨作品的启发,拍出了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十部动画片”之一的《鳄鱼街》。奎氏兄弟发表了如下的“获奖感言”:
“当我们读着他(舒尔茨)的作品时,我们感到那就是我们希望自己的动画所能走的发展方向……舒尔茨释放了我们的想法,他是一位有震撼力的作家,我们甚至可以以余生不断地围绕着他的作品进行尝试和提炼,去理解他的精神宇宙。”
去年冬天的某个夜晚,我在欧盟北京影展活动开幕式上看到一部瑞典电影:《校园规则》。里面有个看上去落拓不羁的老师在给学生上生物课,为了便于学生理解他讲的内容,他比画着一些鸟类标本说:“就像布鲁诺·舒尔茨的小说里写的那样……”
哈!我忍不住叫出声来,像黑暗中认出自己的同志。
Ⅱ 布鲁诺·舒尔茨的奇观
这是一个几乎无法用语言复述的世界,一个此前从未有人展现过的奇观。
这里时空错落扭曲,幻象层出不穷,处处流淌着隐喻与梦魇,神秘、幽暗、怪诞、栩栩如生、富丽堂皇、骄奢靡逸、匪夷所思……这里是单纯与繁复的迷宫,诡异与天真的花园,梦想与神话的源泉,充满了数学的精准和音乐的律动,步步为营的诗意美不胜收,令人窒息。
舒尔茨笔下的世界根植于人类潜意识深处,根植于原始的尚未成形的宇宙,因此充满流动不居的无限可能—“每一页纸上都有生活在爆发”(大卫·格罗斯曼语)。同时,这个世界凝结了难以启齿的辛涩与羞耻,使卑微之物发出闪光,向着平庸、固化、死寂的现实和历史开战。这个世界可以感知,却无从捕捉。当它如巨大的星团朝我们豁然敞开时,我们感到由衷的眩晕、惊奇,却不知如何命名和处置。在伟大而缜密的美面前,读者不得不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宛如回到了懵懂而满怀憧憬的童年。是的,只有回到人类童年,才能深入这个魔镜与万花筒的世界。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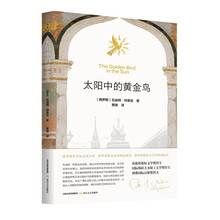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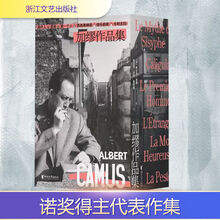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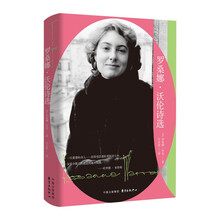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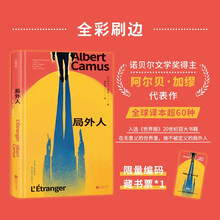




——库切
布鲁诺·舒尔茨的作品最早都是发表在信件上,一封封寄给德博拉?福格尔的信件,这位诗人和哲学博士兴奋地阅读着他的信,并且给予了慷慨的赞美和真诚的鼓励,布鲁诺·舒尔茨终于找到了读者。
——余华
不容易把他归入哪个流派。他可以被称为超现实主义者,象征主义者,表现主义者,现代主义者……他有时候写得像卡夫卡,有时候像普鲁斯特,而且时常成功地达到他们没有达到过的深度。
——艾萨克·辛格
一个无与伦比的作家,世界在他的文字中完成伟大的变形。
——约翰·厄普代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