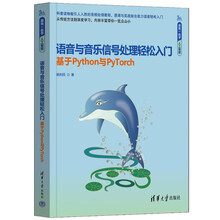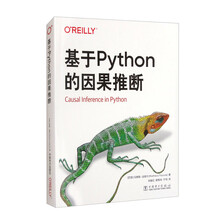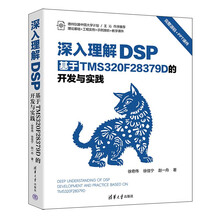孙冶方不知道,如同他一样,1934年的二哥薛明剑也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难关”。那一年,他所服务的申新“搁浅”了,资金链濒临断裂,政府要将其收归国有。为了保住这个中国最大的民营纺织企业,他在宁沪的政府、银行间奔走呼号,折冲调停,同时连自己的薪金都投入了拯救企业的再生产循环中。他当真拿不出过多的钱资助四弟。
在《五五纪事》中,薛明剑如此记载:“(1934年)五月,申新总公司因经济周转呆滞,请求政府救济。迨至七月间,政府忽有收归国有之说。余即奔走京(宁)沪,与行政院汪精卫、实业部陈公博折冲,并访工商界要人,请主张维护民营工业,最后得新新通讯社冯社长、申报史经理量才(室人业师)之助,并得吴稚晖、吴宪塍两先生主持公道,始得打消原议,安渡难关。(详见当日各报及《纺织周刊》)”《五五纪事》,《薛明剑文集》第51页。
这一事件,是申新系统在发展中遇到的最严峻的一次存亡危机。由于涉及许多当时的军政要人,并与当年那场影响深远的经济大危机相联系,使得这一事件的产生、发展和结束,与中国民族资本的命运息息相关,颇具几分悲壮的色彩。
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波及面极广,持续四年之久,给世界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大破坏。“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因关税不能自主,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场所。
荣氏集团经营的面粉、纺织等产业,在大危机爆发前发展到顶点,但这都是在大举借债的条件下形成的,基础十分脆弱。当经济危机爆发后,面粉销路呆滞,纺织业则由于棉花生产不足,加之日纱倾销,出现“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的状况,加之荣氏从事投机生意失利,致使资金周转发生了严重困难,历年积欠的贷款无法偿还。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房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索款更急。此时申新负债累计达6375万元,全部资产总值不过6898万元。到这年6月底,到期的500万应付款,申新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素有“无锡拿破仑”之称的荣宗敬急得几乎要自杀。荣氏家族不得不将自家1000余万股票等有价证券向银行作抵,由新银团放款500万元,但实际只得280万元,难挽荣氏颓势。7月4日,申新即告“搁浅”。
在此万般紧急状况下,荣氏集团向国民政府伸手求援。荣宗敬写信给实业部、财政部、棉业统制会等部门求助。荣德生到南京面见行政院长汪精卫,希望能发行公司债券来渡过难关。汪精卫将此事交陈公博为部长的实业部处理。陈公博随即派员会同全国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的官员去上海调查,很快就提出了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
这份报告书对荣家很不利,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报告书认定申新已资不抵债,过去都是以借债还债、利上滚利的手段应付债权,近年借债困难,则靠签发远期本票和预约栈单来周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困难越来越大。报告书严厉批评申新无组织、无管理,经营毫无系统,结论是:“该公司资力、人力,俱不足以经营此大规模之工业,以致累及方面甚多。长此以往,为害更烈。”报告书提出三条应对方法:(一)由政府责成该公司速行清理,以六个月为限。若清理不成,再由政府派员清查。(二)由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该公司现有九厂,至多以六个月为限;六个月后,依整理所得结果,再定具体办法。(三)在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期内,由政府供给300万元为营运资本。六个月结束,所有盈余或亏损,并入公司债务债权内计算。
陈公博的这一方案,否定了荣氏提出的发行公司债券的请求,以“整理”为名,企图以300万元为代价,攫夺荣氏数千万元的资产。消息传出,荣氏家族气愤难忍,更加恐慌异常。惶急之下,荣氏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以他的资历、能力完全能帮荣氏化解这场危机。这个人就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按薛明剑的说法,“我们找吴稚晖出来讲话,一则因为他在国民党方面能够讲话,二则他与直接经办的官员有矛盾”。
吴稚晖,名眺,后改名敬恒,国民党元老,也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怪人”。他家在无锡与武进交界的雪堰桥,桥南属无锡,桥北属武进,吴稚晖的家在桥北,应该算是武进人。他6岁丧母后寄居在无锡江尖外祖母家,在无锡长大,在无锡受教育,说得一口地道的无锡话,所以他在多数场合自称无锡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