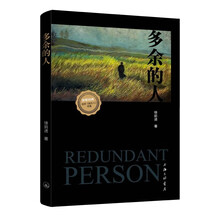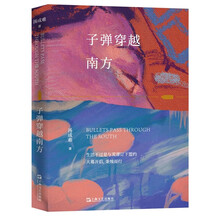我接受护瓜任务时,瓜蛋子只有核桃那么大,可它们像吹气球那样地生长。我猜,它们在听麻雀的吟唱,我甚至感到瓜们幸福的样子,而且,瓜们也在哼唱,后来,我听到风拂过瓜的声音。
我称树上栖的麻雀是“会唱歌的果实”。胡杨树不结果,所以,它十分珍惜栖在它身体里的麻雀,护着掩着。我站在树下,看不见麻雀,只能听见麻雀的歌唱。而且,我想象着麻雀的唱词——有那么多可爱的瓜们当忠实的听众。
甚至,我能听见瓜们发出的微笑——那是甜甜的瓜汁,我以为,只有陶醉在美妙的歌声里,它的心窝才孕育着甜蜜。第一次卸瓜,连队的职工反应是今年的瓜特别甜。
连长认为是选对了土地。这片瓜地成熟的瓜比农场其他瓜地的瓜竞提早了半个月。我看见平时跟我交往的职工——瓜汁的甜蜜很快反映在他们的脸上,我想,那是哈密瓜、西瓜享受了“会唱歌的果实”凝结的微笑,似乎人们在听“会唱歌的果实”的原唱。
连长说:“小伙子,看来,我派你派对了,你把瓜领导得那么甜。”
我笑着说:“我每天都让瓜听歌。”
连长说:“下回,农场文艺汇演,你爆个冷门。”
我说:“我不会唱,我这莫合烟的嗓子,唱得别人非起鸡皮疙瘩不可。我能听见唱,瓜也能听见,瓜一昕,它们就老是笑,笑得一肚子蜜甜。”
连长重重地拍了我的肩膀说:“你在编故事,一个人在那里守瓜就乱编了。”
我的话已经多了——我察觉,我是夹在社会和自然中间的一个角色,两头都没有接纳我,可我能听懂两头的声音。连长怎么理解?再说下去,他一定以为我大脑出了毛病,连长的眼神已流露出疑惑。
还有,连长相信胡杨树的“果实”吗?会唱歌的果实。胡杨树没有刻意结出果实,但那么多的果实不愿意离开胡杨树,果实会飞,它们似乎知道我不会伤害它们。
反正,连长乐不可支,他派车向场部的首脑“进贡”,场部指定我们连里的瓜专门用来接待上边来视察的头儿。我对连长传达的场部“首脑”的微笑无所谓,我欣慰的是“会唱歌的果实”已经得到认可。
连长说:“那是麻雀。”
我说:“我起了个名字,会唱歌的果实。”
连长说:“只要能叫瓜甜,使劲叫它们唱。”
我发现,连长出现,麻雀的歌唱便戛然而止,好似一个猎手潜入了鸟林。我暗暗地希望它们唱起来,甚至,我心里替它们领唱。只有风经过的树叶的喧哗,像是掩护我的“会唱歌的果实”,它们不敢暴露出来。这说明我和连长的差别。
九月,一地的瓜,像戴着头盔的伏兵,大的、小的,都匆匆地赶着去成熟,那是它们的结局—一像是列车即将抵达终点站,透出无奈和仓促,而胡杨树的叶片已经泛黄,成熟的黄色。不过,它的“果实”还是那么天真、执着,照样早早晚晚地吟唱,这是我的时间,我没有钟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