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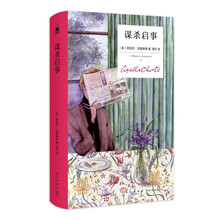

当活着变成诅咒,
亲情沦为束缚,
真的只有死亡才是救赎?
【争议】《绝叫》作者冲击三观的争议作
【杰作】绫辻行人&今野敏:无可挑剔的杰作!
【预见】预见数起轰动日本的护理杀人案
【绝望】一亿日本人正面临的绝望现实
大奖评委全员盛赞,
松本清张之后新一代社会派推理旗手。
如何杀害四十三人,却不被人憎恨?
“我是杀了人,但我的杀戮解脱了那些老人,也拯救了他们的家人。这就是 ‘死亡护理’。”
~~~~~~~~~~
日本推理文学大奖新人奖获奖评语:
【绫辻行人】
能够勇敢直面如此一个极具现实意义和普遍性的重大社会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社会派推理小说。
故事开头便十分吸引人,中期更是引人入胜,结尾震撼又感动,令人心服口服。
【今野敏】
《死亡护理师》是无可挑剔的杰作。故事脉络设计之精妙让我深感佩服。
【近藤史惠】
不论优秀的悬疑性、故事的脉络,还是面对“护理”这一敏感问题时的公正立场,都令人赞叹。
【藤田宜永】
我参加过很多奖项的评审会,但像这本书一样获得全场一致肯定的作品真的少之又少。
《死亡护理师》不论文笔、诡计,还是情节走向等种种方面都胜过其他作品一筹。
此外,每位评委盛赞的重点都有所不同,这也充分反映了这部作品的质量之扎实。
【“他”】
站在被告席上的“他”,前后共计杀害四十三人。发生于“二战”后的连环杀人案中,此案死亡人数最多。被害者几乎都是老人。
在这场审判中,“他”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判决结果除死刑外别无可能。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他”露出了微笑。
【羽田洋子】
被害人家属羽田洋子,在旁听席抬头看向“他”。
洋子的母亲被“他”杀害了。但时至今日,洋子的心里终于再也涌不起对“他”的愤怒和憎恨。
洋子有种冲动,她想去问一问其他那些被害人家属——
喂,你们觉不觉得自己是被“他”拯救了?
【大友秀树】
“他”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到了检察官大友秀树耳中。
“他”应该不会上诉。这一点大友很清楚。
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不光是杀人。罪行暴露,还有法庭审判,甚至死刑,这些都是。
只是待大友意识到一切的真相时,已经太晚了……
羽田洋子 二〇〇六年 十一月四日
同日,下午六点。窗外已经暗了。略微泛黄的荧光灯照亮了卧室。
简直像地狱一样——羽田洋子心想。
“你是谁?你干什么?别碰我!你这个畜生!畜生!畜生!”母亲嘶吼得好像一头母兽。
母亲?
是的。虽难以置信,但这是洋子的母亲。
那个曾经温柔的母亲。
“你最棒啦。你就是我活着的意义呀。”曾经的母亲会当面对洋子这样讲——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当初的母亲,如今正疯狂地甩着干枯的头发,扭曲着行动不便的身体,看起来也不认识眼前的洋子。
就在前一秒,母亲还是偃旗息鼓般地安静。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是母亲的卧室,她半躺在护理床上,既没有睡也不清醒,一副失神的模样。她机械地张口,喝下洋子用勺子喂到嘴边的稀饭。
“妈妈,我要出门了。上不上厕所?”
晚饭吃得有些早,饭后洋子这样问时,母亲的脸色有些不悦。
“嗯?那先上个厕所吧。”
“唔,唔。”
被洋子一催,母亲似乎还不大情愿,晃晃悠悠地起了身。洋子随即搀扶着她走到床边的马桶旁,帮她脱下了裤子,就在那个瞬间——母亲像是忽然回过神了似的,直盯着洋子看。她那空洞的灰色瞳孔深处闪起光芒。然而,映照在那里的却是恐怖和混乱的色泽。
本来安稳的母亲又有发作的架势。
“你……你是谁?”
母亲有些不知所措似的问道。看起来,她是真的不知道眼前的人是自己的女儿。
洋子感到脊背一阵发凉。但她努力保持了冷静,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笑着答道:“妈妈别闹。是我呀,洋子。”
母亲的表情里只写了“恐慌”两个字。
“骗……骗骗……骗子。洋子哪有这么大?你……你是谁?干……干……干什么?”
似乎在母亲的脑子里,洋子还是个小女孩,所以面前的女子看起来陌生又可疑。
就算明白这些,洋子也无计可施。她只有不断地辩解:“没骗你呀。我,我是洋子。”
“骗……骗子!你是什么人?”
暴风雨来了。
眼前是一个陌生的女人。而且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这女人还脱了我的内裤,让我的小肚子暴露在外——母亲恐怕已经被这样的妄想支配了。
母亲混乱了,发狂了。
她的身体在挣脱,不停地把自己的女儿喊作畜生。
“妈妈,停下!危险!”
洋子紧抱住母亲,试图限制她的行动。
“嘁——!”母亲发出怪异的声音,伸长了脖子,对着洋子的手腕一口咬了下去。
“呀!”洋子不禁撒了手,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洋子的左臂,手肘下方,出现了母亲的一排牙印,那里正往外渗着血。
“妈妈、姥姥?出什么事啦?”
儿子飒太出现在房门口。刚才他还在客厅打盹呢,可能听到动静醒了吧。
“啊——!”母亲发出尖锐的叫喊。
“啊——!”飒太也学着姥姥的样子喊。
小飒太还不能理解姥姥的状态。在他看来,姥姥可能在逗他玩儿吧。
“你是哪来的小子?小孩子来偷东西吗?”
母亲面目可憎地瞪着飒太,口沫横飞。
这明显带有敌意的表情和言语让飒太明白了对方并非玩笑,他的脸一下子僵住了。
“姥……姥,我,是飒太!我不是小偷!”
飒太还是个孩子,一定是受了惊吓,他的眼角都湿润了。
“是呀。妈妈,你误会了,不是你想的那样啊。飒太是我儿子,是你外孙子呀!”
“啊!”
母亲突然像被电打了似的,小声惊叫着抬起了下巴。紧接着,响起一阵“噼噼啪啪”的动静,就像有什么东西被撕裂了。
随着那阵动静,黏液状的粪便滴滴答答地顺着母亲裸露的屁股流了下来。
洋子无法控制自己,尖叫起来。
和粪便一起喷出的还有尿液,母亲的大腿湿漉漉的。混合在一起的粪和尿散发出强烈的恶臭,直往鼻孔里钻。
飒太也顿时变了脸色:“哇,姥姥!尿裤子!”
失禁的母亲直勾勾地盯着滴落在地上的大便,若有所思地拿手指抠了抠:“哎哟,真浪费。”
母亲将指尖的大便含进嘴里,就好像是在舔豆沙馅儿。
她已经忘记了那是刚从自己身体里流出来的东西,还以为是什么食物。
“姥姥!臭臭不能吃!”
眼前的诡异事态令飒太大叫起来。
“住手!妈妈,住手啊!”
洋子抱着母亲试图制止她的行为。
飒太走上前来,似乎想帮助妈妈。
“别!飒太,别过来!”
飒太不顾妈妈的阻止走上前来,却因踩到地上的粪便而脚底打了滑。飒太“哇”地叫了一声,跪倒在洋子脚边。有一部分被尿液稀释了的粪便随着飒太的踩踏而飞溅起来,弄脏了洋子的脚和飒太的脸。
“你干什么要过来!你傻吗?”
洋子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还伸手打了飒太一个耳光。
飒太的脸颊红了一块,猛地大哭起来。扇儿子耳光的触感在洋子手心留下一阵温热。
自己的儿子沾了一身自己母亲的粪和尿,还在抽泣,那副模样令洋子胸口一紧,硕大的泪滴便从两眼流了下来。
而另一边,母亲方才的狂暴似乎已平息,回到了平常呆滞的模样。
“洋子?小飒?”母亲像是认出了面前的女儿,但是那瞳孔却失了气力,混浊不堪,“这是怎么了?”
母亲的眼睛什么也没看,也不是明确地向谁发问,她只是问。
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儿子,粪便、尿液、恶臭,还有眼泪。
这是怎么了?真正想知道答案的是洋子。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眼前的地狱状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至少在洋子刚开始和母亲一起生活时还不是这样。
X县八贺市是一处四面环山的盆地,夏季闷热犹如火锅,冬季从冰冻的山上吹下的寒风让这里冷得犹如冷库一般。昭和时期这里是一座卫星城,人口是膨胀了,却没有像样的产业,等到经济泡沫破灭之后,这座城市就开始缓慢但真切地丧失活力。
洋子在婚姻失败后回到城镇上的娘家,那已是六年前的事了。母亲慈祥地接纳了带着刚出生的飒太返家的洋子。
那时候母亲七十一岁,洋子三十八岁。
父亲已经去世,养老金是母亲仅有的收入。洋子是唯一的劳动力,然而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对单亲妈妈来说还算不上照顾,每一天洋子都拼尽全力,就为了温饱。
即便是那样,那时候的生活也不算是地狱。
母亲还常常向洋子表示感谢说:“你跟我一起住可帮了我大忙。”她也乐于跟外孙一起生活,“每天都能见到可爱的小飒,真是令人开心。”
三个人,祖孙三代,日子虽然清贫,但还算快乐安稳。
直到三年前,一切突然改变了。
母亲本来就有点贫血,一直在服用补血药,自从和洋子母子一起生活后,她就以“症状也不明显,还是得节约些”为由停止了服药。
或许这就埋下了祸根。母亲在车站时头晕了,从楼梯跌落,伤情十分严重,腰部和双腿开放性骨折。生命虽无大碍,康复情况却不是很好。腿部功能几乎丧失,仅凭自己而无外力辅助时无法自由站立。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应该就是地狱生活的开始。
除了工作和育儿,洋子还得负责护理母亲。当时护理保险制度已经开始实施了,但要享受该制度压根儿谈不上方便。而且就算在保险补助范围内,对于仅凭洋子一人支撑的这个家来说,母亲的护理费用依然是巨大的经济负担。政府提供的护理服务仅限于洗浴等无法单独完成的困难项目,日常护理还是得靠洋子独自完成。
即便如此,最开始时洋子还是觉得,母亲的护理工作虽算不上快乐,但给人以充实的感觉。周一至周五,洋子在超市收银台上班,周末时,则在小酒馆里招呼那些醉汉。难得的休息日,便将母亲扶上轮椅,带着飒太一起去附近散步。洋子的身体已经吃不消了,但却在内心欣赏着为了家人牺牲自我的自己,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喜悦。
亲情,家人之间的亲情。
这个美丽的辞藻就是促使洋子奋斗的动力。
如若母亲就此安详度日,感谢洋子的自我牺牲,或许洋子还能从那种生活里感受到更多幸福。
然而现实却往相反的方向发展,还算幸福的生活开始一点点地崩塌。
母亲几乎得在全方位的护理下才能生活,但洋子外出工作时,每天大部分时间她都不得不独自一人在家。母亲是个喜爱外出的人,以前就算没事也会时常出去走动,如今却不得不过上一种完全相反的生活,这使得她的心理逐渐产生了变化。
她开始抱怨起哪怕一丁点的小事,每当洋子要出门上班,她就恨恨地抱怨道:“明知道我一个人在家出不了门。”可假日里,当洋子邀她出门散步,她又以“我不想去。看到外头那些人走来走去影响心情”为由,躲在家里闭门不出了。对于照顾自己吃喝拉撒的洋子,她非但不感谢,反而处处找碴儿闹起别扭来。
母亲的心情洋子也并非不理解。七十年了,一双理所当然该支撑身体的腿却突然没了用处,连外出都不能随心所欲了。这一切必定令她感到陌生而恐惧。
并且洋子心里始终有种沉重的负罪感,她觉得母亲受伤,是和他们母子一起生活所导致的。
当初母亲收留了我和飒太,现在轮到我来照顾母亲了。
洋子这样想着,竭力为母亲付出。
然而,从母亲的嘴里再也听不到感谢,给她做吃的被抱怨“难吃,咽不下去”,给她擦身子被指责“好疼,小心点”,想安慰她却被要求“别故意刺激我”,最后竟发展到“看到你的脸我就心烦”这种话。
就这样洋子也忍了。
其实不只身体,她连内心都已开始难以承受,但她选择了无视。
我不痛苦。我不痛苦。我不痛苦。
真正痛苦的是母亲呀。我不痛苦。
我不是那种不想照顾自己母亲的薄情之人。
我们母女间的亲情不会输给这种困难,没有输给这种困难。
她这样说给自己听,近乎强迫。
可母亲的情况却落井下石般一天比一天坏。
除了讲坏话、爱抱怨,有时明明刚吃完饭,她却坚持认为还没吃,还会呼唤早已去世的父亲,这种明显不合常理的行为越来越多。有一次她还在大夏天说“天都这么冷啦”,然后穿上了毛衣。明明没人说话,她却怯怯地说“别那么大声发脾气嘛”。有时候,她连飒太和洋子都认不出了。
失智症。
这个病以前叫“痴呆症”,但好像现在都不这样叫了。
它不仅造成记忆能力和思维能力减退,还改变了母亲的人格,让母亲不再是母亲。
它还无情地撕裂了洋子一直以来的精神依靠——家人之间的亲情。
洋子尽心尽力地照顾母亲,可对方却认不出她,还怯生生地问她“是谁?”,对于此时的母亲来说,洋子并不是女儿,她是一个不明身份的陌生人。比起被抱怨、被指责来说,这更令洋子遭受打击。
失去了亲情的“家人”,只不过是一个冷漠的词语。
即便母亲在意识上成了另一个人,但母亲永远是母亲,不论去查户籍或者验DNA,这都是一个很简单就能被证明的事实。
母亲常常认不出洋子。但她仍是家人,必须去照顾。留给洋子的只有这种尽义务的想法。她无法欣赏这样的自我,空虚和疲劳感越来越重。
就这样,地狱显现了。
走到这一步,洋子承认了。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照顾母亲很痛苦。我想逃离这地狱,哪怕早一天也好。她想。
洋子安抚着仍在抽泣的飒太,勉强擦去了房间里的污秽并喷上除臭剂。她根本没有时间去彻底打扫,也没有力气。
她把飒太从卧室带到客厅,然后用DVD机播放了租来的卡通片。
飒太听到节奏欢快的片头曲,随即停止了哭泣,紧盯着电视。
洋子回到母亲的卧室,从衣柜里取出几根皮带,站在母亲身边。
母亲躺在床上目光呆滞地看向天花板,她已经忘记了刚才的癫狂,仿佛一切都是假的。
“母亲,对不起了。”洋子轻声说完,就用皮带将母亲的右手绑在了床边的铁管上。
母亲茫然,没有反应。
接下来她以同样的方式绑上了左手。母亲的下半身活动不便,这样的处理足以使她无法动弹。不过洋子还是把脚也绑上了,以防万一。母亲被紧紧束缚在床上,仿佛一只被制成标本的昆虫。
失智症发病后,母亲开始趁洋子不在家时自己爬下床。她未曾爬出家门,但家里是无障碍通行的设计,像她那样跟毛毛虫似的四处乱爬已经足够危险,更别提好几次她都直接从床上跌下来过。
所以,每当洋子因为上班而长时间不在家时,她就像这样把母亲绑起来,纵然那样的母亲凄惨不堪,仿佛被夺去了作为人的某种重要东西。
母亲有时候十分抵触手脚被束缚,但今天并未反抗,可能因为刚才闹过一场了吧。狂乱过后的母亲,总是像活死人一般没有生气。
洋子匆匆化了妆,带飒太出了家门。
这是一座不大的木结构平房。听说是已过世的父亲在洋子出生前盖的,所以该有四十多年了。石灰墙壁已有多处裂痕,如今已不常见的白铁屋檐下耷拉着坏掉的雨水管。院子就丁点儿大,也早被枯叶和杂草占据。
洋子拉着飒太的手,沿着已开始昏暗的道路快步疾行。
今天白天还挺暖和,太阳落山后却一下子冷了起来,俨然是冬夜。
间隔数十米设置的路灯的灯光也是淡淡的冷色,使人的体感温度更低了。
飒太只穿了件运动外套,似乎也不觉得冷,口中唱着动画片的主题曲,一路蹦蹦跳跳。他的心情很不错,刚才被打的事情好像已经忘记了,被洋子拉着的小手热乎乎的。
二人正前往车站前的一家小酒吧。酒吧里没有年轻姑娘,也没有阔气酒客,老板娘倒是脾气很好,店里的氛围也不错。洋子每周末晚八点开始在那儿上班。老板娘把洋子当作自家人照顾,告诉她上班时可以让飒太睡在酒吧的二楼,平时她自己就睡那里。好在飒太不抗拒一个人睡,一旦睡着了,中途也不哭闹,于是她便感激地顺着老板娘的意思做了。
在单调的步行过程中,洋子不自觉地想起了一些她不愿去想的事。
如今牵着飒太的这只手,也是刚才打过他的那只手。
她离婚的原因是丈夫的家庭暴力。两人交往时,她就发现了对方的强势和暴力倾向,可还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跟他结了婚。不曾想,前夫居然不顾洋子还怀着身孕对她动粗,让她险些因此流产。即便是现在,回想起那件事都仿佛一场噩梦,不过也全因它发生了,洋子才终于动了离婚的念头。她不顾一切地要跟对方断绝关系,连赔偿金和抚养费都没拿到。
正因为洋子有这样的过往,离婚之后她才发誓以后绝不对儿子动手。可自从母亲需要人照顾后,她却开始频繁破戒了,哪怕心里知道不应该,气上心头时却总也管不住手。
动手程度都和今天差不多,顶多就是脸上打一巴掌,但这也让她很不是滋味,看到儿子捂着被打过的脸颊哭时,她更是喘不过气来。
每当有新闻播报小孩因为父母的虐待丧命,她都会内心不安。
我和那种父母不一样。我不会为了自己而牺牲飒太。我要保护飒太。
可无论她如何说服自己,不安的情绪还是越来越重。
如今握在手里的小手,也正握着我自己。我真的能保护他吗?
洋子的心里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曾经忍受丈夫的暴力,现在还要忍受看护母亲的煎熬。
这,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我得忍到什么时候?
跟丈夫的关系通过离婚断绝了。可是,母亲呢?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上门问诊的医生还说:“老人家身体状况挺健康,一定长寿的。”这不禁让洋子面颊抽搐。
长寿?
假设能活到平均寿命,那还有十多年。
就一直这个样子?
小飒太在一点点成长。今年他六岁。明年春天就上小学了。他的语言表达越来越完整,能表达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但是,母亲不一样。母亲已经不会再成长了。今后恐怕只会变坏,绝不会变得更好。日复一日,她将越来越难以沟通。
日本是个长寿的国家。一直以来洋子都茫然地认为这是件好事,现在才意识到那是极大的误解。
不死,再没什么比这更令人绝望了。
她打心底厌恶怀有这种想法的自己。
序 章 二〇一一年 十二月
第一章 天堂和地狱 二〇〇六年 十一月
第二章 咿呀作响 二〇〇七年 四月
第三章 失去 二〇〇七年 六月
第四章 长传 二〇〇七年 七月
第五章 黄金律 二〇〇七年 八月
终 章 二〇一一年 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