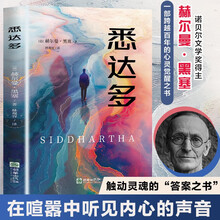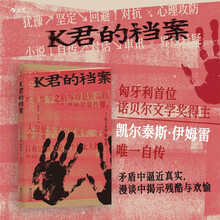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8-)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已三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欧茨是一位多产作家,自1963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北门边》(By the North Gate)以来,迄今为止已发表长篇小说四十余部,另著有多部短篇小说、诗歌、戏剧、随笔、文学评论等文集。1970年以长篇小说代表作《他们》(Them)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人间乐园》(A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1966)等5部小说曾得到图书奖提名奖,《漆黑的水》(Black Water,1992)等3部作品曾获普利策提名奖,《大瀑布》(The Falls,2004)荣获2005年度法国费米纳文学奖。
欧茨素以揭露美国社会的暴力行径和罪恶现象而闻名。题材涉及政治,法律,宗教及强奸、乱伦、谋杀、骚扰、食人、折磨和兽性等。作品整体上构成了一幅当代美国社会的全景图。作品大量运用心理分析、内心独白等意识流手法,尤其擅长营造神秘恐怖气氛,使用心理现实主义手法,注重用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因此被誉为“女福克纳”。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