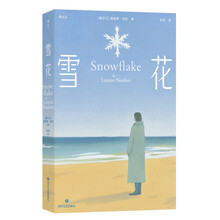第一章
远航,为人生寻找方向
1. 既面朝大海,又通往灵魂
在今天这个时代,地理大发现早已成为过去,人们不必急着外出旅行。就算必须出行,也有更快捷的方式。现在,如果有人要驾一艘小船扬帆出海,那看起来至少是他的判断力出了些问题。有临床依据可以证明,这的确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当然这样想就会让其中的诗意荡然无存。就算撇开诗意不谈,这也是一种奇怪的习惯:开着小船驶向大海,在15节的风速中凭栏远眺,独自一人,直到深夜。
我知道,这是种病。曾经多少次我有过这样的冲动,但都抑制住了,清醒过来,掉转船头回港。驾着小船整晚出航,无论是独自一人还是和别人一起,都纯属怪癖。即使说得文雅一点,也是一种耍帅式的冒险。不管有多安全,这终究是不守规矩的行为,偏离了人类一般的生活方式。很多人都向往这条路,但真正下决心走下去的少之又少。我听说现在世界上,曾经独自驾船、仅在风和水的动力带动下环游过世界的人,甚至还没有去过外太空的人多。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惊讶,如果你和我一起走过这段旅程,你也不会感到惊讶。
驾一艘小船扬帆远航,这件事吸引我的地方,就跟小时候野外宿营一开始吸引我的地方一样。两者都是很简单的过程,或者更准确地说,都是用来获得简单生活的过程。一登上船,生活就回到了其原本的状态。与之相比,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变得纷繁复杂。首先我们得去上学,去工作,去结婚。接下来还没等察觉到,我们就被卷入了生产消费的循环中。这是个永动的旋风,我们被这停不下来的风吹到了空中,直到大约75年后我们又被扔回地面上,临了都没想明白时间和金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我们消费,于是我们生产;我们生产,于是我们消费。
泛舟海上,消费和生产的过程便合二为一了。这便是其美妙之处。风和水既是景观,也是动力;既是方法,也是媒介。不断吹拂在脸上的风让我们着迷,同时也推动我们向前进。大海将我们托起,同时也提供给我们食物。那里没有沃尔玛超市。那里什么都没得买。那里只有生存。
在迈阿密,都市的天空因灯光而燃烧,街道因川流不息的轿车、卡车和行人而沸腾。然而就在离这片海岸仅仅3英里的地方,晚上便没有了车流,没有了噪声,没有了灯光,有的只是月亮和星星。广阔的海洋是地球上唯一一片没有被人类长期占据的地方。
我不知道,在安纳波利斯八月的那天,到底是什么力量驱使着我又走上了航海这条路。也许那是一种无需用太多言语来形容的渴望,一种要将命运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渴望。我必须说,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跟自传《巴比龙》的作者一样。在电影里这一角色是由史蒂夫?麦奎因扮演的。他在暮年终于逃出了恶魔岛,一跳下海、爬上椰子做的筏子,他就对着看不见的听众叫喊:“老子还在这儿,你们这帮混蛋!”
可能有些读者还不太了解我的为人和出身,误以为航海只不过是有钱人的消遣娱乐罢了。对于这一点,我想花些时间做一下说明。有些圈子里的人的确把航海当作休闲活动,但一般来说,他们喜欢的是比拼速度,而不是泛舟漫游。他们会和一帮志趣相投的朋友在海湾里呼啸尖叫,完事后把自己造价昂贵的船绑到游艇俱乐部的柱子上,跑到俱乐部酒吧里享受胜利的滋味或者盘算如何复仇,最后开车回到自己价值不菲的家中,等待下一次比赛的到来。对于他们而言,航海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不是一种心境,也不是一种处世之道,它更像是在水上进行的高尔夫球赛一样。而有一类人与他们截然不同,他们是一些居住在海上的农民,就像是海上的吉普赛人。尽管我还不能真正称自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我对他们心存敬仰已久。
事实上,我在海上所见到的航行者当中,有钱有势的只占极少一部分。很多人仅仅是比银行家们最害怕的那种人略好一点罢了。他们也有自己小小的梦想,但顶多就是希望老天能再给点助推的风,还有半英尺的管道胶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关他们什么事,还不如给帆船装上点耐用的舷墙呢。有句名言说,有钱人和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是不一样的,而真正的航海家也是与有钱人沾不上边的。他们这些人痴迷于航海,但基本都是令人无法忍受的铁公鸡。在世界各地的豪华船坞中,他们遭人鄙夷,被称为“破叫花子”,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的收支清单惨淡不堪,还比不上大学橄榄球比赛后最普通不过的车尾野餐会。这些不修边幅的老家伙们整天穿着脏兮兮的卡其裤,光着脚踩着平底便鞋,挑选着当地船上用品商店里的清漆油壶。
这里我所指的可不是那些“游艇爱好者”。那是些在度假船坞中享受锦衣玉食、在内陆航道里品尝美酒佳酿的人。他们整天向往的是迈阿密的分时度假,而不是麦哲伦式的环球航行。伴随他们梦想的是内燃机的袅袅青烟,而不是海风或想象。我也不是指那些给到加勒比的度假者们提供帆船租赁的人。他们在码头锚地间穿梭时,一般都开得小心翼翼的,生怕把船碰坏。
对于我来说,航海是一种看待生活的方式,也可以说它什么都不是。它是一门哲学,不是写在日历上星期五董事会和星期日早中餐之间的一项安排。我所讲述的这种探险旅程可是租借不到的,就像真正的爱情是无法用钱租到一样。它也不仅仅是一次“经历”,不同于打一次保龄球或者抽一根上等的雪茄。驾驶帆船航行是驾驶者与船只的喜结良缘,而且就像任何健康的婚姻一样,即使悸动于新欢的出现,这层关系也总是愈加密不可分。巩固这层关系的是包容的耐心和共渡难关的承诺。耐心和承诺就是航海家的灵魂。生活、感情、航行,要么全情投入,要么就请出局。
我写这本书目的之一是为自己的灵魂导航——去为我的人生找寻方向,去阐释动与静、变化和偏差,去度量时间和距离,从而使我能在托尔金所说的“大道”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也启迪他人,照亮他们的旅程。每次在海洋里的航行都是双向的,既面朝大海,又通往灵魂。海上的航行可能会遇见风险,但只需做一些计划和准备,采取简单的措施和步骤就可以解决。然而,通往灵魂深处的路线图就没有那么容易绘就了。这一路上定是艰险重重,猛虎当道。所以,带着这些想法,让我们出发吧。
2. 登上梦想之舟,乘风破浪
2009年8月的一天,我乘飞机来到了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下了飞机,我径直走向了机场下面接送旅客的街道。从罗利市飞到那里,我是轻装上阵的,除了手里提的一个小包之外,没带什么别的行李。走出机场,早晨的阳光明媚得刺眼。每年夏天马里兰州都会经历一段潮湿无风的热浪,尽管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但我觉得它让这里有了几分迈阿密的感觉。
我的船名叫“吉普赛月光”号,是艘32英尺长的单桅帆船。6个月前我带她去安纳波利斯城外的玛格西河上的一处码头进行了一次大修,现在她正停泊在那里。自从她离开造船厂开始航行以来,已有30年之久,时间给了她创伤。为了能让她再一次出海航行,我们足足花了5个月时间对其进行必要的修复。过去的几年,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些恢复期,尽管我的创伤不像船上的这样看得见摸得着,但从中恢复对我来说却有很重要的意义。而现在,“吉普赛月光”号已经准备好出航了,我也一样。
我的姐姐和姐夫把我从机场直接接到了船上。以前我到这里来,是一定要去住在附近的我哥哥家吃顿午饭的,他和他的家人会请我们吃马里兰特色的蟹肉蛋糕,然后向我道别。不过这次我没去。过去的一年半里,当我的船停泊在安纳波利斯时,我是多么期待周末能够到一些地方的海湾里航行。从小我就向往有一天能驾着自己的船来到这些地方。现在,我人到中年,已经驾驶着“吉普赛月光”号去过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国会所在地的州议会大厦,也去过我18岁时进行法务实习的地方,当时的那段经历使我再也不想进入政坛。重游故地非常开心,我拜访了当地的亲朋好友。回首往事,也觉得很有意思,25年前,我曾经得到了在两座城市的工作机会,一个在休斯敦,另一个在巴尔的摩,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另外一个,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呢?
我曾计划证明托马斯?沃尔夫关于回家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不久后,这项计划便遭遇了现实问题。我在德克萨斯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客居了30年,这让我更加习惯于南方的温文尔雅,而对北方彪悍好斗却越发地看不顺眼了,不仅仅是因为那里的开车者不愿意让人搭便车。我曾经在靠近巴尔的摩的一处海湾与另一艘船相交而过,我趴在船舷的栏杆上对着它的驾驶者微笑,准备与他互致问候,就像在南方航行时必然会发生的一样。结果我却听到了一串脏话(因为我靠得太近了),这让我大吃一惊,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说了句“实在抱歉”,就掉转了方向。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似乎很多人从小就是随时准备要跟人打一架的样子。于是我发现了,南方除了气候更温和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也是更温和的。我真的好想再次踏上“吉普赛月光”号,扬帆远航。
吃午饭的时候,家人问到了我的计划,我一一做了解释。他们觉得,拿骚是那么远,几乎遥不可及。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毕竟一个人独自驾船出海这种事不是每天都发生的,这事儿听起来比实际上更加需要胆量。我理解他们的担忧,而我自己也有着同样的顾虑。浩渺的大海可不是好惹的,即使是在最好的天气条件下。
当置身于驾驶室时,我感觉自己就像回到了家里一样,尽管我也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这一点的。我在马里兰州长大,母亲离异后带着四个孩子,我是最小的,而且比老三小10岁。两个姐姐一直对我非常宠爱,我哥哥还在家的时候我太小,还认不出他。后来,在我两岁时,酗酒成性的父亲遗弃了我们。我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他的离开对我影响有多大,因为这让我没有办法实现大冒险的梦想。海上航行就像是只有在好莱坞的电影里才会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可望而不可即。在孩提时,我在小得多的范围里实现了梦想,比如在附近的小河或水塘里玩,或者在其他男孩父亲的帮助下参加童子军活动。回想那段时光,我就记得钓鱼归来走过的小路、烧柴火的烟味和生活最本真的样子,无论那有多么短暂,还有就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郊区“开袋即食”的惬意生活。那些逃学跑到树林里玩耍的日子真的很开心,让我的想象力可以飞翔在一个远离老师和考试的世界里。我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不过,对那时的我来说,遥远的切萨皮克海湾和海湾以外的大海才是更神秘的地方。我只有偶尔在哥哥杰伊的带领下才能接近那里,他会带我和姐姐们乘坐各种平底小渔船和小划艇出海。这些船有些是他租的,有些是他买的,还有一条是他自己造的。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哥哥驾驶着一艘罗得岛造的19英尺长单桅帆船,乘风破浪,从南河的入海口冲出,直奔切萨皮克海湾的广阔水面。天际线上的树木和房屋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汪洋和未知的远方。我看了看桅杆下面那个小到只能装下一个行李包的船舱,不禁想到,如果我们就这么一直往前走下去,会发生什么。
不过我们没有继续往前走。当租船的时间到了之后,我们就小心翼翼地把这艘无畏的梦想之舟往回开了。付完钱,我们又回到了陆地上,开车回到了城市里。然而,那一刻和其他类似的经历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我脑海中。多年以后,当我借走杰伊的14英尺单桅帆船,决定开始独自航行时,我仍然会时不时地回想起这些情景。
3. 当日子一天天变得模糊
时间是1976年,那年我18岁,哥哥杰伊去度蜜月了。我借了他的船带心爱的女孩出海,这样的初次约会看起来非常美妙。然而我的计划却因为一股狂风而泡汤了。风吹来时,我没来得及抓住主桅杆的操纵索。于是转眼之间,刚刚还骄傲矗立着的主帆就被吹倒了,船也随之倾覆在水里。女孩自己游上了岸,而我像落汤鸡一样坐在翻倒在水面的船壳上,呆呆地等着海岸警卫队来救援。最终他们来了,还没等把船翻回去,就用不可思议的速度把它拖回了浅水区,拖的时候桅杆咔嚓一下断掉了。
这次在玛格西河上的首航可谓出师不利。几年之后,二十几岁的我在加尔维斯顿湾驾驶“伊特莱度”号时学到了很多航海的知识。它是我拥有的第一艘船,是一艘小型的单桅帆船,船头到船尾共17英尺,中间只有浴缸那么宽,配备的舷外发动机就像是挂在艉板上的一个搅拌器。那时我在休斯敦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里做初级律师,公司的一位资深合伙人有一艘37英尺长的豪华帆船,停泊在最高级的游艇俱乐部里。每个星期一他都会跑到我办公室问我:“这周末打算去水上兜一圈不,赫尔利?”基本上我都会答应去,然后我就像玩跳房子游戏一样驾驶着“伊特莱度”号走南闯北。我去过波浪不断拍打的锚地,碰上过倒霉的事,遭遇过暴风雨。这些经历跟合伙人的周末航行比起来,简直就像是在玩命一样。他一般就待在船坞间的停泊处,从不离开制冰机半步,而多数的大型游艇大部分时间里都停在那里。哈尔?罗斯,一位传奇的远途航海家,同时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曾经将这种只停在码头里的船称为“远处传来的人猿泰山的嚎叫”,因为它们的作用是证明其富贵主人的男子气概。这些人在遥远的写字楼里拼命工作,梦想着去南方的大海,不过从来都不会真正出海。而我也有着这样的梦想。
1986年,我在德克萨斯州博蒙特市又经历了一次无关痛痒的失业。回家的路极其漫长,只有一些斯塔基饭馆偶尔出现在那条一直向前延伸的东德克萨斯公路上。而就在这条路上,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当时我和我妻子都只有20多岁,还没孩子。我们终于上完了法学院的课程,也可以轻松地延迟偿还助学贷款。本来我是可以在公司打拼、争取成为合伙人的,这样会让我很有满足感,可是我这样做的意愿并不高。当时我们拥有一艘1981年产的30英尺长凯普多瑞牌快艇,名为“安妮?阿伦德尔”号。通过驾驶这艘船,我已经学会了很多航海的知识,可以使它一直保持正确的航行船姿。我想,这应该是个绝好的机会,让我能够清空一切,扬帆出海,到海岛上待一段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已经记不清当时为什么没有这么做了,也想不起来是谁要留下来的。不过这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这么做。相反,我们选择建立一个家庭,在我们的职位上努力升迁。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在那之后,有个更好的消息降临了,应该说是两个:我们的儿子出生了,18个月后,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本来我已经被驱逐出玩具王国,这下托自己孩子的福,我又可以在那里面玩耍了。我们一家搬到了东海岸,这样离亲戚们近一些。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上开始了新的法律业务,同时开始学做一名父亲。
到了90年代中期,一等到我的孩子们岁数足够大,我就开始带他们坐独木舟去野外游玩,也开始写一些游记,并送去发表。随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经验越来越丰富,我们的航行也越走越远,去的地方越来越有挑战性。我们的脚步一直延伸到加拿大和辽阔的北方。我又变成了当年那个逃学跑到树林里玩耍的小孩了。不过现在我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本,可以向自己的孩子们展示我小时候只能在脑中想象的远途探险。在8年的时间里,每个月我的孩子们至少有一个会陪我去野外探险,有时会持续一个星期之久。我们的航行经过了50多条江河湖泊,它们遍布美国各地,还包括加拿大的两个省。那些与孩子们一起度过的宁静日子终究会逝去,就像所有的童年都会过去一样,但当时我和他们都不曾预料到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1998年,一家大型的诉讼机构邀请我去担任资深律师,我离开了北卡罗来纳的海边,告别了小镇生活,举家搬到罗利市。在度过了10年悠闲自在的日子后,突然间我又回到了快节奏的商业世界。最初在罗利市的几年里,我担任全职律师的同时还继续带我的孩子们划船旅行。然而,到了2004年,孩子们都已经进入青春期了,很自然地,他们的兴趣转向了朋友和运动队,而不是跟爸爸一起出去野营。同时,我自己的精力也越来越多地投入到了律师事务所的业务需求中。于是,我离开了荒野,停止了写作。业务量激增,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每一天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已经记不清具体都发生了些什么。而就在日子一天天变模糊的时候,我25年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4. 按下人生的暂停键
我决定不把我婚姻的失败原因写出来,甚至不做任何间接的透露。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尝试了各种文风和开头,才找到一种可靠的方式避免这样做。毕竟在婚姻上,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彼此都很难接受对方的说法。
现在我得以写出这些东西,正是因为这次旅行和这本回忆录是在离婚的煎熬中诞生的。我希望从新的视角探视人生的意义,借此得到一些重要的感悟。别人可以对我的所作所为加以评判,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去尝试这么做了。
威廉?马克斯韦尔曾经写道:“当我们谈论过去的时候,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撒谎。”抛开其他不谈,我想以我现在要说的话来证明他这个观点的错误。虽然我的婚姻就跟其他所有婚姻一样,出现了问题一般是夫妻双方都有责任,但这次婚姻失败应该完全归咎于我,因为我有了外遇。
写出这几个字终究是太简单的一件事。文字无法将所发生的一切描述出来。更糟糕的是,一个人在当众忏悔的时候,往往带着自我庆祝的意味,懊恼悔罪总是附带着一种假惺惺的虔诚。然而,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对自己的虔诚程度并未抱有幻想,也没想要去恭喜自己做成了什么事。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被自己所写的关于婚姻的文字困扰得心神不宁,那是我在1998年秋天发表的一篇散文:
时光荏苒,终将有一天,我们对彼此许下海誓山盟,这庄严肃穆的话语将我们从任性放纵的深渊中救出。那一刻起,我们信守诺言,只因那是一个承诺,随之而来的是妻子贴心的信任和小孩喃喃的梦呓。因为彼此信任,所以我们可以不受拘束地以双方的差异为乐,无须忌惮因为彼此的不同而分手。因为可以不受拘束,所以我们可以享受一直以来所追求的平和、快乐与满足。
这篇散文几乎是我收到读者邮件最多的一篇。的确,这些文字是很有感染力,但我现在发现,它们已经不仅是对他人的劝勉,对我自己也敲响了警钟。当时对我来说,夫妻之间的不合使得双方关系越来越紧张,我们无法以此为乐。然而,因为我自己也是离婚家庭的孩子,所以以前总是暗下决心,决不让自己的小孩也经历这样的痛苦。为了减轻自己对于夫妻不和可能导致离婚的不安,我决定大胆地将这一点写出来给大家看,以此在自己对妻子的承诺上“加倍下注”。这些话我当时奉为金科玉律,现在也仍深信不疑。我曾希望通过它们使我自己知耻而后勇,信守承诺。
然而,我发现自己竟是恬不知耻的。2005年11月,在一个温暖如春的日子里,我将所有的警告都抛到了脑后——不论是自己给自己的还是别人给自己的——一股脑儿跳进了万丈深渊之中。
就像一个喝醉酒的旅客飞奔上一艘已经着火、正在下沉的开往迪斯尼乐园的船一样,在与一位有夫之妇偷腥时,我说服自己,我的确享受到了快感。而她也乐在其中,和我一样,已经分不清对与错了。当然,这只是在欺骗自己,与所有其他的婚外情一样。对那些因此受伤最深的人来说,这是极其残忍的。
我写这些并不是希望朋友们鼓励我说:“好了,别太自责了。”这种事情我自己完全做得到。我很清楚,夫妻间的不忠行为并没有我们想象或希望的那么少。有种观点现在在法律和政治领域非常流行,那就是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认为“好人”就永远会做正确的事。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只存在于小说之中吧。乡村音乐里的智慧教导我们,自从“人类的堕落”以来,每一个人都属于“爱欺骗的种群”。无论在生活的哪个方面,只要有巨大的诱惑,人们就会如此。为了保持谦卑,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不应该由自己犯下的错误所定义。一艘船的航行轨迹可以告诉你它去过哪里,但无法告诉你它即将去往哪里。
我经常想起耶稣基督。他肯定知道彼得总有一天会背叛他,但仍然将王国的钥匙交给彼得。他并没有以彼得的缺点来定义这个人,我们也应该这样,不要以自己的缺点来定义自己。的确,深陷自责的泥潭比原罪更堕落、更傲慢,因为这是将自尊的价值置于上帝的宽恕之上。自尊心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寻找,却很少找到的,而上帝的宽恕则是我们很少追寻却已经得到的。
我对神的恩典深信不疑,甚至在最灰暗的日子里,当我彻底迷失方向时,我依然能感觉到上帝就在我身边。在过去的几周时间里,我接受了一位修女耐心的教导。她尽管一生未嫁,但在帮人解决婚姻中的问题方面却是出奇地有经验。一开始我还有些不愿意,后来却对她满怀感激。我明白了婚外情并不是两位灵魂伴侣缠绵悱恻的浪漫,而是两个沉迷者自我堕落的悲剧。可是,就算我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就算这给了我许多慰藉,却不能弥补我所造成的创伤。
这段婚外情最终不了了之,但我妻子头脑比我清楚,也比我更有勇气去承认发生了什么。2006年9月,她要我走。于是,月底之前,我离开了这个家。一年之后,在经历了各种匆忙的约会和失败的恋情之后,我又回到了她门前,请求她原谅我,并跟我破镜重圆。但这两点都被她拒绝了,没人会觉得她这么做是不讲情面。
我并没有逗留。我懂得了,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们总还是得走出灰暗的日子”。分居一年后,我找到了一个专门为离婚者提供精神支持的组织,我真希望离婚后的第一天就找到它。我还加入了一个男士学习圣经组织,与比我年长比我有智慧的人交谈。他们劝我停止约会,好好反省一下,对情不投意不合者的追求是如何导致自我毁灭的。我还读了一些关于人生界线的书,找回了羞耻感——没错,羞耻感——也找到了重新站立起来的勇气。我挣扎过,跌倒过,但再次尝试一步一步往前爬。
我在巴尔的摩下了飞机,找到“吉普赛月光”号并带它出海的时候,已经离婚快3年了。那时候我对一件事情感到很骄傲,就是我并没有再去找曾经与我搞婚外情的那个女人。然而除了这一点小小的胜利之外,我的生活已经变得面目全非,3年前我根本没法想象。我遭遇了孤独和失败,孩子们不再相信我了,曾经亲密的朋友们也离开了我。工作上我大不如前,离婚协议正式达成后不到一年,我又经历了第二次“离婚”:我待了11年的律师事务所全票通过剥夺了我的合伙人地位。51岁的我重新回到了一个人的生活,在这个大萧条后最不景气的信贷市场上为获取商业贷款疲于奔命。
刚刚失业的那段时间,我的收入是零。后来慢慢好了一点,我的新生意开始有了点起色,不过也只有以前收入的一半不到。我算是幸运的了,还能找到工作。不过为了支付离婚后的赡养费、子女抚养费和学费,我不得不卖掉了房子和车,以及一切能卖的东西。我搬进了公寓房里,在公共洗衣房里洗衣服。旁边和我一起洗衣服的是反戴帽子、脚穿木屐的大学生,房间里飘荡着一股大麻的味道。这真是个叫人欲哭无泪的笑话。尽管倒也算不上是贫困或苦难,但对我来说实在是沧海变桑田了。
虽然境况越来越糟糕,但我还是留下了“吉普赛月光”号这艘急需大修和重装帆布的老船。除了因为经济不景气,没人愿意买它之外,它对于我来说代表着梦想,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它就是一块魔毯,在质量检验员的眼里,它的船体依然“像纽约的人行道一样坚硬”,完全可以再次扬帆踏上奇幻之旅。当我还是个切萨皮克海湾的男孩时,它就陪伴着我出海探险了。它的存在时刻提醒着我,人生虽不如意,但我仍有理由去追寻梦想,仍有途径去实现梦想。
默默忍受的火焰,会提炼我们,使我们浴火重生。终于,我的生命开出了新的花朵。当您在阅读这本回忆录时,您将有机会一闻其芬芳,感受其祝福。倘若没有生命中的熊熊火焰,这一切都将不可能发生。
曾经有句名言,说意大利经历了30年的战争和苦痛才孕育出了文艺复兴,而瑞士却只有布谷鸟钟来展示其几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宁。虽然我经历过挣扎,虽然我也明白现在取得的成就更像是布谷鸟钟,跟达芬奇相去甚远,但可能比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所能造出的钟要好一些。至少它可以报时,而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如您所见,2009年8月,我的生命按下了暂停键。那是一段平潮期,汹涌巨浪过后宁静的一刻,而新的波浪即将汹涌而来。到底这是风暴前的宁静,还是黎明前的黑暗,只有去试了才知道,因为潮水是不等人的。然而,无论是福是祸,无论路向何方,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都不想错过它。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