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之智慧》:
父亲之爱父亲过世十年了。一直想写点什么,却无法直抒胸臆。很多话,只有对自己说,变成了喃喃自语,天上的父亲不知是否可以听到。从来没有觉得父亲已离开这个繁杂的尘世,还觉得他依然在故乡的家中,一如往昔,忙着他的事,彼此隔海隔空。只是,没有办法再听到他的声音,再无法过年时给他叩头,再无法见面时给他洗脚,不能在父亲节时问候声:爸爸过节好。如今阴阳两界,天地问的距离是如此遥远,无法对话,无法沟通,只有意会,默默将思念埋藏在心中,每到清明和父亲节时泛滥一会儿。
父亲十周年忌日时,小弟带着他新婚的上海媳妇,回到老家,去给父亲上坟,说第一次将过门的老婆给老爸看看。一手不黄土的墓冢,掩盖在一片青山绿树中,离市区很远,幽静安宁。父亲终于看到,最小的弟弟也成家立业有了太太,有人照顾他的小儿子,可以在天国微笑了。弟弟没有告诉他老婆是否哭了,吾想象着小弟一定泪流满面,双眼婆娑。小弟身为男儿,心竞如泥柔软,对父亲,对母亲,都孝道尽至。
每次给父亲上坟扫墓,总是面伏于地,长泣不起。
在家父过世三年时,我去给父亲坟墓上祭拜过,过程辛苦凄戚,然而却了一桩心愿。原本没有回家的打算,和哥哥通话的时候,忽然意识到自己不孝,父亲过世时竞没有见最后一面,隔着千山万水。虽然父亲过世时正值“非典”时期,母亲说不要我回家,从美国到中国的旅途太劳累是其一,还面临被隔离的可能,想起来却是心痛的遗憾。
在费城上飞机的时候,一个朋友请我带他母亲一同回中国。老人家不懂英文,她非常担心自己一个人在芝加哥转机时走丢了。她说跟着我就不怕了,看着她一丝微笑爬上嘴角。这便是中国老一辈人了。不知父亲会不会亦如此。他们也许从没有想到自己会远渡重洋,到美国来看望他们的儿女。她问我回去多久,我说只是一个星期而已。她说那不是太短吗?我说只是一点家事,办完就回来了。老人看着我,有些困惑。
我没有告诉她,那番回国,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在父亲辞世三周年之际,在他坟上献上一缕轻烟。父亲是无法到美国了,其时他最骄傲的便是他的女儿在美国了。只是最有出息的,却最不孝,不能在他垂危之际守在床榻。父亲的美国行只有在梦中了。从芝加哥到上海的班机不过是十三个小时,我却觉得恍如隔世,回家的路是如此的漫长,却觉得飞在天上离父亲距离最近。和父亲已隔世,想父亲会希望再看到我,父亲只有一次人吾梦乡,醒来的时候竟然全然忘记梦中种种,只有父亲依稀的音容了。
曾赋诗一首,名日《先父三周年忌日祭诗》,此诗作于2006年7月1日回国前夜,仅为祭奠先父在天之灵,呈录于此:“先父已乘仙鹤去,此地唯余满思念。遗憾病榻未尽孝,三年转瞬泪盈余。父知吾心无言语,万里相隔两重天。梦里相见多挂念,无奈醒时湿枕涟。曾经创业坊市间,兢兢业业英名传。辛劳终生无停息,家族兴旺盛景现。重回故土祭清烟,往昔幕幕萦思绪。遥忆女儿高考时,先父彻夜无眠夜。女儿异国终安居,息叹先父无法见。唯有静穆独清宇,寿终正寝慰善灵。’’在父亲坟头焚烧了那首小诗,烟灰飘在空气中,竟然悲戚得无法呼吸。
其实这一生,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日子,从十八岁后便屈指可数。父亲在心中,似乎总是小时候那年轻英俊的样子。老爸老是夸他自己长得如青年时代的毛主席,美男子一枚。他就是我们家的总统,绝对的独裁者。也许,在每个女儿心中,爸爸总是天下最有魅力的男人。岁月如梭,我们都一天天长大,父母却一天天老去,终将离我们而去。留下的,便是回忆,如长长的常春藤,无声无息攀沿着。
从小在一个兄弟姐妹多的家庭长大,居中,哥姐弟妹全有,是天下各种亲戚关系最全的人,做伴娘必能为新人带来幸运。小时候,总以为自己是家中最受冷落的那个小孩,暗自自卑,敏感多愁,又悄悄努力,以上进出色赢得父母更多的目光。长大后和父亲提起,他总是笑笑,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哪有不心爱的,只是没有时间管你们而已,你们是我的五个手指头,咬咬哪个都是疼的。”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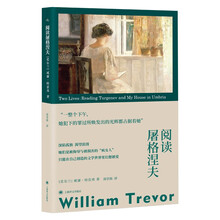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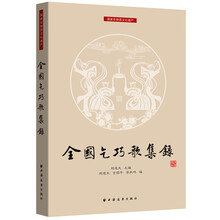

作者与林达、严歌苓一样,都是华裔美籍女作家,共同点是有跨太平洋东西的生活经历,中西文化碰撞产生的灵感,文笔同样有女性的精微雅致;不同的是,林达偏重理性地介绍美国,严歌苓侧重文艺虚构,胡曼荻则知性感性交融,文如泉涌不拘时空。
——鄢烈山
从中国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到美国,胡曼荻勇敢走过大半个地球,使她视野大为开阔。曾经的记者生涯,令她对新环境、新世相、新人新事倍加敏感,禁不住写下“所经所历所观所看所闻所思”。丰富的经见,浅或深,风或雪,眼前或天边,遗落或铭记,有喜有愁,有悲有乐,五味俱浓。无论散文或小说,都是她想与读者分享的心语魂音。
——孟伟哉
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与日常生活。在八卦、段子、小品、肥皂剧时刻弱化着人们智力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有思考、有见识、有真情而又细腻婉约的文字,来滋润我们的生活与灵魂。
这是我读过的有关异域生活最有特色的文学作品。
——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