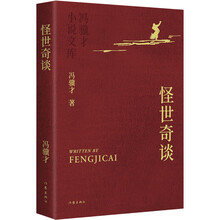清光绪元年,冀中平原有一镇,名唤北镇。
北镇有民千户。镇内有一财主,姓秦名和泰,字平年,百姓常称其:老泰。
北镇财主老泰,房产聚于镇东南角,占地10亩。高门大宅,四合院相衔,错落有致。明式门楼,兰砖灰瓦。青石铺路,阶筑十层。木式框架,神工鬼凿。雕龙画凤,耀人眼目。红灯高悬,流苏飘逸。此院四季常鲜,又加魁伟耸立,犹如鹤立鸡群。
家有田亩千顷,延之外县数十里。在二州三县具有当铺、粮行、布行、旅店、酒楼,且店堂商行各建私宅数座。真个是粮积钱聚,家资巨万,产业广延,有鸦飞不过的田宅,贼扛不动的金银,被誉为州县财主之首。
冀南平原亦有一镇,名唤南镇。镇亦有千户人家,有一药商,姓董,名善堂,字百和,人送雅号老善。
药商老善,是三代行医世家,传承至此,药业兴旺。通一府一州三县,药堂之最还属董家。董家宅院为镇中首户,四合庭院占地10亩。院套院,楼接楼,错落雅致。楠木竖柱横梁,雕栏画栋,色彩艳丽,醒目辉煌。居住主次有别,男佣女婢相隔,经纬分明,不相往来。
董家在州县设药堂六处,管家、医师、司药百人之多。进药之径北有安国,南有亳州,东出关东,西至山西之远。既行医兼卖药,经营之得,可达日进斗金。凡顾一应人员,在职重金聘用,老辞亦有养老之资俸给。常供养老者二三十人,每人每月供奉三五两银不等。为此众人无不施勤尽职,不敢有惰态偷懒之行。
且说北镇秦老泰,自幼念过几年私塾,承祖上教训,尊崇儒学之道,诚信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并以此信条持为发家之本。夫人王氏,与他同庚,年50岁。30岁生一独子,取名文生。文生七岁入学,15岁中秀才。因社会动乱,上下污淖,听从父命,协父料理家业。文生倍受父亲影响之深,父前唯命是听。大庭广众前总唯唯诺诺,不会多进一言,举止从不敢越雷池一步。荏弱之质被众冠以孝子之名。
虽荏弱,但非愚,能写会算,资性聪明伶俐。20岁出箨得面阔而饱满,口方而端正。头圆如满月,耳垂鬓生辉。眉间清气常驻,貌似潘安宋玉。
秦老泰有一管家姓刘名温,人送绰号老温。老温自幼与老泰乃是私塾学友,小老泰一岁。因家贫只读书一年就辍学,跟随父亲躬耕田陌,后文化的长进全凭耕余勤学所得。学的能写会算,能言善辩。15岁就入秦家做工,吃苦耐劳,忠厚善良,乐于助人,深得老泰赏识。老泰常与老温兄弟相称。老温虽不失贫苦本色,但仍以奴效忠秦家,即奉行秦荣我荣,秦衰我衰的宗旨,决不亏心欺主。
董老善少年跟父学医,至成立就以仁慈心卖药行医,接人待物,笃信诚实,德高望重。富裕不骄,名美不张。董老善有一儿一女,儿子董雪松,打理六处药业。女儿董寒梅,从七岁起,董老善就延教授在家设馆,教女儿读书识字。从诸子百家、至唐诗宋词,及至元代文章,皆能口诵背写,并能立笔独篇,堪为当地才女。15岁跟父学习医学,黄帝内经,百草纲目,反复研习。对华佗历史医学名家所传的疗法,俱能深思熟虑,流传千年的望、闻、问、切,细探究竟。她常随父亲坐堂,践行父亲所传妇科、儿科的秘方。久而久之,善察多种疾病,更侧重疗理妇科的妙方。
是年寒梅芳龄19岁,那女儿生得如花似玉,站于花前,花儿就像与她说话。戴上玉镯,玉也要沾染她的馨香。面如满月,发如乌云。虽不浓妆酽施,总显动人容颜。并非舞眉弄姿,尽露自然风韵。俊眼亮眸,藕腕笋指,天生得俊俏端严,真是个镇里老少稀罕,君子艳羡。
这南北二富翁,虽遥距百里,但数年来生意交往,场面接触,彼此之间,各自境况无一不知。秦老泰偶见几次老善之女,老善也面识老泰儿子多次,两家欲有谈婚论嫁之意,碍于自尊皆羞涩启齿,常处心照不宣之状。猜透二翁心事当属管家老温,从中牵线搭桥,将亲事撮合而成。
那时代,男婚女嫁,多为父母做主,当是要选门当户对方可。女方亦求男方品貌端正,父母遵女儿之意,总邀未婚之婿至家,使女儿伺机偷觑,以品头论足。当然女喜男惬,婚嫁成熟,天成宇配,无不称心如意。
婚姻一就,两家欢忭无比。老泰谴老温前往相商,择次年阳春三月某日,完成花烛之喜。此后,两家掐指数日,踮脚企盼。
婚娶那日,天朗气清,云淡风轻,真良辰吉日。迎亲队伍,四抬大轿,大马数骑,迎前跨骏马者,披红挂彩,乃新女婿秦文生。器乐悦耳,彩旗飘飘。百十里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震天动地。迎亲气派可见斑斓。
出嫁的车辆,一字长蛇阵,四辆轿式大车,尽装绸褥缎被,锦衣锦袍,式样家具珍品。只见箱挨箱,包摞包。寒梅出嫁,爹娘赠一名贴身丫环,名叫春柳,寓轿内偎坐姑娘一旁。她怀抱百宝箱,内装珍珠玛瑙,金钏银钗,金麒麟,玉仙童,可谓珠光闪烁,宝色生辉,价值百田四宅。
洞房之内,玉炉喷沉麝之香,幔帏轻垂流苏之带,软垫厚铺,锦被横压,绸帷四裹,香气沁人肺腑。
搀新人进入洞房,揭开盖头,二人对坐相觑,女臊男羞,暗送秋波。只听见外面窗纸捅破了,房门推开了,男挤女拥,看新娘者络绎不绝。才女之美貌,屋亦耀眼,院亦生辉。
秦家娶了个好媳妇,震动了全镇。又是这位好媳妇,不久便引出一段离奇的事儿,轰动四邻八乡。
三月娶妻,三月怀胎,按理并非怪事,亦无可非议。怪异怀胎,六月降生,就成了奇闻。有道是七月、八月已够早熟之儿,六月生孩岂不咄咄怪事儿,就连寒梅懂医之人,生下六月孩儿非但没夭折,却白胖沉重,她也莫名其妙了。
那还是秦老泰得知儿媳怀孕初期,真喜形于色,不易言表,盼孙心切,不亚于文生盼儿。在外催租查账,路上与管家老温聊天,过去只是租佃账目之事。而今,三言两语,就被儿媳妊娠的主题所牵。
老泰问:“你能写会算,给算算文生媳妇生男生女?”他诨言相激,“能算准,我就服了你。”
老温睇一眼于老泰,明知答主何话才可取悦他,可又怎么能瞎蒙胡诌,只好委婉以答。
老温说:“我即便能算个天下雨,地刮风,可真算不出女人生孩儿的事,你呀,还是请算命先生吧。”
老温在家问夫人:“现在是几月啦?”
夫人说:“几月了,你算算·······——有你这么心急的吗,还差仨月哩。”
晚上,他躺在床上,含糊不清重复着夫人的话“还差仨月哩”在梦乡里,还呓语连篇“我的宝贝,我的乖孙子······”
当老泰在梦境,夫人似睡非睡之时,忽然窗棂被击的咚咚响,只听窗外文生急促在喊爹呼娘,说寒梅要生了。
“什么,生生,快叫接生婆呀,”老泰如梦初醒,脑海里一片空白。只有早就运筹的这句话说得更麻利。
夫人焦急万分地说:“叫李嫂赶紧准备大小铺垫,让王婶烧开水,煮剪刀。快去快去,”
老俩口紧穿急束走出房间,直奔儿媳房间而去。
整个院子,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如火烧眉毛。挨出挨入,高呼小叫,忙不停蹄。老泰夫妇见众人忙的不可开交,只觉得眼睛也看花了,喉咙也喊哑了,可谁也不听他的指挥,往日那尊严此时尽威风扫地,不起半点作用。
只听寒梅屋里传出哇一声婴儿的哭啼,屋外众人皆踮脚翘首,瞪目竖耳,只听接生婆连喊带嚷道:“生啦,生啦,是一个白胖的小子。”接生婆手舞足蹈从屋里跃出:“真好福相呀!”
那声音从屋里频传出的一刻,早有管事的将一把把糖果撒向众人,你争我抢,热闹非常。
当人们喧闹之际,老泰却在一角踱来踱去,不吭一声,至人散之后,院里鸦雀无声之时,他想象起他数的日子:“还差三个月,还差三个月呀,这不才六个月么,怎么生了个六月孩儿呢?”
六月坠地孩儿,像卧在他面前的一只虎,惊吓出失色之状。已经忘记迈步回房,只显得失魂落魄,像落水爬岸的老鼠不知所措。
他回到自己房间,便觉露声无妨,疑问就如六月深夜的高粱杆,响出清脆的拔节声。他自言自语道:“生男也罢,生女也罢,怎么偏偏给生个六月孩儿,有六月生孩儿吗?”他象想起什么,仍自语道:“常言说‘七成八不成’,口有传,书有载,倒也不奇。只是六月生孩儿百年未闻,百里无传,这叫从何说起呀!”
这时的老泰就像脑袋灌进雾水,而这头雾水却叫他随波逐流漂向一条邪径,只有这条邪径上才能找寻解疑儿媳、孙子的答案。他不愿要这样的答案,而似乎这个答案才是正确的。他再次发出愤懑的自语:“只怕这小孩不姓秦!”
此时,管家老温蹑手蹑脚推门踏进,对垂头丧气的老泰一拱手,说:“向大哥贺喜。”
怒气未消的老泰,头不抬,眼不睁,说:“贺什么喜?是你喜,我喜,还是旁人喜呀?”
老温满脸疑惑说:“怎么,不愿先结果,乐意先开花呀,我看你是乐极生悲了吧。”
“你诚心气我,看我笑话不是,”老泰极其严肃地说,“六月孩儿,你不觉得怪吗。”
聪明的老温并非没想到六月孩儿的蹊跷,但蹊跷归蹊跷,若论寒梅的人品,总不是别人的种吧。不管六月孩儿,五月孩儿,总是秦家的骨血,会错到别家不成?联想秦老泰的儒理多疑之心,不免心中抖颤。这问题还真蕴含着危险的信息。他也只是觉得奇异而已,老泰可是有恐惧之心。一个坦然,一个惊慌,必然会产生两种结果。老温心里暗暗祷告着:千万别弄得祸起萧蔷呀。自古以来,多少富豪之家,因祸起萧墙搞得家破人亡啊!
老温了解老泰的脾气,再说下去不知多么尴尬,只好默不作声迈出屋去。
若说这孩子生在贫家,六月生也罢,五月降也罢,奇便奇,异便异,任去笑谈,亦不怕闲言碎语。生在豪门就非同一般,生在豪门难免舆论纷纷,一片哗然。
这事一个月以后,街谈巷议仍在咭咭呱呱之中。
一农夫说:“天下女人哪有六月生孩儿的,我看不是娶的姑娘,倒是引来一个带肚妇。”
另一老妇说:“带肚妇当作黄花姑娘娶,嫁者愿嫁,娶者愿娶,嫁者清,娶者迷,秦老泰想早抱孙子,老天爷偏给他个野种,你说这不是天意是什么?”
好事的小伙子说:“照这样说,六月孩儿原是别人的种呀,哎呦呦?六月孩儿这顶绿帽子,一下子就给老泰和儿子扣牢了。”
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传至之远,传至之歪。数日里,整个北镇搞得是纷纷扬扬。秦家大院更是愁云密布,恐惧四围。寒梅想不明,文生弄不懂,老泰愁不尽。秦老泰脚没出过二门,大门口像被贴上封条,一应外事均由老温一人奔忙。他和儿子在一处只管“研究”六月孩儿的话题。那种抱怨、嗔怒、埋怨的气氛常充斥客厅。
老泰问夫人:“你听说过六月孩儿的事没?”
王夫人只是摇头,不知可否。
他诘问管家老温,老温说:“我向你保证,董家的姑娘是贞洁的。”他解释说,“谁不知寒梅做姑娘时,足不出户,身不外移,深藏闺阁。——她家凡男不可登女楼,凡女不可外引,姑娘面如花,手如玉,哪个不知,谁人不晓。”
老泰说:“你给我解释一下六月孩儿的缘故,”他很自信,“我给你讲,天下的事儿璧有瑕疵,水无真清,只恐这六月孩儿与我秦家无关,非是我家血脉。我恳你近日细细去访问,望能给我个确切的答复。”
老温站在一旁哭笑不得。他知道老泰要什么答案,但那个答案是错的。
是时,窗外有耳,寒梅的贴身丫鬟春柳,在此经过听得一清二楚,她向屋内狠狠的摩拳擦掌,真想去搧秦老泰俩耳光,她恨老泰对寒梅的侮辱,捶胸顿足气愤不已。她急切切走进寒梅的房间。只见寒梅坐在床沿,微低头向着娇儿,泪如断线珍珠,话儿凄凄,自言道:“我的小继儿,”这是老泰早已起的名字,“你生的不是时日呀,你怎么在娘的腹中长得那么快,又是那么的壮。六个月生下你,娘也弄不懂呀,只是天知,地知,神知呀。可天不能言,地不能语,神不能见。娘虽知你是秦门之后,娘的话由谁能听,你的生命有谁来护。我可怜的孩子,苦命的孩子,娘生你只恐难逃一劫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