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此轻柔:爱上莎士比亚书店的理由》:
下面将讲述的是,我如何在巴黎一家老书店找到安身之处的故事,以及在我旅居的那段日子里发生的诸多不同寻常的往事。
在写这部回忆录时,过往的一切如流水般真切涌现。那些带我来到法国和在书店所发生的一切事实,远非本书篇幅所能容纳。因此,这些往事经过了提炼、浓缩、再提炼。在按照年代顺序的叙述中,有些做了微小的变动,省略或修改了某些事,并应某些人要求隐去了其姓名。
除此之外,本书在叙述上将尽可能地做到真实。
我来到这家书店时,时值冬季的一个暗淡周日。
在那段困顿的日子里,我养成了散步的习惯。从无明确终点,只是漫无目的地到处闲逛,借以消磨时光,转移我对眼下困境的关注。令人惊讶的是,当你置身于那些熙熙攘攘的集市、宽阔的大街、修剪整齐的园林和大理石纪念碑之间时,忘我成了一件极其容易的事。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下午时分天空早早地飘起了细细的雨丝。起初,雨几乎不能打湿一件羊毛衫,更不必说打断我认真的散步了。但后来,几近黄昏,天空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当时我正在巴黎圣母院附近,必须要找个地方躲雨,刚好瞥见河对岸有块黄绿色的店铺招牌。
那时我在巴黎已经待了一个月,隐约听说过这家传奇书店的许多传闻。我对它很是好奇,当然,也时时打算前去拜访。但当时大风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裤腿上,雨伞如雨后春笋般在我身边涌现,我走过桥后,那些传闻早就被我抛在了脑后。我唯一的念头就是躲过暴风雨,把下雨的时间打发过去。
书店门口,一群游客仍勇敢地为最后一轮照片摆着姿势。他们用厚厚的旅行指南遮挡相机,一边牙齿打战一边努力摆出笑脸。一个女人从雨衣的兜帽下探出头来,她丈夫还在旋转着复杂的镜头。“赶紧,”她催促说,“快点。”透过起雾的书店玻璃窗,能看到一抹暖暖的灯光和些许移动的身影。左边是一扇窄木门,门上的绿漆已经斑驳脱落。嘎吱一声,我有点兴奋地推开了门。
开裂的天花板上垂下来一盏枝形吊灯,角落里一个胖男人正在抖他那宽大的绿松石色穆穆袍上的雨水。一群顾客围在书桌前,用各种语言高声地对店员讲话。当然还有书,无处不在的书。它们或压弯了木头书架,或散落在硬纸盒外,或摇摇欲坠地堆在桌子和椅子上。一只毛色光亮的黑猫趴在窗台上,瞅着这股乱劲。我敢说它抬起头看了我一下,还朝我眨了一下眼。
那些游客推门而进时带进一阵急风。我向前走过堆满东西的书桌,踏上漆着“为人文而生”几个字的两级石头台阶,走进了宽敞的中央大厅。桌子上、书架上堆着快要溢出来的书,有两条路通往书店更深处,头顶上有一扇阴暗的天窗。不同寻常的是,这扇天窗的下面正对着一个镶着铁边的许愿井。一个男人这会儿正屈膝跪在那儿,从井里往外掏大面额的硬币。
等我凑上去,他看了我一眼,迅速用他弯曲的胳膊遮住了那些硬币。
远远地离开这家伙,我穿过一条窄窄的走道,发现周围到处是俄语图书。接下来我转错了方向,走到了一条尽头是个水槽的死路,水槽周围是成堆的黄色封面的《自然》杂志。在一期报道马达加斯加丛林的杂志上,有一把沾有肥皂泡的剃刀。这点泡沫给杂志上一头卧着的豹子增添了几许不自然的气息。
我顺着原路退回,走到一排放着德语小说的书架前,突然,我被轻轻绊了一下,看到一个岔口,还有一堆印刷精美的、堆成金字塔形的艺术书籍。另一头是一座镶着彩色玻璃的壁龛,里面有一只灯泡在闪闪发光。一个女人蹲在那儿用意大利语嘟囔着,试图借着这点闪烁的灯光看清书上的书名。
我又穿过另外一条路,回到了那个有许愿井的房间。掏硬币的男人不见了,但游客已经汹涌而至,占领了这个地方。闪烁的相机亮得几乎让我失明,我从他们潮湿的肩膀旁挤出去,来到了我一开始到过!的那个诛宫。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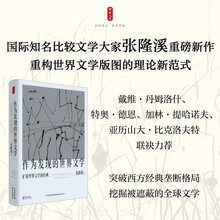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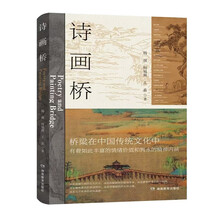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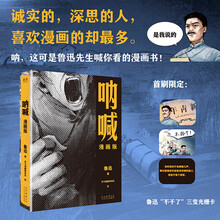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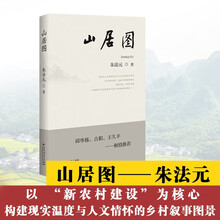




——劳伦斯·费林盖蒂,“城市之光”书店创办人
《时光如此轻柔》不仅仅是发生在千禧年来临之际的轶事,不仅仅是波西米亚式的巴黎文学。它更是有关传奇的莎士比亚书店的第一手资料。
——《新闻周刊》
这是一部绘声绘色的惠特曼传记,是一部关于巴黎左岸激进主义文学的回忆录,结构紧凑且富有洞察力。一部了不起的佳作,内容风趣,于平静叙述中打动人心。
——《旧金山纪事报》
本书所呈现的那种氛围,虽与《迷惘的一代》不同,却自有魅力。
——《华尔街日报》
莫塞尔是一个好作家,目光敏锐、视角独特。
——《芝加哥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