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
根本不可能的事怎么会发生呢?我想不通。世界开始黑白混淆、上下颠倒。或许,那东西不过是我的幻觉。
不可能出现的东西却被我看到了,我想是这样的。我这是疯了吗?没有啊!让我平静一下,先理理头绪再说话。我要拿起那支钝刀似的秃头铅笔,写出来可能会好一点。
今天的早饭是煎蛋和烤面包,大家都一样。我没胃口,勉强吞下一只煎蛋和两片没抹黄油的面包。早饭前,我刮了胡子,穿上衣服。接下来该写什么?此时此刻,我正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抬眼就能望见窗外的街景——孩子们在楼前踢球,红色的皮球滚来滚去,滚过高高低低的房子、邮筒、垃圾桶,草丛里有个玻璃瓶,晾衣绳上垂着几件湿嗒嗒的衣服。这一切不都挺正常吗?我应该把椅子转个方向,看看房间里的情况。好的,现在就转椅子——眼前是书架,撑满了书,不少书是被我斜插着硬塞进去的。旁边是我的床,被子乱摊在上面,那被子还是我前妻留下的。屋里还有一盏铜制落地灯,亚麻灯罩歪向一边。茶几上放着一盒薄脆饼干,贴切点说是一盒饼干渣。书桌上摆着一杯水,还有我手中的铅笔和一沓纸。
我到现在还能背出勾股定理: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而且只适用于直角三角形。一个42岁的疯子有可能背出勾股定理吗?
又开始头晕了,天旋地转,七荤八素。手抖得写不下去了。做个深呼吸会好一点吧,吸气,呼气……
让我先看看刚才写了些什么。还不错,视力好像没问题。是的,有必要谈到视力,有必要把沾边的事都写个明白。一个人看到了奇怪的东西,首先肯定要怀疑自己的视力,当然,神经出了问题也说不定。我想尽可能把一切都写下来。前几天,我也试着把这件事讲给几个人听,但怎么都说不清楚,就连现在还是词不达意。是爱伦建议我把它写下来的,但她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得而知,也不知道她是否相信我。给她说这事的时候,我俩正在她最喜欢的印度餐厅吃晚饭。她一边听,一边像往常一样和服务员打情骂俏,我知道她想让我吃醋,但她原本就是个轻浮的人,我也习惯了她的半真半假。我的话音刚落,她便拉起我的手,让我把一切写下来。
写到哪儿了?对了,视力。每隔一年,我都会去找验光师检查一下眼睛,每次都能轻而易举地看清视力表末行最小的字母。还记得小时候和同学们一起等校车,我总是第一个望见车子的那个,远方那个小黄点一出现就被我看见了。小伙伴们都说我在吹牛,说我看到的不过是车前扬起的土,可我真的看见了那个小黄点,虽然挺模糊,但真的是它。当然我承认,在实际生活中,如此好的视力却从未派上过大用场。从小到大,我的书本都是标准大小的印刷字体。在银行工作时看到的数字虽多,但字号都不小,不过再小的字体也逃不过我锐利的双眼,我有这个自信。要说听力,我也挺正常,那个怪东西闪现的时候我并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响,唯一能听见马丁办公室那个时钟的滴答声。
再说,我绝对不是一个……怎么说呢……易受控制的人。这个词还是比较贴切的。我活了大半辈子,从来都不容易受别人操控。许多年前,有个催眠师在一次聚会上想把我催眠,结果没得手。当时,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我很难“受制于人”,好像我永远都无法坠人爱河一样。如果真能穿越时空回到那次聚会——当时我才二十多岁吧——我会对那个老兄和所有在场的人宣布,我很高兴自己能不受外力控制。我喜欢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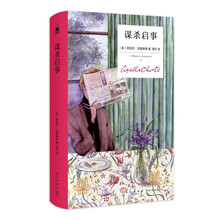

——《书单》
★在《幽灵》中,莱特曼精妙洞察到了普通人面对巨变时所产生的复杂情感。
——《纽约客》
★关于上帝是否存在,死后是否仍然有生,时间又是如何流逝,小说着力于这些令人耳熟能详的问题,或许描摹得仍然不够幽微,但作者对主人公大卫那层层逼近的心理焦灼的描写足以让故事引人入胜。
——《出版商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