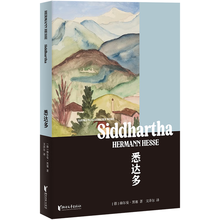1
炎热异常的酷夏。间谍罗森柏夫妇就在这个夏天因泄露核弹资料给苏联遭到处决。而我,在这个夏天来到纽约,却不知来这里做什么。我对处决这种事懵里懵懂,但想到全身通电而死,就整个人不舒服,偏偏报纸上全是这件事。每个街角,每个弥漫着花生和霉臭味的地铁出入口,都有电椅处死的标题睁大眼盯着我。照理说这事与我无关,但我就是禁不住好奇,纳闷电流窜遍神经,被活活烧死是什么感觉。
世上可怖,莫此为甚吧。
纽约本身就够糟,而这会儿不知打哪儿渗入夜里的伪乡村清润气息,不到早上九点,就如同美梦余韵,蒸发得无影无踪。巍峨高楼构筑出都市版的花岗岩峡谷,谷底氤氲灰蒙,犹如海市蜃楼。暑气逼人的街道在阳光底下颤颤晃晃,车辆顶部热得嘶嘶作响,灼灼发亮。燥干如烬的尘土吹入我的眼睛,灌入我的喉咙。
不论是从收音机,还是在办公室,我老是听到罗森柏夫妇的事。他们盘踞在我的脑袋里,甩都甩不掉。那感觉就像第一次见到尸体后的好几个礼拜,尸首的头──或者该说留在尸体上的那颗残余物──仍不停浮现我的眼前。早餐时从我的蛋和培根后面冒上来,也从巴帝·魏勒的头颅后方浮出来。而我之所以会见到那具尸首,正是拜巴帝·魏勒之赐。那天之后没多久,我就觉得自己随身携着一颗系在绳子上的头颅。那颗没有鼻子的死人头,就像一颗散发出酸醋味的黑色气球。
那个夏天,我察觉自己一定不对劲,否则怎么会满脑子都是罗森柏夫妇的事,要不就是成天想着我怎么会那么蠢,买下那些昂贵却难穿的衣服,最后只能让它们像一条条死鱼软趴趴地吊在衣橱。还有我在大学期间累积起来的小小成就原本让我很得意,怎么一来到麦迪逊大道上成排的光亮大理石墙和橱窗玻璃外,开心的情绪就消散于无形。
照理说,我会在纽约享受大好人生。
照理说,我会是全美成千上万女大学生的羡慕对象。她们渴望像我一样穿上那双七号的漆皮鞋,骄傲地游走于城市四方。这双鞋子是我有一天趁午休跑到高档百货公司布鲁明黛(Bloomingdale’s)买的,当时还买了一条黑色的漆皮皮带和黑色的漆皮手提包来搭配。尤其是我和另外十一个女孩短暂见习的时尚杂志还刊登了我的照片,我想谁都会以为我肯定乐不可支。照片中的我穿着仿银片质料的马甲型上衣,下半身是一件宛如硕大云朵的白纱大蓬裙,手里握着一杯马丁尼,在星空点点的露天屋顶上啜饮,身旁还有数位不知名的猛男相伴。这几位拥有健美身材的年轻男子全是杂志社专为这次拍摄雇用或借调来的。
大家会说,瞧瞧美国,新鲜事无奇不有呢。一个在穷乡僻壤住了十九年,穷到连本杂志都买不起的乡下姑娘,竟然能拿奖学金念大学,还一会儿得这个奖,一会儿得那个奖,最后甚至将纽约当私家车般驾驭悠游。
然而,其实我什么都驾驭不了,甚至连自己都掌握不住。我像一辆无感觉的路面电车,颠颠簸簸地从旅馆移动到办公室,从办公室移动到派对,再从派对到旅馆,再到办公室。或许,我该像多数女孩雀跃开心,但我就是没这种感觉,有的,只是一种极度的静和极度的空,像暴风眼,在周遭的喧扰哄闹中,呆滞地被动前进。
我们共有十二人住在这旅馆。
这十二人当中,有人以散文,有人以小说,有人以时尚文案赢得时尚杂志社所举办的比赛,奖品就是在纽约市见习一个月。开销全由杂志社支付,除此之外还有各式优惠福利,比如芭蕾舞和时尚秀的门票,顶极沙龙的头发造型,针对个人肤质的化妆咨询,而且还有机会跟我们有意效法的各行杰出人士见面。
我手边仍有他们送的一整套化妆品。这套化妆品适合棕眼褐发的女孩,里头有一支椭圆形兼附小刷子的褐色睫毛膏﹔一小盒圆盘状,只容指尖放入的蓝色眼影﹔三条口红,颜色从艳红到粉红。这些全装在一个镀金的小盒里,盒盖的一侧还黏着化妆镜。另外,还有一个塑胶制的白色墨镜盒,盒子上镶饰着彩色贝壳、金属圆片和绿色的塑胶海星。
我明白我们之所以有源源不绝的礼物,是因为厂商认为这是免费打广告的好机会,但即便看穿这一点,我也没办法对这些礼物冷嘲热讽。说实在的,这些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可是收得心花怒放,虽然我把礼物收起来过好一阵子,但一等整个人恢复正常,又将它们一一拿出来摆在屋内各处。现在,我不时会涂涂那几支唇膏,上个礼拜,还把墨镜盒上的塑胶海星割下来送给小宝宝玩。
就这样,我们十二个人住在同一间旅馆的单人房,同层同翼,一间紧邻一间。这种安排让我想起大学宿舍。在我看来,这间旅馆上不了台面。我认为,容许男女房客交错住同层的旅馆才像样。
而这间“亚马逊仕女宾馆”只招待女宾。住在这里的多半是年纪跟我相仿的富家女。她们的父母要宝贝女儿住在不会被男人勾引欺骗的地方。这些女孩有的是学生──念的都是专门培养高级秘书的贵族女校,如凯萨琳·吉布思专校(Katharine Gibbs College)之类,上课得戴正式的帽子,戴手套,穿长袜──要不,就是已从这类学校毕业,目前担任各级主管的秘书。她们留在纽约,无非为了寻觅金龟婿,等着嫁给事业有成的男人。
这些女孩似乎都觉得日子乏味无趣。我常看见她们在屋顶晒日光浴,用心维护去百慕大群岛度假所晒出的古铜肤色,一边涂指甲油一边打呵欠,表情看起来无聊透顶。我跟其中一人聊过,她说,她厌倦了游艇,厌倦了搭飞机来来去去,厌倦了圣诞节到瑞士滑雪,厌倦了巴西的热情男人。
我实在受够了她们。她们让我嫉妒到说不出话来。从出生到现在这十九年来,我不曾踏出新英格兰地区,除了这次来纽约。这次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大好机会,但我只是呆坐着,任凭机会像流水,从我指间哗啦流失。
我想,我的烦恼有部分来自朵琳。
我以前不曾认识像朵琳这样的女孩。她在南方一所贵族女校念书,一头耀眼夺目、闪闪发亮的蓬松白发像一团棉花糖,圈住她整张脸。那双蓝眸如澄澈的玛瑙弹珠,又硬又亮,刀枪不入。而那张嘴,永远都挂着一抹讪笑。我说的不是那种恶毒的讥笑,而是一种被逗乐的神秘讽笑,仿佛周遭尽是蠢人,而她只要愿意,随时都能以他们为促狭对象,说出精彩的笑话。
朵琳第一眼就特别注意我,让我觉得我比其他人聪慧。她这人很有趣,开会时老喜欢挨着我坐,来访的名流说话时,她会压低声音,在我耳边说些讽刺的诙言谐语。
她说,她学校里的女孩很时髦,皮包都有跟衣服同布料的保护套,所以,每换一套衣服,就有相同布料的手提包可以搭配。这种对时尚的讲究,让我印象深刻。它代表的是奇炫细琢的糜烂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方式,如磁铁般深深地吸引我。
唯一会让朵琳提高分贝对我说话,是当她想催促我如期完成工作。
“你怎么满头大汗,在忙什么呀?”朵琳懒洋洋地窝在我的床上,身上是一件蜜桃色的丝缎晨袍,手里拿着锉板磨着被尼古丁熏黄的修长手指,而我则忙着在打字机上敲出先前采访一位畅销小说家的访谈稿。
这又是朵琳与众不同之处──我们穿的是上过浆的夏季棉质睡衣和铺棉家居服,或者,可以充当海滩衣的毛巾布长袍,唯独朵琳,穿的若不是半透明的尼龙蕾丝罩袍,就是会因静电而黏在肌肤上的肤色晨袍。她身上有一股微带汗味的奇特体香,让人联想到香蕨木。摘下香蕨木的扇形叶片,放在指间搓碎,就会闻到一股麝香味。
“你知道的,老洁?西根本不会在乎你这篇稿子是明天交或星期一交。”朵琳点燃一根烟,鼻孔冉冉喷出的烟雾逐渐散开,迷蒙了她的眼。“洁·西长得真是丑。”朵琳冷冷地说,“我敢打赌,她那年纪一大把的老公肯定得把灯全关了,才能亲近她,否则非吐死不可。”
洁·西是我的上司,我很喜欢她,虽然朵琳把她批评得一文不值。她不是时尚杂志圈里那种戴假睫毛、珠光宝气、虚情假意的人,她有脑袋,所以即使粗丑如地痞,也不影响我对她的观感。她会数种语言,还对这一行里的优秀作家了若指掌。
我试着想象洁·西脱下拘谨的套装,拿掉午宴专用帽,跟她那肥老公上床的模样,但实在难以想象。对我来说,想象别人上床就跟登天一样难。
洁·西想教我一些东西──我认识的每个年长女性都想谆谆教导我──可是我忽然觉得她们根本没东西好教我。我把打字机的盖子装好,咔的一声合上。
朵琳咧嘴一笑:“聪明。”
有人敲门。
“谁啊?”我懒得起身。
“是我,贝琪。你要不要去派对?”
“大概会去吧。”我还是没起身开门。
从堪萨斯直接被请来纽约见习的贝琪有一头轻盈弹跳的金发马尾,脸上总是带着甜美端庄的笑容,就像“ΣΧ兄弟会的甜姐儿”那首歌里所描写的女孩。记得有一次,我们两个被某电视制作人叫进办公室。这个胡碴青嫩,穿着细条纹西装的制作人问我们有没有什么点子可以拿来做节目。贝琪一听,开始畅谈起她老家堪萨斯州的公玉米和母玉米,说得口沫横飞、感人肺腑,连制作人都听得眼眶噙泪,不过他说,真可惜,这些题材都用不上。
后来,美容组的编辑说服贝琪,要她剪短发,当模特儿拍摄一组封面。到现在我仍不时看见她在“魁北克的太太们都爱穿B.H. Wragge服饰”的平面广告中露出迷人笑脸。
贝琪老爱邀我和她那伙女孩一起做这做那,仿佛这样是在帮我的忙。但她从不找朵琳。朵琳私底下都叫她“牛仔傻大妞”。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搭计程车?”贝琪在门外问道。
朵琳对着我摇摇头。
“没关系,贝琪,我待会儿和朵琳一起去。”我说。
“好吧。”
我听见贝琪步履轻盈地踱向走廊另一端。
“我们去看看吧,受够了就离开。”朵琳说着把烟蒂按熄在床边阅读灯的底座上,“然后进城去找我们自己的乐子。他们在这里办的派对总是让我想起学校体育馆办的老派舞会。真搞不懂他们干吗老喜欢找耶鲁的来?耶鲁的都很蠢唉!”
巴帝·魏勒就是耶鲁的学生,现在一想,我才发现他的毛病就是蠢。对,他是努力拼出不错的成绩,还曾经在鳕鱼角跟一个叫葛莱娣的二流女侍交往过,但他这个人就是毫无直觉力。而朵琳有。朵琳有办法说出我偷偷藏在骨子里的每个想法。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