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寻找格林先生》:
记住我这件事当周围杂事纷繁,使你难以忍受时,你或许宁可当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觉得你的生命就像一个转盘在持续不断地转着。然后有一天你意识到,你曾经认为是个又平又滑的转盘的生命实际上是一个旋涡。我第一次意识到平平凡凡的日子底下隐藏着暗流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具体日期对你来说并不怎么重要。不过,你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想你会愿意听听这与我有关的隐藏着的暗流。你小时候对家史很感兴趣,但下面我要告诉你的在当时可不能说,原因你马上会明白。现在的人可不对小孩谈什么死亡啊,旋涡啊。而我小时候,父母却不忌讳谈死亡和临死的情形。他们很少提及的是性。现代人则刚好相反。
我母亲去世时,我还是个少年。这一点我已经告诉过你好几次了。我没说的是:当时我知道她要死了,却不允许自己这样想——这样你就有了一个转盘。
那是二月份,我已说过,具体日期对你来说并不重要。不瞒你说,我自己并不愿意把日子弄准确。
正值冬季,芝加哥仿佛穿着灰色的冰盔甲。天低沉沉的,路很不好走。
当时我正在读高中最后一年,对周围一切不感兴趣,并.不引人注目,也不合群。我只有在作为一名跳高运动员时才有机会在公众场合露脸。我没受过什么训练,只是到了最后笨拙地一跳,也可说是一抽搐,越过横杆。不料这竞引起了师生们的注目。
我无心学习,却有书呆子气。对家庭生活守口如瓶。事实上我不想谈起母亲。此外,对自己古里古怪的兴趣,也不知道怎样用语言表达。
不过,就让我说说那个二月初重要的一天吧。
早晨起来,就和其他冬季上学的日子一样平常而不愉快。
气温接近零度,窗玻璃上结满了霜花。人们已经把雪铲成一堆一堆。冰踩在脚下嘎吱嘎吱地响,各街区之间的马路的共同特点是上面覆盖着铁灰色小天空。我的早餐是粥、吐司和茶。和往常一样已经不早,我朝病中的母亲的房间瞧上一眼,弯腰凑过去,说:“是路易,要上学去了。”她像是点了点头,眼睑现出棕黄色,两颊的色泽则淡多了。我把书用背带一扎,就匆匆上学去了。
来到公园边的林荫路,我看见两个矮小的男人拿着枪从一个门口冲了出来,身体转来转去,一边往上瞄准,朝在屋顶上的鸽子开枪。有几只直落下来。他们随即捡起软绵绵的死鸟跑进屋去。他们的皮肤黝黑,白衬衫随风飘动,是些经济大萧条时期城里的打鸟人。就在刻把钟前,警车以十英里的时速缓缓驶过这里。这两人一直等到警车远去才出来活动。
此事与我无关。只是因为它发生了,我才提一提。我绕过遗有鸟血的地方,进入公园。
在小径右边,冬季百合花的枝干后面,冰雪的表层破碎了。在漆黑的夜晚,我和斯蒂芬妮曾在那儿接吻、爱抚、拥抱。我的双手伸入了她浣熊皮袄的下面,羊毛套衫的下面,裙子下面。少男少女的接吻真是无所顾忌。她浣熊皮袄的帽子滑到了脑后。她解开有麝香味的上衣,让我靠得更紧。
走近学校大楼,为了赶在最后铃响前走进教室,我不得不跑了起来。家里警告过我:这段时间里不准给老师惹麻烦,别让校长找去谈话。我虽然不喜欢上课,但仍然遵守校纪校规。
不过,我把所有能搞到的钱都投进了哈默斯马克书店。我读《曼哈顿中转站》、《巨大的房间》、《艺术家的肖像》,参加了“法语圈”和“高年级辩论俱乐部”。俱乐部今天下午的讨论主题是“冯·兴登堡选择希特勒组成新政府”:但我不能去了,我有一份课后的活要干,是父亲执意要我找的。
课后去上班前,我顺便在家里切了一片面包和一块威斯康星楔形奶酪吃,再看看母亲是否醒着。她在最后的日子里服用大量的镇静剂,很少说话。床边高高的方瓶里面装满了清澈的红色戊巴比妥钠。这种液体的颜色总是保持不变,好像不容许有阴影似的。母亲已无力坐起来洗头,头发也就索性剪短了,这使她的脸显得更瘦长。她的唇色暗淡,呼吸急躁短促,梗阻不畅。窗帘拉上了一半,下摆呈扇贝状,底部是白色的流苏。
往窗外看,只见路上的冰呈深灰色,雪堆在树旁。树干是石墨色,上面堆积了煤灰,好像穿着鳄鱼皮盔甲,等待着冬天的逝去。
母亲醒着时也无力说话,有时做做手势而已。屋里除了护士没有别人。父亲是个生意人,姐姐在闹市区工作,我几个哥哥也拼命工作。大哥艾伯特受雇于闹市区的一位律师。另一个哥哥莱恩过去曾为我在西北公司郊区火车上找到过工作。我还一度做过小贩,卖巧克力和晚报,因为很晚才能回家,遭到了母亲的反对,不过那时我已经找到了另一份工作——为城北大道的一家花店送货,搭上电车把花环、花束送到市区各地。花店老板贝伦斯给我一个下午五十美分的工钱,这样加上小费,可以挣到一美元。这使我能找到时间预习三角学课程,而且在见过斯蒂芬妮后,还可以读书到深夜。大家都入睡后,我独自坐在厨房里,四周一片宁静。窗下是风吹成的雪堆,下面,看门人的铁锹碰到水泥地发出刺耳的尖音,碰到炉门时又发出铿锵声。我读同学问传阅的禁书,政治小册子,读《普鲁弗洛克》①和《毛伯利》②,我也研读秘术的书籍,这些书过于晦涩,没人愿意跟我讨论。
我在电车上读书。一读书,就不去留意外面的风景了。其实也没什么风景,都是千篇一律,一个面孔的:铺面、车库、货栈,还有狭窄的砖砌平房。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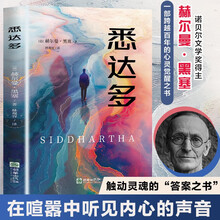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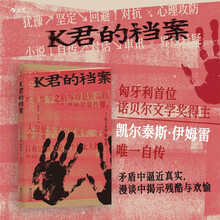




与他洋洋洒洒,狂放不羁的长篇小说相比,索尔·贝娄的中短篇似乎显得更为精炼,更为节制。但用任何确定的词去形容贝娄的作品都是危险的,因为它们是如此鲜活和具有生命力,拒绝任何僵硬的标签。它们是庄重的,但同时又充满诙谐,甚至令人捧腹;它们是尖锐的,但无疑又是温柔的,令人抚慰的;它们是清晰的,但有时又显得暧昧而模糊,仿佛街角的暗影;它们是简洁的,但也不乏看似无用却神秘动人的闲笔。是的,它们就像这个世界本身:不可概括,不可预测,无处可逃。
与许多其他作家的小说相比,索尔·贝娄的短篇小说代表作能带来更强烈的情感冲击……这是一份文学的愉悦,每一道故事佳肴都津津有味。
——《波士顿先驱报》
“人物、地点和事件,在这些小说中骤然闪亮,变得无比清晰,令人大呼意外……福克纳是惊雷,贝娄则是闪电。”
——《纽约时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