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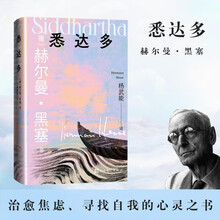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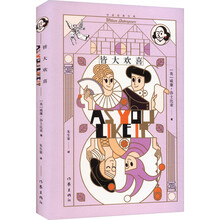


男·女
一台iPod
一场独特恋爱
一部美国流行音乐史
与某人发展出一段情感经验,而对方却不自知,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是那独特的例外,当她正在舞台上演唱,而你正隐身于台下数千名的仰慕人潮中观赏她的演出。那看似不可能,至少台下的你在脑海中,不可能认为她唱歌不是关于你。
《如歌似你》是一部以二十世纪的音乐文化和先进科技为背景的浪漫爱情小说,文中精确捕捉中年男女对生命态度的正反两面,贴切描绘出现代男女的恋爱。主角朱利安?唐纳修(Julian Donahue) 深深依赖他的iPod ,他用iPod播放的每首歌,都触发出一段属于他的生命回忆。丧子之后的他与妻子分居,因为音乐陷入了对爱尔兰女歌手的迷恋之中。
朱利安·唐纳修的父亲迷恋比莉·哈乐黛的一张唱片。
他热爱她的音乐,从她的音乐还是时尚而非潮流(这是乐迷的区分标准)的时候就喜欢。一九五三年四月,他从军队休假,四天后他将前往韩国——天晓得,他把十六磅重的肉体献给了永远僵持的战场,说不定那就是最后所需的一丁点军事牺牲,打破平衡,力挽狂澜,克敌制胜。他搭火车从弗吉尼亚向北到纽约,在银河剧院观看偶像演出。你要是喜欢追踪历史地点的现状,不妨告诉你银河剧院如今是一幢三层楼的香蕉共和国专卖店,最左边更衣室奶黄色的墙上挂着哈乐黛的带框照片。
他花了比门票高得多的价钱,搞到三排正中间的位置,早早进场,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九十分钟,又是摇头又是叹息,半张着嘴笑得停不下来。《我的男人》一曲唱罢,掌声过后,全场近乎于寂静,只剩下窸窣声响,比莉在和乐队商量什么,她背对观众,淡金色的小腿、银色裙褶间的电线和黑色鞋子的系带相映成趣,他想也没想、毫不犹豫地喊道:“《水边》!”渴望炽烈得吓了他自己一跳——“《我走过水边》!”
比莉扭头张望。“好像有人说话?”她侧过身,带着喉音淘气地说,剧院里笑声此起彼伏。她转过身,上前两步,抬手挡住聚光灯,眯着眼睛瞅向前面几排座位。“是你吗?”她说的正是他。
“是的,女士。”
“还挺懂礼貌的,”观众起哄喝彩,“英俊的白人大兵,”她若有所思道。在他多年后的复述中,此刻的比莉微微浮空,女神冷静地打量着底下观众席上顶礼膜拜的他,他的双眼与她的双脚齐平,还不如孩子——完全是个崇拜者。“亲爱的,你要点歌?”
“哈乐黛小姐,我可太想听您唱《我走过水边》了。”
“说得好听,”她望着他,轻轻偏过头,对乐队大声说,“好吧,弟兄们,漂亮的南方大兵想听《水边》,就给他唱一首好了。免得他去告咱们的状,你们说呢?”
他后来经常琢磨,高高在台上的她,能不能感受到自己对他来说犹如女皇。“真的,任何事情。”他这么告诉他的第二个儿子(名字随了一位中音萨克斯手,首张专辑出版于这孩子出生前十年,在定下这个名字之前,他老婆已经否定了——不得不补充一句,第二次否定了——迈尔斯、查理、哈利、迪齐、珀西、伍迪、赫比、泰迪、吉米、莱诺尔、迪克斯特、莱斯特、温顿、瓦戴尔、汉普顿、公爵、伯爵、切特、奈特、汉克、萨德、玛尔、亚特、麦克斯、米尔特、比克斯、若昂和伊利诺斯①),“朱利安,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
比莉数完节拍,开始唱副歌之前的词句,伴奏的只有钢琴:“离开市区……”真是难得,这段引子可以略去——绝大多数歌手甚至不知道还有这段,绝大多数乐手从来不演奏这段——士兵希望哈乐黛觉察到他和别人的不同,比起不那么懂行的点歌者,她格外优待了他。她唱到叠句,唱到曲名那句,贝斯和鼓加入演奏,普通乐迷纷纷鼓掌——他们直到此刻才听出这首歌,一个念头跳进脑海:他乐于为她杀人。歌词里,她在水边等待,盼望爱人的船归来。她唱着他渴望的音乐,在对他歌唱,就仿佛她期盼归来的爱人正是即将远赴海外打仗的他,这个念头在他胸中震荡,犹如刚刚击中目标的飞箭:他愿意为她杀死他左边这个警官,愿意为她杀死右边那个年轻女人。他知道这个念头很奇怪。他并不热衷于暴力,但正如他后来说的,这就是他当时感受到的爱意。他被音乐提升到狂喜的巅峰,俯瞰人世,考虑要不要抹杀众生。
悸动过去。唱到第二个八小节,他终于可以静下来细细品尝这份馈赠,欣赏为他献唱的、这位真正的女人。她闭着眼睛歌唱。他望着她闪亮发梢间摇曳的木槿花,几乎能闻到香味。他幻想着在她生命中的某处找到一个他能扮演的角色,在她的黑人伙伴之间他会活得多么自在,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融入称职的经纪人这个角色,赢得尊重,和乐队痛饮美酒,度过辉煌的漫漫长夜,跟莱斯特·杨或吉米·罗尔斯交上朋友,他和她也许会走上空荡荡的街道,他用皮草披肩围住她的脖子。他们互相偎依,走到街上唯一的路灯底下……他悄声说个笑话,比方说某位乐手朋友长得像短腿猎犬,伴着她温柔的笑声,她的双手抱住他的上臂,压紧他的袖管……今夜在舞台上,她唱的是“星光满夜(stally)”,像是她忘了歌词里是“星光满天(starlit)”还是“漫天夜星(starry)”,于是自己生造了一个词。
她唱到过渡乐段,他琢磨自己能不能学个乐器,跟着她浪迹天涯,他担心她持续使用麻醉品的传闻是真的,他还知道这首歌——他的歌——已经唱完了一多半。倒不是说他没听清——他听到了她的每次呼吸,脚踏钹和响弦鼓的每次轻响,贝斯手的左手顺着乐器后颈上下移动,仿佛一只犹豫不定但侵略好斗的蜘蛛,奏出的每一下深邃重击和木质敲击声也听得清清楚楚——但歌曲没有把他送进茫然的出神境界,而是激发了各种各样的疯狂念头。他幻想这首歌在派对或婚礼上奏响,幻想孩童和宽阔的前院,幻想“和你不无相似之处的男孩”——他这么告诉朱利安。他想着在纽约慢慢变老或者在韩国早早死去,想着学习演奏爵士乐或者在战斗中脱颖而出,拯救整个连队。她结束了独唱部分。
中音萨克斯手上前吹奏十六小节乐段。不是陪着比莉录制了许多经典唱片的“总统”莱斯特·杨,也不是替代莱斯特·杨加入老贝西乐队的保罗·昆尼雪(他的外号是“副总统”,因为他能惟妙惟肖地模仿杨的音色),而是昆尼雪的模仿者。这位模仿者的中音萨克斯手被某份爵士乐杂志冠以“白宫发言人”的名号,这让朱利安的父亲很不高兴,因为他觉得连盖茨、柯恩和希姆斯都比这家伙强,坚持认为他顶多只算是“农业部长”。
比莉在过渡乐段重新加入,唱出叠句。一曲唱罢,她睁开眼睛,朝着第三排微笑,使个眼色,向印象中乐迷所在的位置送上一个飞吻,但聚光灯从上方直射,她看不清楚,因此这个吻向左稍微偏离了目标。
右边的女人转向他——灯光照得哈乐黛头晕目眩,而哈乐黛让他头晕目眩——仿佛歌手在他脸上的倒影吓了她一跳,她觉得自己也变得头重脚轻了。她顿时隐约爱上了这个那么爱着歌手的男人。“你啊,”她后来用带着法国口音的英语对他说,“一张脸那么开心,但片刻之后,又变得那么哀伤。”(每次被朱利安发现他单独一个人坐着,以为没有人在看他,因为痛楚或回忆而愁眉苦脸,他就会打趣道:“悲伤的脸,哦,太对了,她们就爱这张悲伤的脸。”)
他和那女人共度当晚,第二天也是,第三天还是。他有心想擅离职守一周,甚至从此失踪,但终究还是按时登上火车,前往战场。抵达战场一个月左右、负伤仅仅几周之后,战争就结束了。他动了几次手术,先是为了保住那条腿,继而要限制感染范围,接着是保留足够支撑义肢的残桩,最后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完全截肢。“他们一片一片地切掉我那条腿,就像切萨拉米香肠。”他喜欢这么说。“我说啊,萨姆,”他会学着优柔寡断的家庭主妇对肉铺老板那样说,“还是来一磅好了,今晚有客人。”
最后一次手术结束,还得继续动手术的阴影尚未消散,某天清晨,他在日本的陆军医院里醒来,见到了一件礼物。护士在病房里装起一台唱机,调到三十三转,把唱片封套靠在唱机背后的墙上:比莉·哈乐黛的特写照片,她举着一只手,用优雅的手势阐述什么歌词,她闭着眼睛,嘴巴张开,仰着脸,一行灰色小写字母标着:黛女士在银河剧院。
当时他惨叫得震耳欲聋(余生中他时不时还会这样),偶尔有一两秒会听不见别人在对他说什么,因为集中精神需要他克制自己受苦的声音。就像这次,他只听见一名护士说:“——从巴黎来的。”法国女人把这张唱片送到韩国,朱利安的父亲一直没有机会通知她他受了伤并被送到了日本,这份礼物(她父母的昂方路居所附近有家唱片店,她在橱窗里见到这张唱片,惊讶地听了一遍,然后用黄纸打成包裹,还垫上了稻草防震)跟着这个在行程中一片一片地丢掉一条腿的士兵周游亚洲,先是前线附近的帐篷,接着是首尔和东京,终于来到这个大雪纷飞的城郊。
他站不起来,也不能动,于是护士开始播放A面:《紫罗兰配皮草》《乐于忧郁》《那双眼睛》和《我的男人》。《我的男人》正是比莉接受他点歌之前唱的那一首,他躺在床上,在十二月里汗流浃背,头发像新生儿似的贴在脑袋上,内衣透湿发黄,两片嘴唇摩擦蠕动,又一场高烧折磨着他。“……不管我的男人是什么样,我都是他的,永远是……哎呀,这可真好。谢谢你。”掌声雷动,尽管病痛入骨,听着掌声逐渐小下去,他还是有冲动想高喊“水边!”掌声渐渐退潮,化作泡沫,继而消失。唱臂飘过深黑色的空间,走向厂牌的标签:两只黑鸟停在电话线上,变成两个音符。嘶嘶声结束,唱臂回到原点,唱片停止转动,他哭得像个孩子。
他拼命召唤护士来给唱片换面,当初躺在柔软的土地上,看着碎裂的骨头张牙舞爪时呼叫救护兵都没这么拼命,喊着喊着他睡着了。晨光中,他再次醒来,吗啡和高烧让他梦到了法国女人,耳边响起《比莉的布鲁斯》,是《我走过水边》之后的那首歌。“早上好,士兵,”新来的护士说,“你不会反对听点音乐吧。再说,开开心心享受一个钟头永远没错。”她说着换了一袋吗啡。《暴雨天》《细柳为我哭泣》和《纽约的秋天》,B面结束。他们截掉了他的过去,不但是他的声音,甚至是比莉唱他点的歌曲。他禁止护士再次播放这张唱片,他扔掉了随唱片寄来的信件——里面温文尔雅地提到了“一场难忘的音乐会”。一个护士把他禁止播放的唱片带回家,很高兴能在鸟不拉屎的日本听点新鲜的音乐,播放的次数太多,终于灌满了护士的耳朵。她时不时地哼唱上面的歌曲。
一两周后,护士值班时在他的病房里用口哨吹起《我走过水边》,他醒着,闷闷不乐地说:“这是我最喜欢的歌。”护士在一个词的半中间从吹口哨换成唱歌,“—边”,她又唱了几句,有点跑调,模仿哈乐黛那难以模仿的颤音,他心里一阵骚动——不是爱,只是某种暖意,不是因为她,而是她释放出的东西。
第二天,护士把唱片带了回来。他醒着,面对窗户,前面的护士按计划帮他侧过身子,以便促进血液循环。护士把唱臂放在B面开始处,他没有看见。唱机嘶嘶作响,随即响起掌声,他听见背后传来自己的叫声:“《水边》《我走过水边》!”接下来剪掉了一小段,然后比莉使劲清清喉咙,钢琴奏响第一个和弦。“从头重新放。”他对着枕头和湿漉漉的胳膊说。“可是宝贝,这才刚开始啊。”护士答道。“求你了。”他说。他又听见了自己的叫声,那声音发自一具完整的躯体,响彻那声音曾经拥有过的每一条肢体。他们把他保留在了唱片上。他的声音很重要,对于再现那段体验——永远无法重复,哪怕只是小规模地重复——必不可少:二十个月之前的银河剧院,一个四月的夜晚,他在那个时代(多年后他对朱利安这么解释,在一九七三年唤起了孩子对一九五三年偏颇的想象)的男男女女之间,深深爱上了比莉·哈乐黛(对于孩子来说,她是歌剧角色或国父华盛顿一般的古老人物,形象模糊),而且身边就站着他未来的妻子,只是自己还不知道,三分十九秒(加上他和歌手的对话)后你将遇见她,随后你将不得不和她分开,随后你的一条腿将被炸烂,一片一片从你身上被切除,连同你对欢乐的信仰一起被带走,直到你再次听见她的声音,彼时你身处医院的病房,隔着脏兮兮的窗户和铁丝网,望着暗褐色的雪景、暗褐色的天空和附近工厂飘来的如云黑烟。
这张唱片他搜集了许多份。朋友在欢庆和哀悼的时候送给他当礼物。妻子又给了他两张。他把多余的送给值得交往的朋友,赠予军队里的伙伴。他经常播放这张唱片,在各个纪念日(四月那场音乐会,六月的婚礼,妻子早逝的那一天)播放。后来这张唱片绝版多年,爵士从流行音乐变成了仅供品鉴家享用的门类,他的这张唱片只剩下了两份。
后来,朱利安已经记不清父亲做了什么让他那么生气,也记不清他想给老先生什么教训了。肯定是为了父亲好——朱利安记得这句野蛮的咒语如何扰动他的青春心灵。他大可藏起那两张唱片,或者卖给还能赎回来的什么商店——但这只是日后的懊悔罢了。但是,关键就是要让父亲亲眼看见——原因他已经想不起来了——让楼上坐在高窗口轮椅里的父亲看见那两张唱片落进火海,看着火焰熔化黑胶,点燃封套,封面上仰着脸的比莉·哈乐黛特写吐出火苗。
……
序幕
冬
春
夏
秋
★阿瑟.菲利普斯,全美当今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
——《华盛顿邮报》
★对仅知道感受生命的人而言,人生是场悲剧;但对知道如何感受和思考生命的人而言,人生会是场喜剧。《如歌似你》这部小说精确捕捉中年男女对生命态度的正反两面。在全美现今小说家中,阿瑟.菲利普斯可称为是智者中的智者。
——《纽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