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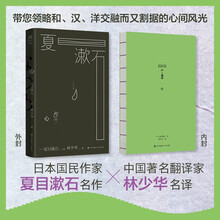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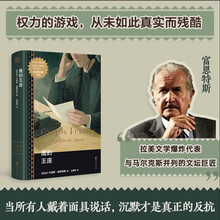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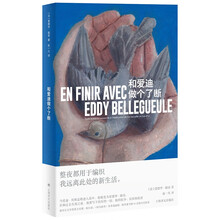
《谢谢你,了不起的泽尔达》在印度,流浪狗简直和垃圾没两样。但是,这只脏兮兮、流落街头的狗儿泽尔达以她的勇气和魅力成功掳获了作者的心,也成为一家四口的重要同伴。当保罗·查特考调职巴黎时,也带着泽尔达一起就任新职。除了作者极少数的朋友之外,自视甚高的巴黎邻居非常瞧不起这只“美国人饲养的、无法无天的杂种狗”。但是在几次的紧急意外中,幸好有忠心耿耿的泽尔达机警解危与相伴,因而拯救了保罗·查特考的新生儿,也赢得主人深厚的信赖。书中还纪录了泽尔达许多有趣的生活小故事,例如:她竟然爱上了法式的卡门贝软奶酪(Camembertche
泽尔达从未转变成一只法国贵宾犬。
即使在她被加冕为“巴黎狗女王”之后,即使在我们那些邻居们为答谢她挽救了他们宝贵的酒品珍藏而用礼物将她层层包围之后,泽尔达也从未狂妄自大或摆起架子来。我们在卢森堡花园里漫步时,或是当我们停下脚步到某家巴黎咖啡馆里喝咖啡或饮酒时,泽尔达会倾尽全力,扮出一副欧洲式的优雅和教养,可内心深处,在她抑制不住的那部分特质中,她依然是那个活泼冲动的印度街头女孩,可爱,任性,野性未泯,她的天性就是如此。
如今,泽尔达不守规矩的情况极少发生,不过在温暖的春日里,泽尔达仍有时会跳出窗外,将一两只松鼠赶到最近的树上,或是周末在勒梅斯尼泰里比时,她还是会趁着没人注意偷偷溜到牧场上,将一些倒霉的绵羊赶到一起围成球状。她的各种发作并无恶意,而且再也没有造成更多伤害;这不过是泽尔达拿出泽尔达的样子来,向我们表明,虽然她在巴黎的生活已变得舒适而惬意,但她偶尔还是必须挣脱束缚,维护她的独立性,她必须对循规蹈矩和资产阶级法国的种种约束不屑一顾,铭记自由自在的感觉。
泽尔达的精神具有感染力。
我们在伊森身上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在巴黎的一个夏天,当时他只有三岁,我们遭受到热浪的侵袭,伊森找到了一种开心的方式来给他自己降温:他将泽尔达喝水用的碗举过头顶,给他自己淋了个澡。他往自己身上和地面上到处泼水——分分秒秒都是享受。起初,伊达觉得很有趣,为他机灵的表现而高兴,但她很快就对为他擦干身子和拖地板而厌烦了。“伊森,”她厉声说道,“别再闹了!”
可是,伊森不一会儿就会跑开去玩,再次热得汗流浃背,然后他又会回到泽尔达的水碗前淋上一个清凉澡。就这么折腾了三四回之后,伊达彻底被激怒了:“伊森,够了!瞧瞧你搞得一团糟!你要是再这么做,我可就要打你的手了!”
呃,“我的食物我做主”先生对于这样的最后通牒完全不以为然。大约一小时以后,伊森再一次热得大汗淋漓,忍不住要测试他母亲的耐性。他拿起泽尔达的水碗,来了一场纵情的悠长淋浴。一听到骚动声,伊达怒不可遏地冲出厨房:“伊森·查特考,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听到这话,伊森老老实实地伸出手来,准备挨打——能犯下如此愉快的罪行,这点小小代价算不了什么。伊达最终还是执行了处罚,但绷着脸做这种事情还是挺困难的。
泽尔达的不羁精神感染了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一天上午我正在美联社分社阅读报纸,突然从挪威奥斯陆电报发来了一则紧急报道:特蕾莎修女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我立即坐下来,写了一篇讲述她的深入报道,其中部分内容是根据我在加尔各答与她相处时的经历而写成。不过,我还想做进一步的报道。于是我游说了我的美联社同事们,他们都爽快地同意了:我要去奥斯陆报道和平奖的颁奖仪式以及依照惯例举办的相关活动。
从某些方面来看,驻外记者和消防队员没什么两样:哪个地方一旦发生地震或空难,你就要带上笔记本电脑和工具设备赶往机场,做好最坏的打算。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我已登上法航飞往奥斯陆的航班,一种亢奋之情油然而生:这将是一次积极向上的报道——总算有这么一回了。自从我到达法国的那一刻起,我的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报道恐怖、恶意和仇恨行为上。借着这种或那种理由的名义,恐怖组织实施了绑架、劫持、炸弹袭击和暗杀等行径,有些事件就发生在巴黎的街头。眼下并不是这座光之城的辉煌年代。我需要歇一歇,我需要感受新鲜、积极的能量,而奥斯陆恰好能为我提供这一希望。
我在举办诺贝尔颁奖仪式的前一晚抵达了奥斯陆,当地一位美联社工作人员陪我在市内愉快地散步。随后,在一家迷人的咖啡馆里,我们坐下来品尝“lutefisk”(碱鱼),这种传统的挪威菜肴通常用鳕鱼干或另一种白色的鱼制成。我对这道菜寄予很大的期望,可是,那鳕鱼有一股介于老鼠药和松节油之间的味道,那些配菜就更糟糕了:糊状的豌豆搭配几块油腻的熏肉、芜菁甘蓝泥、土豆泥,浇上褐色的浓汁,再加上一块疙瘩状的面团混合物,科林夫人是绝对不会管这玩意叫“面包”的。当然啦,我不得不客套地对这道碱鱼菜赞不绝口,这一外交举动只有在饮下大量的阿夸维特酒之后才成为了可能,斯堪的纳维亚人常用这种酒来取暖。好吧,我也能成为不可一世的美食家。
挪威人的烹饪手艺不太精湛,不过他们的高贵和优雅却远远地弥补了这点不足之处:第二天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在每一处细节上都精雕细琢。挪威皇室、挪威议会(由议会的五名成员评选出每年的和平奖获得者)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往届诺贝尔奖得主齐聚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向特蕾莎修女和她为穷苦中的至苦者所做的高尚工作表达敬意。当她走上领奖台接受奖项并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我看到无论是她的着装还是她的精神,特蕾莎修女跟她在加尔各答时毫无二致:她态度谦逊,却又聪慧过人,拥有坚定的价值观。在她的感言中,特蕾莎修女谈到了为穷人服务的荣幸,当然也谈到了全程指引她前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在疲倦不堪、追求物质的古老欧洲,听到这样的启示着实很不寻常,这位身材瘦小的女性将整个诺贝尔奖大会握在了她的手掌心。
仪式结束后,她与一些媒体进行了非正式的会面,我谨慎地靠近特蕾莎修女,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我;离我在加尔各答跟她见面时已经过去了三年多的时间。我有这样的疑虑真是愚蠢。我刚一走上前,她就逗趣地咯咯发笑,朝我晃了晃手指:“你瞧,保罗,我告诉过你我们会再见的!”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我们私下简短地聊了一会儿,接着她问:“你今晚会参加我们的活动吗?”
“会的,院长。我是绝对不会错过的。”
这天晚上,大批的民众冒着冷风和严寒聚集在一起,为的是陪特蕾莎修女漫步奥斯陆街头。他们来自挪威各地以及欧洲的其他地区,还有很多人来自于印度,全都是为了瞻仰特蕾莎修女,声援和平以及世界各族人民间的深入了解。特蕾莎修女走在人群的前面,脚上穿着她平时那双皮革凉鞋和那件蓝白衣衫,唯有一双羊毛袜和一条厚厚的羊毛披肩供她保暖。起初,人群在行进时保持肃静,后来,人们开始自发地唱起歌来。在多种语言汇集而成的动人歌声中,他们唱着圣诞颂歌和灵歌,许多人边走边举着蜡烛,用双手保护着火焰,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下来。这位女性有着怎样的灵魂啊;她激励着怎样的无尽信念与虔诚啊。
当我回到巴黎时,情绪极度低落。尽管伊达、贾斯汀、伊森和泽尔达让我倍感美妙温馨,尽管我在巴黎实现着当一名作家的梦想,但我依然会觉得压抑,缺乏成就感。看着写着特蕾莎修女的事迹促使我面对这个重大的问题:我这辈子到底在做些什么呢?是的,借助美联社的影响力和全球覆盖面,我能够向数百万人提供资讯,这无疑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公共服务,可是我究竟鼓舞过多少人呢?就算有,也只是寥寥数人。我依然很喜欢报道国际新闻时那种肾上腺素飙升的痛快感觉,但是从奥斯陆回来以后,我厌倦了当一名消防队员,厌倦了任凭外界事件和地球上每一个疯子的摆布,我烦透了时刻沉浸在恐怖、暴力、仇恨以及击溃人类心灵的其他一切当中。我需要一个新的方向,追求生活中新的使命感。我不知道该转向何处,但我知道我必须做出实质性的改变。
于是有一天,我辞职退出了美联社。
伊达,祝福她,对我的决定十分支持——她看出了我与日俱增的挫败感——但是我在美联社的老板和同事们都觉得我完全发疯了。就连跟我最亲密的一些朋友也有同感。不过,在离开美联社不久后,我手头上就有了三份自由撰稿人的工作:我向路透通讯社提供咨询服务,我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进行直播评论,我成为了《政治家报》的流动记者,这家印度主要报纸始创于鲁德亚德·吉卜林[①]的年代。不久后,我还开始了一份鼓舞人心的新工作:传授写作技巧。虽然有这么多的工作,但我的工资还是有所减少,我没有任何福利,也得不到工作保障。但是,如今的我快乐而自由。我可以跳到窗外忙着追赶松鼠。
在巴黎的一个春日,至此我已经做了一年半的自由职业工作,我正在和美国之音的巴黎记者约翰·比埃共进午餐。约翰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也是一位来自旧世界、慈父般的绅士,他的文化修养有一半为英国特色,另一半则是法国特色。我们在他最爱的摩洛哥餐厅里共同享用着一盘古斯米和一瓶红葡萄酒。我对他说,“听着,约翰。伊达和我很想带上我们的孩子去休一阵子假。你知不知道地中海附近有什么安静点的地方吗?”
约翰笑了笑。“亲爱的孩子,我还以为你知道呢!我们家在撒丁岛有一处避暑别墅,就在海滩边上,”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去那里呆上个把月呢?”
“谢谢你,约翰。这听起来美妙极了,可是我们现在手头挺紧的,在那样的地方住上一个月的时间我可付不起租金啊。”
“傻孩子,”约翰说道,“那个地方无人居住!伊莲娜和我要到七月中旬才会过去。你们为什么不去那里,在海滩上呆一个月,把那地方打扫收拾一下,整理得井井有条,方便我们过去住呢?你们会帮上我们一个大忙的。作为交换条件,我们可以把租金定为……哎呀,我说不上来。一个月300美元可以吗?怎么样?”
怎么样?哪有这样的好事啊!但我还是犹豫了许久。“呃,约翰,这事有点儿难以开口,不过我们可不可以带上我们的狗一块去?她很乖巧的……”
“当然可以啦,亲爱的孩子!那个地方简直就是狗的天堂!”
于是,巴黎狗女王泽尔达的下一章历险记就此开启了。我们从印度来的小小流浪狗已经征服了巴黎,而且现在要向意大利的撒丁岛进发,前往地中海附近的一座房子啦。
一开始,我对撒丁岛几乎一无所知。不过,在查了地图做了点研究之后,我发现撒丁岛是地中海第二大岛,仅次于西西里岛,它坐落在科西嘉岛的正南方,位于古代地中海商贸和船运航道的心脏地带。这座岛屿的定居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约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此后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罗马人、西班牙人和一个名叫汪达尔的德国部族都曾于不同时代占领过该岛。撒丁岛现在是意大利的一个自治区,享有高度的独立性。从我读到的资料来看,岛上的萨德人保留了他们特有的方言,以及想要维持他们独特传统、文化和美食的坚定决心。这些听起来很有意思。但是,我也读到,岛上有一处名流专属的胜地叫翡翠海岸,吸引到欧洲的不少豪华游艇前来游览,开销不菲。于是,我打电话给约翰道出了我的顾虑。我会不会在撒丁岛上破产呢?
约翰哈哈大笑。“亲爱的孩子,你去过肯塔基州的边远地区或是纽芬兰的荒野海岸吗?”
“呃,没有……”
“好吧,我也没去过。但是,我敢肯定我们所在的撒丁岛地区比起翡翠海岸来更像是这些地方。我可以向你保证,索菲娅·罗兰不会在我们的海滩上享受日光浴,碧姬·芭铎同样不会在那里现身。实际上,除了一些当地居民之外,那里的海滩完全归你们尽情享受。”
约翰随后给了我一份清单,将他在离他家最近的城镇穆拉韦拉最喜欢的商店和市场一一列出。他向我保证说他所在的撒丁岛地区依然是一块隐秘的珍宝,纯朴而文雅,并且可喜的是那里的自然之美未遭破坏。开销也承受得起。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收拾行李出发了。
到了六月份第一个星期的周末,一切准备就绪。伊达和我将行李装上汽车,给贾斯汀和伊森系好后座上的安全带,狗女王也跳上了车,蓄势待发准备前往地中海海滨享受一个月的欢乐休闲时光。为了这趟皇家之旅,伊达准备了一个体面的宝座,先用一袋潜水装备垫在地上,上面再放上一个舒适的枕头来确保安全。在那里歇息时,泽尔达可以在贾斯汀和伊森中间舒展身子,将前腿伸到伊达和我中间的控制台上。我向你保证,为了我们的小姑娘,我们在所不惜。
我们一路上尽情玩乐,和贾斯汀、伊森玩文字游戏,聆听音乐,享受在开阔公路上驾车时的快感。在第一天时,我们沿着勃艮第、里昂和罗纳河谷一路畅游,当天晚上我们在阿尔卑斯山脚一家古雅的乡村客栈里落脚。这个地方不仅接纳狗狗进入房间和餐厅,而且还对泽尔达热情欢迎。第二天驾车沿着连绵的阿尔卑斯山行进,穿过勃朗峰隧道,然后顺着地中海海岸前往热那亚,在那里搭乘晚上六点钟开往撒丁岛的夜班渡轮。我们抵达码头时离开船还有充裕的时间,我们将车开到船尾加入停放汽车的长队列中。就在我们等待登船时,我们在汽车旁边给泽尔达喂食。接着我们让她最后散个步,解个手。说句实在话,泽尔达一路上作为旅客表现得规规矩矩。“嗯,”我心想,“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