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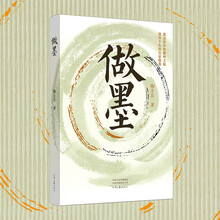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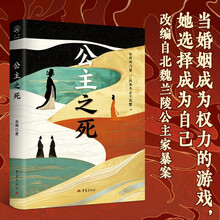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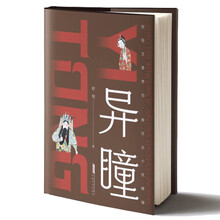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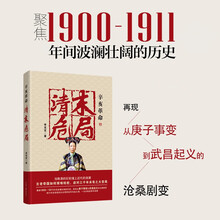


1.这是知名历史作者陶短房有关太平天国的一组历史小说,多年来仅在天国迷中流传并深获好评,首次结集出版,将带给读者全面、震撼的阅读体验!
2.陶短房以《这个天国不太平》闻名于历史写作圈,他的文字有历史的高度、文学的温度,场面雄浑,细节真实,情感真挚,发人深省。
这是一本中短篇历史小说集,所有作品皆以天平天国为题材。作者浸淫太平天国史料多年,尝试以小说形式再现太平天国的时代氛围、社会状况、人物命运。书中展现了苏州降城、天京失陷等重大历史事件,描写了上至幼天王下至普通将士的跌宕命运,呈现了敌我双方在对峙、杀戮中的所思所感,为读者描摹出太平天国具体可感、血肉丰实的一面。
月圆(节选)
夜已深,风仿佛也停了。波涛渐消,湖水如镜,把一轮圆月倒映得玉碗冰盘般晶莹皎洁。
一切抵抗仿佛都已结束,寨墙内外,唯有大小黄旗纷披。
街上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路边林里壮丁们的伏尸,井台池畔投水妇孺们遗下的鞋袜钗环,也狼藉着无人收拾。
喇叭赵迷惘地望着这一切,漫无目的地走着,腰间,瘪了口的喇叭血迹斑斑,手中的矛子却已不见了踪影。
“光棍刘,你干什么!”敞开的院门里,突然响起铁柱的大嗓门来。
“长毛富贵长毛富贵,我……”光棍刘的声音怯怯地听不真切。
循声穿堂入室,却见光棍刘惶惑地站在张雕花大床上,满怀抱的珠玉绮罗;铁柱一手横刀,一手叉腰,正怒目而对。
他们中间的屋梁上,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直挺挺地吊着,晃荡着,她的头发披散着,身上只穿着内衣,衣物首饰,想必都已入了光棍刘的怀抱。
“罪过罪过!光棍刘,快放下!”
喇叭赵一手掩目,一手过去拉扯光棍刘。
光棍刘往墙角缩了半步,嘴里不住嘟囔着:“哼,她是自己寻死的,须不是我图财害命。说是长毛富贵,当官的有圣库,我们呢?你们不要是你们的事,我……”
“住口!”
黄功勋佝偻的身体突然出现在门口,熟悉的浔州腔已带上了颤音。
光棍刘手一软,珠玉绮罗,落了一床:
“黄……黄……”
黄功勋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用竹棍不住指指点点:“尔们看看,尔们看看,这还叫圣兵么,当年东王领兵,合营兵将有妄入民宅者,不论官职大小,左足踏入便斩左足,右足踏入便斩右足,尔们、尔们……”
他咳嗽着,喘息着,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光棍刘蜷缩在墙角,嗫嚅着不敢还口。铁柱狠狠地瞪着他。
喇叭赵吁了口气,上得前去,便要解下梁上吊着的妇人。
“娃崽,还是我来吧,”黄功勋一边唠叨,一边站上方凳,用独手吃力地解着绳扣,“总宜男分男行女分女行么,我这把年纪,方不碍事呢……”
“娃崽们,让开让开!”
他用独臂托着妇人的尸体,小心地放在雕花大床上,慢慢踱向墙边的红木立橱。
“光棍刘尔这物件,竟然剥妇人衣物,也不怕皇上帝降罪。唉,这橱里总有些衣被吧……”
他一步步走到立橱前,伸出独臂,拉开了橱门。
“啊——”
一声女子的惊叫,紧接着便是黄功勋的惨呼声和猝然倒地声。
众人急看时,却见橱门大开,一个不过十三四岁,红红衣服红红脸蛋的少女怔怔地站在橱里,手中剪刀闪亮,鲜血一滴一滴,落在衣上鞋上。
黄功勋仰面倒地,独手捂住胸口,血汩汩地从五指间渗出,他的浊眼大睁着,嘴里喃喃,不知念叨着什么。
众人都呆住了,半晌,铁柱大吼一声,挥刀扑到橱前。
少女的头发飘拂着,幽幽的眼神,仿佛天上皎洁的圆月。
铁柱的刀凝在半空,劈也不是,不劈也不是。
喇叭赵也冲了过来,俯身扶住黄功勋的头肩。
那少女忽地烟波流转,一咬牙,倒转剪刀,刺进了自己的咽喉。
霎时血光喷出,众人眼前,迷茫一片红雾。
“当啷啷!”
剪刀钢刀,几乎同时落地,屋里一下子变得死一般寂静。
“哈哈哈哈——”
半晌,光棍刘嘴角扭曲,突然发出一阵毛骨悚然的狂笑,纵身撞开方格窗,跳了出去:
“长毛富贵,长毛富贵啊——”
“娃……娃崽们,别……别费事了,”铁柱和喇叭赵又是哭唤,又是包扎,良久,黄功勋才挣扎着吐出半句话来。
“契叔,您……您老歇歇,我们……我们……”铁柱哽咽着道。
黄功勋笑了笑:“哭什么,升天头等好事,宜欢不宜哭,金田……金田团营时我……我们寨子一同入营男妇四十三口,我……我已经是最后一个了,我……我……”
他失神的老眼突然闪出一道光芒:
“堪嘉弟妹耐心坚,立志勤王不怨天,止愿纲常同顶起,不因……”
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眼里的光芒也一点点地黯淡。
天似乎开始放亮了,湖水如镜,把一轮圆月倒映得玉碗冰盘般晶莹皎洁。
“……那会儿你们从寨墙上败退下来,黄功勋把我拉到一边,突然给我跪下,流着眼泪说:‘娃崽,当年三十检点打武昌,也就你这般年纪,这寨墙,只有童子攀得上,咱们几千天兵,这回都靠你的了。’于是我带了红粉葫芦 和先锋包 ,偷偷从湖壁攀过寨墙放……”
祠堂前的旷地,小把戏浑身透湿,裹着面大黄旗,骑在一个大个子圣兵的身上,正神采飞扬地述说着,他的身边,十几个兵将笑嘻嘻地团团围着。
喇叭赵和铁柱低着头,慢慢地蹭过来,听得黄功勋的名字,眼睛都不由得一酸。
“是你们啊,黄功勋呢?”小把戏居高临下,一眼望见熟人,笑得更欢了。
铁柱使劲扭过头去,喇叭赵忍住泪水,伸出双臂来:
“下来吧,我带你去找熊大人。”
小把戏伸手欲扶,忽地指着祠堂,欢声叫着:
“灯笼灯笼!”
祠堂高高的廊柱上,火红的灯笼摇曳着,映着黎明淡淡的月色。
“喇叭叔,你答应我的,你答应我的!”小把戏叫嚷着,笑得更欢了。
这个灯笼真的很大,虽然不是兔儿灯。
喇叭赵往手心吐了口唾沫,伸手扶住柱子。
战了一夜,浑身酸软,右腕更是兀自隐隐作痛。
身后,十几个兄弟鼓噪着,小把戏更是大叔长,大叔短,一声高过一声。
喇叭赵深吸一口气,作势欲上。
“慢着,”一只大手突然按住他的手背,愕然回头,熊丞相满面征尘,眼带血丝,嘴角却挂着笑意,“你的手有伤,这个灯笼让我来取!”
不待喇叭赵答话,他已经纵身而起,手足并用,三两下便攀了六七尺高。
不一会儿,他的指尖已经触到了灯笼的穗子。火红的灯笼摇曳着,映着黎明淡淡的月色。
小把戏已经从别人肩上跳下来,伸展着双臂,笑着跳着,奔向那团火红。
熊丞相憨憨地笑着,一手扶柱,一手伸向灯笼。
“轰”
一声巨响,一团飞焰,霎时间,肢体血肉,欢声笑语,红灯圆月,都被这霹雳击得粉碎,化作漫天纷落的血红。
血城(节选)
太阳渐渐地高了,又渐渐地低了,几点星帆,稀稀落落地点缀在大江之上。
“熊哥,好久了,那许老四该不会反草把咱哥俩给卖了吧?”
泥鳅的衣服早已一点点捂得干了,心情却也似乎因此一点点变得躁急了起来。
“应该不会,”熊有方沉吟道,“他若反草,妖兵妖练早就来了,如何能待到这般辰光?我倒是怕这兵荒马乱的,采石干……”
正说着,山崖那边,忽地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细微的脚步声。两人脸色都是一喜:
“来了。”
许老四吭哧吭哧爬上崖来,一屁股坐在石头上,一面喘,一面把两个包得密密实实的大油纸包塞到熊有方手里:
“哎哟妈呀,可累死我了,这柴老实针鼻儿大的胆子,小老儿好说歹说,好歹给做了两包。唉,这世道,人情比纸薄,半点也不假。”
熊有方把油纸包小心翼翼放进革囊里,从胳膊上褪下个金钏,递了
过去:
“偏劳你了,这金钏,便当作使费好了。”
许老四犹豫片刻,伸手接过:“也罢,不是小老儿贪心,这柴老实一番惊吓,却不能叫他白受吧。熊大人,泥鳅爷们,你二位在这里耐心猫到日落,顺着那条小路去码头,寻条下水船,和来时一样,照样划葫芦回天京吧,小老儿这便回去了。”
熊有方和泥鳅正待再客套几句,忽听不远处,许老四适才来路上,响起一阵铿锵喧哗之声:
“柴老实,你瞅明白了?那两个长毛贼,果是往这里来了?”青布头巾,青布号衣,刀枪、棍棒、旗帜、绳索,足有五六十号壮丁。
“回……回练总老爷话,不……不会有错,是许……许多日子前见过的长毛,自小人家里出来,便……便直奔这条路下去了。”
“嗯,我来问你,他们奔这里来,是你亲眼所见?”
“是……不……不是不是,是……是小人估摸着……”
“混账东西!这样大事情,能胡乱估摸么?本练总出一次队,每个练丁便是二斤酒,二斤肉,半吊足钱,你……”
“该天杀的柴老实!”
熊有方等三人躲在大石下,不敢出声,也不敢乱动,六目相交,心中无不这样恨恨咒骂着。
“老爷别和这刁民一般见识,”一个师爷模样的人劝那练总道,“照学生看来,这两个发逆必是顺此小路,直奔码头,妄图混出卡子逃窜。”
“奶奶的,不早说!”练总骂道,“兄弟们,给我撵!”
他忽地回头,看一眼身边瑟瑟发抖的柴老实:
“来人,把这混账绑了!”
柴老实大惊:
“老……老爷,我冤,我冤哪!”
“你冤老爷不更冤?快绑上!”练总嗔道,“此番拿住发逆,算你小子走运,若拿不到,老爷也不能白出钱出力,只好把你小子割了舌头送官,就算是长毛窝主——愣着做啥,还不给老爷我追?”
练丁们的呐喊声杂着柴老实的哀号声,很快湮没在江风江涛声里。
“许老四,此番连累你了,”熊有方歉然道,“你速走,速走!”
许老四连连跺着脚:“你们哪,你们要打来便打来,要退走便退走,何苦这样偷鸡摸狗地跑了来?你们这下子可把小老儿我给害惨了!”
他话锋一转,瞠目道:“叫我走?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嘛子办?走得了就走,走不了就拼呗!”泥鳅哼了一声。
“走?拼?码头已去不得,官兵、团练,那许多人枪,你们两个浑身是铁,能捻几根钉子?再说,你们身上,还背着几万条性命,死不得啊!”
熊有方和泥鳅都低下头,不再言语。许老四急了,一把一个,拽住两人衣袖:“愣什么愣?还不跟小老儿走?”
“崖下这去处叫做望渔津,原是江上捕夜渔避官家渔税的苦哈哈们泊船的浅滩,如今江上风声紧,渔船都归大渡了,可这采石沿江五十里,除了码头大渡,便只有这里下得水。二位都是老船客,好水性,下江这点水路,好歹漂得过吧?”
许老四一面走,一面小心翼翼地望着崖上和四周,见没什么动静,顿了一顿又道:“这条乱石小路是小老儿打柴采药摸出来的,没第二个人知道,你们下了水就赶紧游得远远的,没事莫再回来祸害人了!”
熊有方使劲拍了拍许老四佝偻的腰背:“许老四,你宽草,我们天兵若再来,必是带了几百号战船打回来。”
“不好了!”
走在最前面的泥鳅忽地跑了回来,一脸的气急败坏:
“熊哥,你来看!”
望渔津,嶙峋山崖边伸出的一片浅滩上,新搭出一抹凉棚,棚外或坐或躺着八九个标兵,凉棚顶上,有气没力地耷拉着一面红旗,红地,白字:
官办船厘。
许老四脸色登时煞白,口中不住叫苦:“该天杀的官兵,啥时候在这兔子都不来的地儿添了个厘卡!”
熊有方看了泥鳅一眼,点了点头:“泥鳅,此番用得上你我弟兄的大刀了。”
泥鳅会意一笑:“熊哥,留神着采石干,老四,你歇着,看爷们诛妖!”
两人呼啸一声,齐刷刷拔刀跃起,几个兔起鹘落,已扑到凉棚边,刀光过处,登时砍翻了两个。
“长毛!”
标兵们惊呼着跃起散开,但旋即发觉对方不过两人,胆气稍壮,摸刀捻枪,又重新围拢上来。
“挡我者死!”
熊有方和泥鳅如两头出山猛虎,两口钢刀旋舞如飞,连连惨呼声中,标兵们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
“砰!”
一声枪响,熊有方魁伟的身躯猛地晃了一晃,旋即又怒吼着扑了上去,转瞬间,那个放枪的营弁,和剩下的两三个标兵,都被两人的钢刀,劈倒在凉棚外的血泊之中。
“熊哥……熊老爷,你没事吧?”
许老四从山脚奔出,和泥鳅一起扶住了熊有方。
枪声的余音,犹在江面山崖间回响着。
熊有方拄刀挺立着,胸口血糊糊的一大片,嘴角却挂着笑意:
“这妖崽子,惶急之下,没装子药 ,否则老熊早升天见天父去了。”
两人都吁了口气。熊有方放开刀柄,伸手解下染血革囊,小心地系到泥鳅身上:
“兄弟,你快下水,带着这采石干,顺江直游进天京去。”
泥鳅一惊:“熊哥,嘛子这样子讲,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便了。”
熊有方怒道:“糊涂话!我如今中了枪,下不得水,如何拖累你?”
“熊哥……”
熊有方真急了:
“你再磨蹭,须误了天国江山社稷!”
泥鳅一咬牙:
“熊哥,天父看顾!”
“许老四,你速走吧,莫陪我白送了性命。”见泥鳅已游得远了,熊有方转脸看着许老四道。
许老四苦笑一声:“小老儿不想死呢,可是晚了。”
他伸手一指,顺指望去,团练的旗帜缨枪,已在不远处的山石尖跳跃。
熊有方扫视一眼周围,见凉棚里堆了几桶火药,捂着胸口的伤处,慢慢走了过去:
“许老四,有火镰没得?”
许老四黑着脸,寻了根干柴,哆哆嗦嗦地点起根火把来:
“也罢,也罢,小老儿这把年纪,没亲没故的,活也活得够了,熊老爷,听你们王爷讲道理,你们活着坐小天堂,死后便上大天堂,永远享福,永远威风,如何,让小老儿也沾些光吧?”
熊有方朗声长笑,宽阔的脸膛被火把照耀着,显得一片明亮:
“好老四,来来来,你我同登天堂享福!”
许老四跨前一步,又停住了,把火把递给熊有方,伸手捋下金钏,放在凉棚口的地上:
“欠柴老实的采石干钱还没给呢,都上大天堂了,好歹不能辱没了天国的颜面。”
“轰!”
当惊魂未定的练丁们战战兢兢地蹭到夷作一片白地的凉棚边,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禀老爷,棚外俱是官兵的骸骨,棚内死了两人,都炸得烂了,连脑袋也找不着。”
练总嘟囔着咒骂了几句,忽见不远处金光灿灿,见是个金钏,赶忙奔去捡起,揣进怀里:
“呸呸,大吉大利大吉大利——也罢,这回总算没干赔本买卖,来人哪,把那小子放开吧!我说柴老实,你想明白了,长毛就是两个人,是也不是?”
“那个……是!是!”
柴老实嗫嚅着呆立在原地,不住揉着被绑得酸麻的胳膊。
“你咋地还不滚?”练总不耐烦了,“留你条性命就算本老爷格外开恩,咋了,你还想领赏不成?”
夕阳下的江水,默默地向东流去。
泥鳅头也不回地奋力划着水,他的眼睛湿润着,也不知是血水,江水,还是夺眶的泪水。
血路
月圆
血城
血洲
椎沙
孤城
鹦鹉之魂
陶短房的历史小说极好,而且这个系列,都是从小人物视角切入大时代,当年也给我很大的震动。
——百度读者 april_chan
看这小说(《椎沙》),忍不住觉得,越是小人物,越能够察觉本质和真相,选择的余地却也越小……
——流觞亭读者 如耶如也
我认为《血路》这篇小说的精彩在于它的直面现实与鲜血。作者不加掩饰地揭露了屠杀,但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破口大骂,文中所包含的谴责和同情,都是十分深沉的。
——天涯读者 numzero
老猫虽然没有经过战争,但是能够把几场战役描写得如此扣人心弦,如此悲壮与连绵起伏,实在是让人说不出话来。
——流觞亭读者 游子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