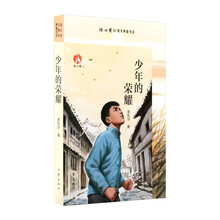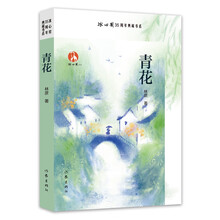那一天早晨,寒梅给我打来电话,尽管电话里她的声音已经颤抖得有些语无伦次,然而我还是从她那夹杂着断断续续哭声的陈述中听到了一个使我震惊得几乎跌坐在那一片刚刚浇过水的绿茸茸的草坪上。那一天的早晨风很大,把我刚刚从眼睛里涌出来的泪水一转眼便吹得无影无踪,几乎没有留下一丝泪的痕迹。
妻子从房间里欢快地走了出来,她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递到我的手上,并且给我捋了捋被风吹乱了的头发。当她看到了掉在草丛里的手机正在无辜地遭受着水的洗礼,脸上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我告诉妻子,卷毛儿在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长着荒草的、能够看到大海的山坡上……饮弹自尽了。他死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张已经发黄了的被烧掉了一个角的旧照片,照片上的那个梳着两条小水辫,清秀的、有些羞答答的少女,就是寒梅。那张照片应该是寒梅20多年前和卷毛儿刚刚谈恋爱时照的。卷毛儿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从中国带到了美国,又从北加州奥克兰的家,带到了那个长着荒草的、能够看到大海的山坡上。
寒梅悲痛欲绝,她说她将以妻子的身份料理卷毛儿身后的一切事宜,包括替他偿还他所欠下的一切债务。等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她将带着儿子回到中国去,不再来美国了。那样,她就和卷毛儿彻彻底底地断绝了。她说卷毛儿激怒了上帝,是上帝把他带走的。她还告诉我,过几天她会来我们家,或许还会住上几天。
寒梅是属于卷毛儿的女人。这种属于是牢不可破的、是上帝的指派。然而卷毛儿来到美国后身边却又有了另外一个叫杨雪的女人,那个叫杨雪的女人不是上帝指派的,所以他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于是,上帝便发给了他一支枪和一粒子弹。在他临别的时候,心里一定在狂呼着寒梅的名字,而他手里捏着的那张旧照片,也似乎在向上帝表白,他的心除寒梅外,从来没有爱过其他女人。
卷毛儿是属于寒梅的男人。是上帝把卷毛儿领到了寒梅的心里。既然是上帝的指派,寒梅也就义无反顾、心无旁骛地爱着卷毛儿。然而当卷毛儿来到美国后,像那么多来到美国的孤男寡女一样,辜负了上帝最初的旨意而另寻新欢,肆意妄为,寒梅心灰意冷了。她拒绝了上帝的旨意,像卷毛儿一样,从中国一个荒僻的小城来到了美国,来到了洛杉矶,像一个探险者,用她的躯体和灵魂宣泄着对卷毛儿最严厉最冷酷的审判,直到卷毛儿心灰意冷地用那粒子弹洞穿了他自己的头颅而宣告对自己救赎的终结。或许,寒梅就是上帝发给卷毛儿的那支枪和那一粒子弹。当一切都烟消云散的时候,寒梅才清晰地意识到,其实在她的心里也和卷毛儿一样,从来就没有装过除卷毛儿以外的任何一个男人,包括她现在的丈夫,那个也是长着一头卷发的美籍犹太裔的老男人毛瑞斯。
卷毛儿最后一次从我们家走的时候好像对我说过,他将做最大的努力和寒梅沟通,请求她的宽恕。尽管寒梅现在已经有了家庭,有了丈夫,但他还是想挽回她的心,除此之外他好像也别无所求了。记得,临走的时候他从他的那辆已经开了四五年的破旧的小货车里取出一个塞得满满的黑色小皮箱交给我,让我保管,如果有机会再让我转交给寒梅。我似乎从来没有看到过卷毛儿如此地沮丧过,说话有些语无伦次,从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悲哀与绝望让我感到不安甚至恐慌。
“你应该看一看心理医生。”我一脸的严肃,并没有和他开玩笑的意思。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