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飞机在寻常可怕的八月天,于一个格外闷热不快的礼拜二晚上八点二十五分飞离肯尼迪机场。两个礼拜以来,气象报告一直向早知此事的人们预测,老天将会降下甘霖,让热浪稍歇。但老天却丝毫没有下雨的迹象,热浪不退,直到气象播报员似乎竞相在拿气象预报作为赌注,执拗地在阴雨凉爽上加倍押注,而晴朗炎热的天气仍然持续着,让人苦闷不已。如果他们再不快点赢得赌注的话,就要黔驴技穷了。在此同时,我们则纷纷“跑离”纽约。
当然,不是真的用跑的离开,我们是要“飞离”纽约。在登上庞大的727客机,系紧安全带,聆听如何适当使用氧气罩的示范说明后,我突然有个错觉,仿佛我们不是正要逃离或飞离纽约,到蒙特利尔去,好像只是要开车离开。
客机不断前后滑行,机长在客机还未飞离地面前就滑行了好几英里。米娜握紧我的手。我低头看她,她噘着嘴,一脸紧绷。
“你说我们会飞的。”她说。
“我们会的,耐心点。”
“这真的是一架飞机吗?”
“当然。”
“它表现得一点也不像架飞机。”
米娜曾经坐过一次飞机,那是一架我们从爱沙尼亚导弹基地劫持而来的苏联战斗轰炸机。那时我们是垂直起飞,因此我可以了解飞机现在在跑道上的滑行为何使她失望。我向她保证,727客机的确是一架飞机,它很快就会表现得像一架飞机,但我想她并不相信我。
机长在又滑行了十五分钟后,通过对讲机致歉,并且自我介绍。我还以为他将会告诉我们,飞机上有炸弹,或蒙特利尔的机场已因淡季而关闭。他的解释令人沮丧:我们前头排了六架飞机,但迟早会轮到我们起飞,感谢我们的耐心等待。
米娜用立陶宛语说了些粗话。
“小心点!”我说。
“没有人听得懂我说的话呀,伊凡。”
“那就是重点。”我轻拍她的手,“在我们进入加拿大前,请你只说英语。你要记得,你是美国公民,出生于纽约,名字叫米娜·谭纳,只会说英文。”
“好吧。机长是个——”
“说正规的英文。”
“——不错的人。”
她不是个美国公民,也并非出生于纽约,更不是叫米娜·谭纳,而我也不确定她会说多少种语言。她会说流利的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英语和波多黎各西班牙语。她还从我公寓里的书籍、录音带和偶尔来访的客人身上,东拼西凑地学了许多语言。那间公寓虽然是我在住,当家的可是她。她是明道加斯硕果仅存的直系子孙,而明道加斯是立陶宛七个世纪以前唯一的国王。
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住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个阴郁的地下室里,由一对胡涂愚蠢的老女佣照顾,她们一心等待着她登基成为立陶宛女王的那天。我将她带离那些纷扰,而现在,在我那位于第107西街的舒适公寓内,她俨然是位女王。有时候我会威胁她,说要送她去学校读书,或让在快乐郊区拥有快乐房子的快乐夫妇收养她算了。但她和我都知道不会发生这种事,因为她带给我很多乐趣。自从凯蒂·巴塞里恩的外祖母教会她怎么泡美式咖啡后,我就少不了她。
“我们要在这飞机上坐多久呢,伊凡?”
“飞行时间只有一小时,如果我们开始起飞的话。”
“然后我们会抵达蒙特利尔?”
“是的,但我们的行李会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
“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从不信任航空公司。我是开玩笑的,没错,我们会在蒙特利尔降落。”
“我们今晚能去看世界博览会吗?”
“今天太晚了。”
“我不累,伊凡。”
“等我们到饭店时你就会累的。”
“我不会。我很少觉得累,伊凡。就像你一样,我不怎么需要睡眠,根本没睡多少。”
我看看她。米娜一天平均睡十小时,很健康的数字。我根本不睡觉,在朝鲜的榴弹碎片击中我的脑袋,破坏所谓的睡眠中枢后,我就丧失这个能力,从那时起就不曾睡着过。我每个月领一百一十二美金的残障补助津贴,一毛都不用花在睡衣上。
“如果我们今晚去看世界博览会,”米娜小心翼翼地说,“我明天可以睡到很晚。我不希望你为了我,延迟去博览会的时间。我今晚可以熬夜,明天再补觉。”
“你很体贴。”
“没什么。”
“你上礼拜六也很贴心,自愿陪桑妮亚去儿童动物园。”
“她想去看呀,伊凡。成人除非有小孩陪同,才能进去参观,我只是帮她个忙。”
她陪所有我带去公寓的女人到儿童动物园去玩,把她们哄得服服帖帖。“如果你这么想去的话,”我说,“我们今晚就去世界博览会。”
“我只希望对你公平点。喔,这的确是一架飞机耶!”
它的确是。我们最后终于得到起飞许可,庞大的客机轰隆隆地驶向跑道,然后起飞。我靠坐在椅背上,米娜的脸贴着窗户,看着地面逐渐离开视线。
飞机飞离地面后,表现得可圈可点。我喝了一杯酒,米娜喝了牛奶。等我们喝完时,机长再度通过对讲机咕咕哝哝地要我们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降落杜瓦尔机场。我们没有松开安全带,因此无此必要。降落相当平稳。飞机慢慢滑行,最后停下来,我们下机。
我们跟着乘客进入机场,排队拿行李。行李从输送带的斜坡冒出来,跟着输送带旋转。我第一次没有抓到我们的行李,只好静待它第二次绕过来。我们到另一支队伍排队,经过一个桌子,说着法文腔调的海关人员要加拿大人排左边,美国人排右边。我们排到右边。总共有三支队伍,我们选择了最短的那排。
我将护照放在西装口袋里。其实进入加拿大或回到美国并不需要护照,但航空公司的作业人员建议我们带着公民证明,反正我也喜欢在旅行时带着护照。
我带的是假护照,但它闯关过无数次,我已经不会紧张了。一位和蔼的亚美尼亚老人在不久前于雅典帮我做了这个假护照,因为捷克政府没收了我的真护照。假护照上有所有的正确信息,包括真护照的号码,所以我不担心。但米娜的护照可就是真的了。我们所需要的文件不过是纽约的出生证明,诺福克街的一位克罗地亚国家主义分子在十五分钟内便办好这件事,而且不收费用。我以前曾经帮过他一次忙。
“你的名字是米娜·谭纳,出生于纽约。”我说。
“我知道,我知道。”
“我是你的父亲。”
“我知道。”
队伍往前移动,轮到我们排到最前面,海关人员有着波浪般的黑发和削瘦的鼻梁,微笑着,问我们叫什么。
“伊凡·麦可·谭纳。”我说。
“米娜·谭纳。”米娜说。
“你们是美国公民?”
“是的。”
“你出生就是?”
“是的。”米娜说。
我畏缩了一下,他微笑着。“你在哪里出生?”他温柔地问。
“纽约市。”
“纽约市?”
“是的。”
他说:“你为什么来蒙特利尔,你姓……”
“谭纳,来看博览会。”
“来看博览会。你打算待多久?”
“大约一个礼拜。”
“大约一个礼拜。是的。”他本来要说什么,但突然住口,皱了一会儿眉头,然后打量我,好像第一次见到我。“伊凡·谭纳,伊凡·谭纳,”他说,“我很抱歉,谭纳先生,你身上有证明文件吗?”
他的法文腔调现在变得很浓厚。我将我们的护照交给他。他仔细检查护照,端详我和米娜的照片,凝视我和米娜的脸,再看看护照,无声地吹着口哨,然后站起身。“请等一下。”他说,然后离开。
米娜看着我。“有什么不对劲吗?”
“显然是。”
“什么事呢?”
“我不知道。”
“护照有问题吗?”
“我想不是。”
“你说要进加拿大很简单,根本就是畅行无阻。”
“我知道。”
“我不懂。”
“我也是。”
“那人去哪儿了?”
我耸耸肩膀。我想,他们也许收到一份通缉名单,罪犯的名字跟我很像。也许有个叫伊凡·马纳的蠢蛋凑巧从国家银行盗用了几十万块。我想不出有什么问题会让他突然转变态度。
他终于回来了,跟在一位较为年长的男人后面,这个男人白发苍苍,蓄着小胡须。年长的男人说“请跟我来”,而年轻的关员则说“请你们跟他走”。我们遵照指示。白发苍苍的男人领着我们走过走廊,到一个小房间,门口有武装警卫看守。米娜抓着我的手,一声不吭。
房内只有一张沉重的木椅放在桌子后面。白发苍苍的男人坐上它,我们则站在桌子前面低头看他。他的桌面上摆着我们的护照,他翻阅一叠文件。
“我不懂,”我说,“有什么问题吗?”
“伊凡·谭纳,”他说。
“没错。”
“纽约市的伊凡·谭纳。”
“正是。我不——”
他眯起眼睛看着我,“也许你可以告诉我,谭纳先生,为何你对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独立运动如此热衷?”
“喔。”
“没错。”他再度翻阅文件。“你不是加拿大人,”他说,“也不是法国人,从未住过魁北克,在这里也没有亲人。但就我所了解,你是一个最激进的独立组织,也就是魁北克国家运动的成员。为什么呢?”
“因为语言和文化的不同会构成国籍的差异,”我听到我自己说,“因为魁北克是法语区,而且将会永远都是法语区,尽管沃尔夫打败了蒙特卡蒙。因为英国殖民主义两个世纪以来的统治无法改变加拿大法语区和加拿大英语区大相径庭的这个基本事实。因为兄弟阋墙,家则不保。因为——”
“拜托,谭纳先生,”他的手摸着额头,“拜托……”
我并不想说这些的,我真的不想说,但这些话就这样脱口而出。
“我可不想听你的政治哲学,谭纳先生。这些日子以来,任谁都可以听到那些极端荒谬的论调,读到独立派报纸的疯狂理论。我早听过这些论点,而且认为它们很可笑。我无法相信加拿大的法语人口会听得下这些谎言,但显然有一小部分人是相信的。每个社会都有疯狂的偏激论者。”他摇摇头,悲叹疯子和偏激论者的存在,“但你不是法国人,也不是加拿大人。我再问你一次,你热衷的是什么?为何要介入根本和你无关的事务?”
“我同情它的理想。”
“即使那不是你的理想?”
跟他争论毫无用处。人们不是认同政治极端分子,就是将他们当作疯子。人们不是拥抱无望的理想,就是不当一回事。我大可以告诉这个讨厌的男人,我还是基里基安亚美尼亚复兴同盟、泛希腊友谊协会、爱尔兰共和兄弟会、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和地平协会的成员——我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但我干嘛增加他的反感呢?那本来就是无望的理想,而我投身效力的已经够多了。
“你为何来到蒙特利尔,谭纳先生?”
“来看世界博览会。”
“你认为我会相信你吗?”
“我不这么认为。”
“你能告诉我你的真正目的吗?”
“我已经告诉你了,但你说得对,我觉得你不会相信。”
他往后推开椅子,站起身,转过身子,走到另一端的墙壁,双手紧握在身后。我看看米娜,她一脸不悦。
“谭纳先生。”
“是的?”
“你计划在蒙特利尔发起示威吗?或是另一场恐怖行动?”
“我计划参观世界博览会,仅仅如此罢了。”
“你知道,英国女王将亲自莅临。你来此地跟她有关连吗?”
“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女人。”
他的双手握拳,闭上眼睛,身体变得僵硬。我想他大概就快中风了,这想法让我有一丝快感。然后他冷静下来,坐回椅子上。“我不打算跟你浪费时间,”他说,“魁北克国家运动是个笑话,惹人厌的小麻烦,不值得我们费心。你试图进入加拿大实在很愚蠢,更令人厌恶的是,还带着小孩同行。你当然得马上滚回美国,你在此地不受欢迎。如果你只关心美国事务,让加拿大人处理自己的家务事,我会很感激你。”他看着一张纸,“一小时二十分钟后,就有一班飞机飞往纽约,你和你的女儿将搭乘那班飞机。你将不会获准进入加拿大。你懂吗?”
米娜说:“我们不能去世界博览会了,伊凡?”
“这个男人是这么说的。”
男人倾身越过桌面,对米娜微笑。这世界上最差劲的恶棍总以为对小孩微笑就能展现他们人性的一面,“我很希望能带你去世界博览会,小女孩,但你的父亲不能进入我们的国家。”
“你的母亲,”米娜用亚美尼亚语说,“长满跳蚤,还是个妓女,跟野外的野兽杂交。”
他看着我:“那是什么语言?”
“法文。”我说。
直到登机前,他们都将我们关在房间里,米娜得去上厕所,他们派一位保姆护送她去。我们登机后,他们将护照还给我们,这次我们等待起飞许可的时间很短。飞回纽约像飞往蒙特利尔一般沉闷无聊。我这次喝了两杯酒,米娜还是喝牛奶,然后我们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抵达时间接近凌晨一点,米娜站着沉沉入睡,而我已准备好要炸毁加拿大大使馆。
我在全世界都做过非法旅行。我曾以步行、坐着驴车和躲在汽车后车厢等各种你所能想象到的方式跨越国际边界。我曾偷渡到巴尔干半岛国家和苏联,还曾开着苏联坦克车横越南北越的非军事区。
但我竟然进不了加拿大国土。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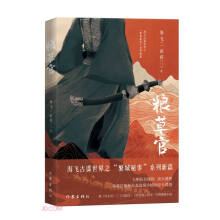



——《旧金山纪事报》
当今最佳侦探小说作家。
——《华尔街日报》
侦探小说中的硬汉……这不是轻松的闲逛,但却是一次了不起的旅行。
——《纽约时报书评》
当然,这些情节都不是真实的,可除了布洛克,还有谁能驾驭这样的故事呢?引人入胜的悬念,滑稽搞笑的场景,大胆成功的尝试……总之,这是布洛克的杰作。
——《圣路易斯邮报》
劳伦斯·布洛克所有的作品都非常有趣……再来一本,劳伦斯·布洛克。
——美联社
布洛克书中最大的主角不是凯勒,不是谭纳,也不是斯卡德,而是一个城市——纽约……令人难忘的小城蓝调,极其生动的人物,直截了当的动作,对纽约街区的细微刻画,为这个坚定无畏的故事增色不少。这本书描绘了一段充斥怀疑主义的时期,又时常闪现着令人惊艳的希望之火。
——《人物》
美国有个作家叫布洛克的,写的关于探案的书很棒。或许有机会我会跟他合作。
——梁朝伟
拍《悲情城市》时,我常让梁朝伟看些书。空闲时,他就在旁边看书。拍完后,我习惯了看到好看的书就寄给他,或者去香港时顺道带给他。他可能也介绍给王家卫看,后来他们拍《蓝莓之夜》,找的编剧就是布洛克。
——侯孝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