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的回忆录《循规蹈矩》中,讲述他如何舍弃了音乐生涯,因为,不像他的导师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他缺乏完美的音高辨别力。大约五十年后,年轻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他自己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狂热爱好者——同样放弃了音乐,最终选定电影作为自己的职业。他始终无法解释究竟是什么吸引他去从事电影工作。然而,正是在这里,塔可夫斯基发现了他自己那种形式的完美的音高辨别力,表现为准确无误的审美灵敏度和对文化冲动的敏锐反应,这使得他七部故事片中的每一部都作为重大文化事件,在苏联和全世界引起共鸣。
塔可夫斯基成名始于《伊万的童年》(1962),这个项目好像失去父母的孤儿,万不得已才被托付给这位新手导演。塔可夫斯基的这部电影拍摄于尼基塔?赫鲁晓夫1956年批判约瑟夫?斯大林之后的解冻时期,其流畅优美的拍摄方式是那个时期的苏联新浪潮运动中特别典型的。在西方,塔可夫斯基的处女作和其他电影一道,例如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的《雁南飞》(1957)和格里高利?丘赫莱依的《士兵之歌》(1959),帮助人们出乎意料地瞥见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潜在的复兴,这种潜在的复兴表现在这些电影中年轻主人公们的身上,也同样表现在电影大胆、自信的审美态度上。在国内外,《伊万的童年》都捕捉到了当下的精神,在三十岁的青春年华,塔可夫斯基发现自己在欧洲各大电影节受到赞扬,被欧洲重要的知识分子们讨论,并被推到苏联文化的最前沿。
然而,和在年龄地位上与他最接近的一些人不同,塔可夫斯基拒绝让这种称誉淹没他个人的艺术观点对他更为微妙的驱使。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塔可夫斯基常常发现自己与体制发生冲突,这种体制首先寻求保卫自己的顺利运转。他的下一部电影,规模宏大的史诗巨片《安德烈?鲁布廖夫》(1966年完成),不仅立即成为经典。苏联知识阶层还立即把它作为一种福音书接受,认为这部电影刻印了他们相当模糊的精神渴望,以及他们的受压迫感、倦怠和可能性。当然,《安德烈?鲁布廖夫》,就像塔可夫斯基后来的电影一样,由于它实验性的叙事结构以及对它发行的限制,所以不仅难以理解,而且难得一见。然而,体制阻止电影放映的笨拙努力(赫鲁晓夫倒台、解冻时期结束后,这部电影才刚刚完成,于是被搁置了三年多,直到一份拷贝神秘地发行到西方,并在戛纳电影节放映)只是增强了它的文化共鸣。《安德烈?鲁布廖夫》成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电影上的对等物,后者是一部激发了前者难解的叙事结构的小说。与帕斯捷尔纳克一样(《日瓦戈医生》在苏联遭禁后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也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不满足于他被官方认可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获得的有限成功),塔可夫斯基遭受的经历赋予了他在国内外无与伦比的文化权威。历史研究将表明,即使在被禁止的情况下,《安德烈?鲁布廖夫》也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许多最好的苏联电影(实际上包括整个苏联集团的)。在戛纳电影节获得成功后,这种影响扩展到了世界范围。塔可夫斯基随后在苏联拍摄的每部电影——《索拉里斯》(1972)、《镜子》(1974)和《潜行者》(1979)——在苏联国内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作为社会情绪的风向标和知识阶层不成熟的创造和精神渴望的发泄口。每一部都在西方作为一种天启被接受,巩固了塔可夫斯基作为继谢尔盖?爱森斯坦之后唯一伟大的俄罗斯导演的地位,他史诗般叙事的力量可以媲美俄罗斯伟大的作家和作曲家,既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又具有深刻的世界性。
塔可夫斯基1982年离开苏联去拍摄《乡愁》,苏联和意大利联合制作的一部电影,影片表面上关注的是俄罗斯人和祖国分离后感受的特殊的心痛。塔可夫斯基暂时的离开在1984年变成永久的“叛逃”, 这个事件,在某些方面标志着苏联体制最终拒绝由其最杰出的人才从内部使它恢复活力。一个令人心酸的细节是,1986年底塔可夫斯基因癌症逝世,正值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苏联自由化(改革)的开始,这场运动将迅速导致国家解体,并使塔可夫斯基被热情地接纳进俄罗斯文化的官方经典。在变化了的政治气候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成了改革时期电影院和电视节目中的主打产品。今天,它们仍然是俄罗斯文化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许多方面,塔可夫斯基的电影继续被人用其冷战的政治化来界定。对于塔可夫斯基的最后一部电影《牺牲》(1986)而言尤其是这样,这部影片常常被形容为他对世界的信仰声明,对于迫在眉睫的核战争灾难、资本主义的实利主义和现代的混乱的警告,我们感觉到的这些信息在他1986年出版的《雕刻时光》一书中得到加强。这些收集在一起的文章,是在他职业生涯的过程中撰写或口述的,但在他的欧洲流亡期间经过重大修订,它们传达了越来越强烈的僧侣式口吻,这种口吻在后苏联形势下的国内和西方都找到了心甘情愿的听众。鉴于这段历史,塔可夫斯基被当作先知并不太令人意外: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关于他自己的死亡、关于苏联的解体或者关于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然而,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中寻找女巫的预言将是严重误解它们的本质。塔可夫斯基不是试图给现实强加一种解释方案,而是将现实连同它所有的偶然性和可能性刻印或记录下来。塔可夫斯基不是一个演说家,而是观察者和倾听者。
……
长期冲突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存在了。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第六创作单元艺术委员会中,冈察洛夫斯基和塔可夫斯基已经强调,电影的名称不叫“安德烈·鲁布廖夫”。冈察洛夫斯基宣称:这不是一个关于鲁布廖夫的剧本。……我们想通过鲁布廖夫的眼睛观察那个时代,以这种形式,观众会准确地知道鲁布廖夫是谁。观众不会记得鲁布廖夫在这一或另一事件中是如何行动的,但观众会彻底了解他的心理状态。我们希望观众明白(鲁布廖夫)是如何体验事物的。塔可夫斯基补充说:“这当然不是一部关于鲁布廖夫的电影……那是一个重大错误。”塔可夫斯基从未打算讲述一个关于鲁布廖夫的特定的故事或说明,而是勾画它的轮廓,以暗示一种难以想象和再现的画面的丰富性。在艺术委员会,他把剧本形容为音乐的展开,“从大调到小调”,再从“小调到大调”。组成整个电影的各个“短篇故事”之间的联系,不在于安德烈向结局的发展,而在于“安德烈道德命运的情感运动”。在这一发展中,结尾转换到彩色以展示鲁布廖夫的圣像画,“这将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冲击效果,也许正是这一步骤在某个地方用传统方法划分了生活和艺术”。在这次和其他讨论期间,塔可夫斯基一边强调鲁布廖夫在意识形态上的相关性,一边又提出自己的任务是内在存在状态的视觉和听觉的交流,拒绝被简化为有条理的信息。
在塔可夫斯基计划、拍摄和剪辑电影期间,它的视觉话语不断地变得更加深奥和复杂。此时产生了新的困难,例如,当权者不愿为一部双倍时长的电影提供资金,以及在国外销售这种电影的困难。塔可夫斯基在每个阶段都面临着缩短电影的需要,他有意识地选择为了它“胶片的完整性”而“破坏它知性的完整性”。当这部电影渐渐接近于一个抽象的作品、一个“沉默的存在”,塔可夫斯基的同事们告诫他,实验手法可能使概念模糊,正如有人所声称已经在《伊万的童年》中发生的那样。
电影完成之后发生的故事很复杂,但是先前已经讲述过,在此没有必要完整地复述。塔可夫斯基把他大量的素材剪辑到205分钟左右,并于1966年8月26日将电影以“安德烈的激情”的名称提交,这一版本的制作如此匆忙,以至于一些演员的名字从演职员表中删去。影片被送还塔可夫斯基,并附加了一份需要修改的清单,大多是关于影片过分的长度,以及暴虐、裸体和粗俗的场景。到了1966年12月,塔可夫斯基完成了其中大部分修改,现在电影的名称叫作“安德烈·鲁布廖夫”,产生了第二个版本(该版本从未有人见过,但仍有传闻说它是存在的),结果只是得到国家电影事务委员会提出的一份要求改动的新清单,其中一些要求塔可夫斯基拒绝满足。再一次,当权者反对的最终来源从来都不清楚,但是这些反对意见肯定是相当严肃的,要求电影系统基本驳回自己最重要的产品和最重大的投资之一。罗斯季斯拉夫·尤热涅夫一边批评塔可夫斯基的固执,一边表达了对这位年轻导演困境的同情:“对于这部电影没有具体的决议,理所当然的是,塔可夫斯基无法根据传闻中的某些(官员)太太的意见,来剪贴影片。”这一僵局一直持续到1969年,这一年,电影的新版本得到批准,名称定为“安德烈·鲁布廖夫”,时长是187分钟。影片销售给一家欧洲发行商,通过角逐进入了戛纳电影节。苏联当权者直到1971年才允许国内发行,此前塔可夫斯基勇敢地挫败了若干进一步删减影片的要求。此时,塔可夫斯基和国家电影机关已经达成一种不舒服的和解,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83年。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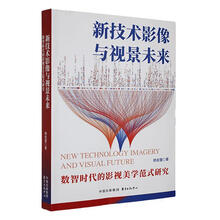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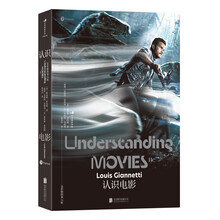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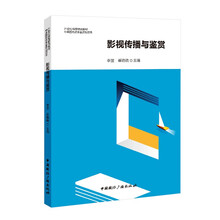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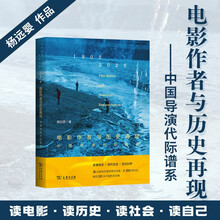

“这本深刻流畅的书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具有洞察力,思想清晰。”
——《俄罗斯与苏联电影研究》
“令人印象深刻的解释性研究。”
——《电影人》
“他(伯德)广泛涉猎文献,从经典俄语文学与哲学到当代视觉艺术,令人耳目一新……”
——《视与听》
“对塔可夫斯基研究领域的一次非常受欢迎的贡献。”
——《加拿大斯拉夫语文集》
“有关该电影导演在文献上的重大贡献。罗伯特·伯德完全熟悉英语读者难以获得的俄语文献,他对电影构造的细微差别有着非凡的敏感度。”
——P. 亚当斯·希特尼(普林斯顿大学视觉艺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