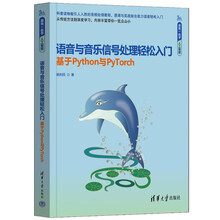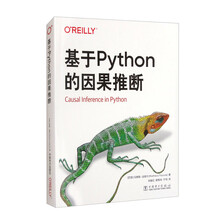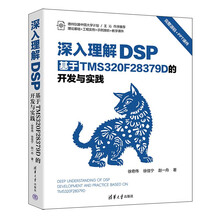1980年的夏秋之交,长沙市天气多变。那是一个阴湿闷热的夜晚,城北上大陇高坡上一栋普通四层灰楼的门前,有零星几个军人进进出出。这座老楼房虽然不起眼,可牌子挺硬——国防科技大学的招待所。两年前,这里还叫长沙工学院——当年从哈尔滨市那所赫赫有名的神秘军校——“哈军工”搬迁过来的大学,坎坎坷坷地度过了好多年,1978年6月才由“土草鸡变成金凤凰”,被中央军委、国务院批准穿上了军装,学校恢复军队编制,更名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晚上九十点钟,夜色朦胧,阵阵热风掠过树梢,招待所四周宁静而晦暗。没有住宿客人进门,招待员姑娘早躲进房间里玩扑克牌了。此时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来到大门前,他稍有一点迟疑,旋即迈过门槛,走向走廊尽头,在公共厕所间面前停了下来,他回头张望一下,才大步走了进去,从三个空着的蹲坑中选了一个较为干净的,拉上门,从里面插上门闩。
奇怪的是,这个人站在坑池边并无意解大手,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本书,借着厕所天花板那盏昏黄的电灯看起来。此时,他瘦削苍白的面容上透出一股坚忍不拔、从容不迫的气度,他在快速翻书,同时也保持着高度警觉,一旦听到脚步声近了,就马上停止翻书,屏息静气地等人离开厕所后,他才继续俯首阅读。
他是谁?他为什么要到厕所里看书?他有什么难言之隐而必须躲开人们的视线?
夜幕低垂,万籁俱寂。这个男子还在翻来覆去读他手中的那本书,且口里念念有词,看来他是想把这本书背下来。通宵不睡觉,他疲惫至极,身体靠着墙壁,不时变换着姿势,腰酸腿疼难耐之时就坐在蹲坑旁的水泥地上喘口气,厕所里污浊的空气令他头晕眼花。
一抹晨曦终于透过天窗照射进来,他闭上泛着血丝的双眼,歇息片刻,才小心地收起书,轻手轻脚地走出招待所。
他到底是什么人?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上午,这个人出现在国防科技大学一间教室的门口。教室里早就坐满了人,有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有身着绿军装的系、室领导干部,还有许多刚穿上军装的中青年教师。
等待多时的人们突然瞪大双眼,望着门外,惊讶不已。天呀!站在教室门口的这个人,身上居然穿着黑色的劳改服——劳改工厂里服刑犯人穿的那种更生布制作的粗劣工装,前排的人看清了他左胸上的四个红色小字——“江苏二监”。开天辟地,有谁听说身穿囚服的人登上大学殿堂的讲台?可现在这样的奇闻怪事就发生在声名日隆的国防科技大学了。
政治部姚副主任是今天这个特殊讲堂的主持者,他站起来,朝门口招一下手,粗声大气地喊道:“耿鼎发,你进来吧!”姚副主任鄙夷地瞥一眼包裹在劳改服里的清瘦身影,根本不屑看那人的脸,“今天听你试讲,开始吧!”
原来昨夜在厕所里看书的人叫耿鼎发!原来他是在通宵备课,为了今天上午这个试讲!
坐在下面听课的人都看清楚了:耿鼎发面色惨白泛青,没有血色,单薄瘦弱的身体表明他长期营养不良,然而他们看不到耿鼎发四肢上由脚镣手铐啃咬出来的成串疤痕……
听课的人当中有不少是耿鼎发的哈军工老教师和老同学,他们都知道,当年这位哈军工第二期优秀毕业生、哈军工优秀教员是被哈军工制造的一桩通天大冤案扔进了无底深渊,他差一点被处决,蹲了十多年的大牢,刚刚被江苏省彻底平反,来到学校要求落实政策,大半年了,国防科大那些吃政工饭的人一直在故意刁难他。这不,昨天中午突然扔给他一大本他从来没有看过的计算机专业书——《数字信号处理》,有50多万字,今天就让他登台讲课。
哎呀,他连教案都没有写,是空着手走进来的,听课的人为耿鼎发捏一把汗,他今天能讲好这两堂课吗?毕竟是刚从大牢里出来的啊。
姚副主任和几位政工干部斜靠在椅子上,嘴角挂着一丝冷笑,他们的心态与老教师们正好相反,你耿鼎发蹲了十多年的大牢,还能上讲台授课?哼,等着看笑话吧!
耿鼎发站到讲台中间,他环顾教室,刹那间百感交集。他看到那么多熟悉的面孔——自己当年的恩师和老同事们,他们的眼神传递着担忧、同情、支持和信任。他的心境突然出奇地平稳下来,他清清嗓子,先说明昨天中午才接到政治部的试讲通知,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耿鼎发拿起粉笔,面对黑板,在左上角写出本课的题目,便开始讲课,略带苏北口音的普通话清晰明快,他把复杂的科技理论深入浅出、条分缕析地阐述出来,他一边讲,一边提纲挈领地写出重点和重要的公式,步步推导,纹丝不乱,而且不断用启发性的生动语言提出问题,让听课者思考。他的板书极好,笔迹苍劲,布局合理。
不知不觉间耿鼎发从从容容把两个学时的课讲完了,教室里响起一片掌声。听课的老教师们都围拢过来,赞不绝口,没有人注意到姚副主任等人讪讪离去。副校长慈云桂教授第一个握住耿鼎发的手,不住地点头。
昨天下午,耿鼎发去找恩师慈云桂,说刚刚接到政治部通知:“明天叫耿鼎发试讲,组织专家听课。”
慈副校长闻言很气愤,他说:“这个课不能讲,这是故意刁难嘛。任何教员讲课都要有备课时间,这样搞突然袭击是为了让教授们卡掉你,好把责任推给教授们。”
耿鼎发说:“即使给我备课时间,要卡也照样可以卡掉,反而落下‘备了很长时间也讲不好’的口实,不如孤注一试,或许教授们能够宽容我呢。”
慈副校长叹口气,无奈地看看自己的学生,同意他的想法。
大半年来,耿鼎发在岳麓山上一间破旧的空木棚里栖身,现在已经来不及回山了。国防科大又是一个高度保密的单位,晚上是不容外人逗留的。住招待所当然可以,但他孑然一身,身无分文,他已经很长时间靠在湘江桥下的小饭馆里打点零工,吃人家的残汤剩饭充饥了。于是,他只好混进招待所的厕所里,靠那盏小电灯备课……
下午,慈云桂副校长拨了一个北京长话,把耿鼎发试讲的情况告诉了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张震寰主任。
很巧,出差外地多日的国防科大校长张衍在傍晚回来了。去接站的秘书小金在轿车上就把耿鼎发试讲情况特别是老教授们的一致好评,向张校长汇报了。
张衍刚进家门,北京来了电话,是张震寰主任打来的。
“情况我都知道了,”张衍擦拭着满头汗水,微笑道:“张主任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给耿鼎发同志安排工作,哈军工遗留下的这桩冤案的确让我们很被动。”
放下电话,张衍皱起眉头,对小金说:“你去把姚亚新给我叫来!”
政治部姚副主任挨了张校长一顿训斥,垂头丧气走出门,转身走向办公大楼。他抓起电话,给部下下达任务:“赶快安排耿鼎发住进招待所,再让他住岳麓山,我们都得下台!明天开始给他办理各种手续,快点办!”
第二天早晨,耿鼎发走出招待所,路过张衍校长家门口时,张校长正在二楼阳台上做晨练,远远就向他大声喊道:“耿鼎发啊!你的课讲得很生动、很好啊!他们都向我报告啦!马上给你安排工作!”
几天后,耿鼎发收到留校任教的通知,他知道专家们给他做了非常好的鉴定。
耿鼎发的名字一传十,十传百,在国防科技大学里不胫而走,人们开始关注耿鼎发的身世和经历,他是怎样一个人?他走过一条什么样的路?他为什么至今还穿着一身劳改服?
那么,就让笔者穿越百年时空,从头细说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