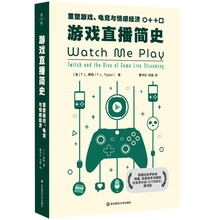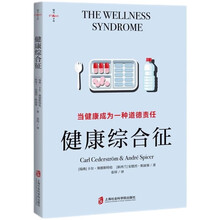或许有一个更为乐观的态度,对于现代性,或者说对于科学技术,不要一味地去拒绝,我们毕竟已经生活在一个无法回返到过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那种愤愤不平地从一种前现代想象来理解已经沦为科学技术话语霸权的世界已经于事无补。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者,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如何从这种话语霸权中找到破除其魔咒的隙缝,从中找到女性身体的未来之路。这条未来之路不能建立在一种与现实毫无关联的想象中,我们需要认可的是在这个已经被科学技术拆解了的世界上,或者说,倚靠着这个已经被科学技术介入了的身体,如何找到作为身体的活性本身(技术虽然中介了身体、扭曲了身体,但是毕竟没有消灭身体,身体在被技术所扭曲之后,仍然是作为活物而存在)在世存在(being-in-world)之路。
当娜·哈拉维(Dana Haraway)和维希留(Virilio)是这个希望的传播者,她们已经创建了一个新型的技术批判范式。哈拉维的“合成人”是一种新型的思维架构,她认为我们要摆脱那种纯然的身体谎言,而我们的身体早就是技术的合成物,如果是这样,我们只能在作为技术合成物的身体上来进一步反思身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抹除我们身体上的技术痕迹.而是去解决如何在同技术性话语的斗争中,争夺领导权(he-gemony)的问题。同样,法国社会思想家维希留也保留了与技术共生的未来希望,但是,我们不能在这个过程中沦为技术的奴仆,而是应在解放中成为一种技术方向的掌控者,维希留在其《解放的速度》中谈到:“逐渐地打破所有的对抗,所有的地区约束,迫使不光是地球地平线的时间延续与空间扩展的对立投降,而且还使我们的自然卫星的环地球高度的时间延续和空间扩展的对立投降,这就是人的科学和技术今后所要达到的目标。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