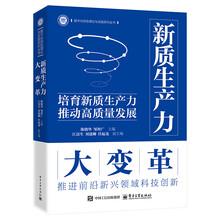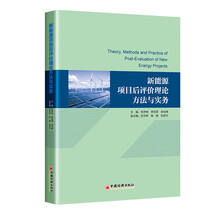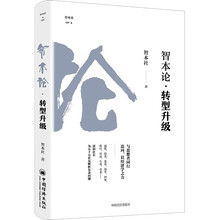顶层设计“总农会”
一个国家和政府对待农民的态度,反映了这个民族的良心。判断是否想真心解决“三农”问题有两个标准:一是能否真正分田给农户,使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二是敢不敢成立农会,使农民拥有政治参与权。
在我国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合法、正式的群体组织,例如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工商联”,文艺工作者有“文联”,学生有“学联”,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联”,也就是说在工农兵学商中,惟独全国最大、处于最弱势地位的农民却没有自己的全国性合法代言组织。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实在有悖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宗旨,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奇怪又很不合理的事情。
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说:“农业界别107名委员,居然没有一位是真正的农民代表,实在匪夷所思。”关于在全国政协中增加真正的农民委员,大会已经听到不止一次的呼吁。郑州市政协副主席、农业界别的委员舒安娜指出,全国政协农业界别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代表,十分不合理,这是对几亿农民公民权利的极大漠视。
一个国家和政府对待农民的态度,反映了这个民族的良心。判断是否想真心解决“三农”问题有两个标准:一是能否真正分田给农户,使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二是敢不敢成立农会,使农民拥有政治参与权。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三农”问题日益复杂化,从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考量,必须立即着手重建新时期农会组织,从国家制度层面实现对农民基本利益的维护。
现代与传统总是处于一种冲突状态,社会的进步总会表现出某种对传统的背离。但是传统也是一种资源。“农会”,在我国历史上早就出现过,并且曾以不同方式发挥过不同作用。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农会既可以成为破坏农村社会秩序的武器,又可以成为社会整合的工具。由于中国共产党曾经将成立农会作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工具,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共产党领导的农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关系进行了无情的冲击,并运用农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所以,农会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就仅仅是一个社会革命组织了。这是中国革命留给我们许多人的记忆。
正是由于这种记忆过于强大,我们却严重忽略了农会更多是一种社会整合组织的事实。新中国成立后,农会也曾在土地改革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传统农会实际上具有农村自组织的性质。农会的功能在今天的转型农村实践中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尤其在诸如自治性、公益性、群众性等功能特征上正是当今农村所欠缺的,也是广大农民的现实诉求。总体而言,传统农会的建设适应了我国当时的农业发展和农村政权建设的需要。
目前,农村、农民、农业问题错综复杂,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基层干部与民争利,官民矛盾日益尖锐。“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或者“农民收入”背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些农村的基层组织异化为盘剥农民的工具,广大农民不得不面对政府的与市场的双重体制“盘剥”,不仅要支付信息极不对称市场条件下的高额交易成本,还要为日益昂贵的政府管理成本买单。无论是黄宗羲定律还是帕金森定律,在涉农话题中说的无非是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全能政府”具有天然的增税倾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已经成为不少基层政府的“盘剥”的借口。政府的收费倾向,已经在经济伦理上决定了其与调整对象的矛盾地位。
就像中科院于建嵘研究员在题为《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的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乡镇,如果没有其他财政来源,那么乡镇政府只有从农民手里收钱,收上钱才有工资发,收不上钱就没有工资发,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成了'要和不给'的关系。某些乡镇将政府权力私有化,把权力变成掠夺社会财富的一种手段,成了'掠夺性政府',这才是认识三农问题的关键。”
目前许多乡政府一般都有100多个干部,多的达到200-300多人,一些乡镇的总人口才2万-3万人,差不多200多个农民就要养一个乡干部。在一些地方,如果你问农民如何评价乡镇干部工作时,农民会说,“他们就是'要钱要命'(收税和计划生育)。天天吃到这里,喝到那里,应付上级检查。平时连个人影儿也见不到,一收钱都来了。”
农民,在我国土地承包制的背景下也还具有天然的分散性,在政治与经济上均处于极为弱势群体的地位,是政府-市场-农民三角关系中最脆弱的一环。农民“讨价还价”的能力缺失,不仅突显“政府”与市场的霸权,更重要的是其直接后果使各方在“成本-收益”的博弈中偏离最佳均衡。
从现实情况开看,最昂贵的政府与最低效率产业的并存,其实是一体两面的问题。过多地责难地方政府或基层政府或许是不公平的:中央政府的投机性——事权的下放与财权的上收,正是默许地方暴敛预算外收入的关键原由之所在。
于建嵘研究员认为:“如果体制不改变,这种矛盾就不会根本解决。乡村干部迫于各种压力和出于自己的利益对农民暴力相向,让不少农民扬言与干部誓不两立,你死我活。这是他们双方的不幸,更是国家的不幸。”
于建嵘写到:“在湖南衡阳县,我看到了许多流泪的场面。农民在讲述他们受的冤屈时痛哭失声;减负上访代表为自己受到政府不公正对待和得到农民舍身营救与精心照顾而泪流满面;乡镇干部为因为领不到工资而不得不让独生女远行打工而哽咽难言。应该说,流泪的农民和流泪的乡镇干部,都是不合理的干部管理体制的受害者,而这不合理的体制又把两个受害者变成了冤家对头。”
面对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应该着手进行制度的顶层设计,允许农民成立农会,它可以是个社会整合组织,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农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团结全体农民,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扶贫帮困,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共同致富;维护社会稳定,清除社会黑恶势力。
也许有人会担心“成立农会,要是被坏人利用了怎么办?”这是一种不健康的阴暗心理,老是觉得自己比农民高明。现在的农民,已不是过去的农民,所谓的小农。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农民,了解农民,让农民自己讲话。近些年来,在关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调查报告中,几乎无例外地断言这些事件的组织者是“别有用心”。这种阴谋论的看法显然过于简单化,与事实不符,掩盖了事态的严重性和政治性,必将误导决策。
作为靠“农村包围城市”和工农联盟打天下获得江山的执政党,广大农民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过重大的历史贡献。特别是在解放60多年后的今天,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不平衡,有些地区可以说是面貌依旧,但广大农民仍然是艰辛地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农民,更没有理由害怕和防范农民。党和政府必须严加防范的是那些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封锁农民心声、民意,为追求个人升迁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地方党政领导;是那些推诿责任、不关心农民疾苦、麻木不仁的贪官污吏;是那些避重就轻、粉饰太平、无视农民抗争、甚至以阴谋论解释农民抗争、为一己私利不惜误国误民的所谓农民个别政策研究者。
应当客观地看到,经过60多年的共产党领导使广大农民对党中央有坚定的信任,多年的革命宣传已经使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民权利观念深入人心,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了农民一定的经济自主权,文化教育的发展使农民有了作出独立政治判断的能力,现代化的通讯和宣传为农民提供了获取党中央政策信息的渠道。这一切都决定了党和国家不可能再以命令主义的方式管理农民。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的生命线,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信任农民、承认和尊重农民作为政治人的公民权利、与广大农民开展协商对话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一些农民从对少数基层干部施政行为的怨恨,发展到对体制的不满情绪,应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政治信号。如果执政者不能清楚地理解这个信号,将产生的政治后果则是可以预测的。
从当前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来看,重建农会是维护农民权益,落实农民主人翁地位,提高农民素质的必然要求。农民问题是当下中国比较棘手又不得不解决的问题。通过政府一刀切地减轻农民的负担,实际上是政策在起直接作用,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上各种损害农民权益,剥夺农民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要解决三农问题,保障农民权益,最根本的是要发挥农民主体的作用,让农民自愿地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农会的建立正好能为农民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同时,农会组织在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信息传递、改变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别、推进新农村建设等方面都可以间接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国家应尽快制订《农会法》,给予法律方面的保障和规范,以便从国家制度层面实现对农民基本利益的维护。农会应当就像工会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维护工人利益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样,成为维护广大农民利益的群众团体。在农村依法建立农会,反映农民利益,保护农民利益,建立与政府的信息渠道,同时从事农村社区公益活动。
在组织形式上,农会的建设可遵循自下而上、先点后面的组建原则。在农民存在组织农会需求的地方,先在各个乡镇成立基层农民协会,各县成立统一的协调机构,以此类推逐级上至中央层面建立起一个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平行运行的机构——“中华全国总农会”。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