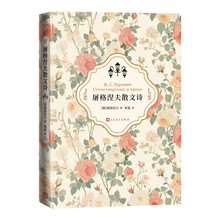《南部非洲文学中的跨国主义:现代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与印刷文化的不平等》:
然而,这点不仅对重申詹斯玛“道路”的多样性很重要,而且还对反省它们轨迹之间的差异很重要。除去常见的“精神分裂症”追索权,还有一个同样强烈的趋势,即通过“南非”的管理比喻来挽回詹斯玛抒情诗破碎的本质。早先,詹斯玛被冠之于“第一个完全整合的南非人”(罗伯茨1977),甚至“第一个南非人”(威廉1973)。泰斯托泰,尤其是阿什拉夫·贾马尔(2003)都反对这点,并坚持保持全面看待破碎或融合。但即使在他们的阅读中,承认破裂和援引南非作为詹斯玛诗歌的超验所指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的局面。碎片,是的,融合,是的,但是,在某种方式上,它最终重新提及了南非的现实,或者南非的象征,这个具体情况看情形而定。
这给詹斯玛诗歌的无界性帮了倒忙。的确,那些意味着“南非”的历史、地志和语言标记在他的书里很普遍。其中一个可能是指他混合南非、荷兰语和英语的方式,对南非空间的持久命名以及提及南非音乐家——这点我就不必预演了。但是,这个民族的名字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组织阅读詹斯玛的方法。大都市想象的跨国概念,就如我正这样使用的一样,暗示了意义的其他载体。当和鲁伊·诺夫里一起时,詹斯玛的大都市想象有助于探索位置和文本之间、地理和媒体之间的分离,有时还是作为莫桑比克诗人,在一个非常相似的互文空间里探索——证明他们提及了爵士音乐家,比如凯派·莫伊科特斯和索隆纽斯·蒙克,或者他们对葡语现代主义的使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