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与风格》试读
4姚、曾二氏选文分类之异同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下了一阵大雨之后,天气异常凉爽。振福、子寿、承良祖孙父子同坐在堂前的廊下。子寿今天接到承辉从重庆寄来的信,这封信还是国历六月底寄出的,在路上竟走了一个半月。信里谈到重庆虽曾遭轰炸,情形非常安谧,他在厂里,也能安心工作。他在技术工作之外,又被派充工人补习班的教师。他深刻地感到国文程度的不够应用,希望他的妹妹和弟弟,趁尹太先生在他们村子里,于暑期中努力自修国文。他又问他弟弟在简易师范毕业后,还是去服务,还是再去升学。如果不升学,与其到别处去,不如留在本村。一则爸爸和他都出门了,祖父年迈,弟弟在家,不但有些事可以代劳,而且老人家的心里也得到许多安慰;二则可以在课余自修国文,请尹太先生指教;三则弟弟既学师范,对于桑梓的教育,也应负相当的责任。又说他妹妹在初中肄业,离毕业只差了一年,因战事发生辍学,是很可惜的。如果她想复学,希望爸爸不要拦阻她。如果仍在本村小学帮忙,也希望能于课余自修国文。
振福的眼睛花了,晚上不能看信;子寿把信里的话一一讲给他听。讲完了,把这封信递给了承良。承良一面看,一面又讲给刚从里面出来的妈妈听。讲完了,把信交还子寿。振福忽然问道:“素秋呢?哪里去了?——今晚天凉,不如早些睡吧!”振福是睡在西边厢房里的;承良原陪着他祖父睡的,忙先去替他点上了那盏青油灯,又在床上点了一支葫芦牌蚊香。振福进去时,他早已都安排好了。陆氏也上楼去了。子寿见东边厢房里还点着灯,走过去一看,原来素秋一个人在那儿抄写她那篇《姚曾二氏选文分类之异同》,已全篇抄好,在那儿加标点了。子寿就在书桌旁坐下,把这篇文章拿起来看时,只见上面写着:
姚、曾二氏选文分类之异同
山素秋试作
我国文章的分类,有以章句组织的形式为标准的,如从前的骈文和散文,韵文和无韵文,现在的文言文和语体文;有以写作的方法为标准的,如现在一般人所主张的议论文、说明文、记叙文、描写文和抒情文。而古今讨论文章体裁的,远之如《文选》和《文心》,近之如姚姬传的《古文辞类纂》和曾涤生的《经史百家杂钞》,则多以应用的方面不同,来分别文章的体裁。《文选》《文心》二书,我未曾阅读过,无从说起;现在姑就姚曾二氏的选文分类,比较其同异如下:
(一)姚氏之《古文辞类纂》分文章为十三类,曰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哀祭原书遗漏了“哀祭”一类,这里“哀祭”系编者据第29页之引文所加。——编者注。、辞赋。曾氏之《经史百家杂钞》,则以著述、告语、记载三门为纲,十一类为目;著述门有论著、词赋、序跋三类,告语门有诏令、奏议、书牍、哀祭四类,记载门有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四类。——这诚如曾氏原序所说,“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了。
(二)以时代论,曾氏在姚氏之后,其文体分类之此有彼无者,可以说曾氏对姚氏的分类有所增删。赠序一类,姚氏所有,曾氏删之;叙记、典志二类,姚氏所无,曾氏增之;这是二氏见解最不同的地方。
(三)曾氏对于姚氏所分各类,不但有所增删,而且有所并合。如姚氏的箴铭、颂赞、辞赋三类,曾氏并合为词赋类;姚氏的传状、墓志二类,曾氏并合为传志类;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异点。
(四)此外,还有每类立名的略异和次序的不同。如姚曰论辨,曾曰论著;姚曰书说,曾曰书牍;姚曰辞赋,曾曰词赋;这是立名的微异。姚氏十三类,始于论辨,终于辞赋;曾氏十一类,始于论著,终于杂记。既如上述,二氏所列次序的不同,已可一望而知了。
子寿看罢道:“素秋,你的作文已有相当的进步了。这篇文章,词句上已没有什么大病,层次也很清楚。可是‘远之如《文选》和《文心》’这一句,还得加几个字,改作‘远之如萧统的《文选》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一则因为下句把姚、曾二人的姓字提出,上句也当把萧统和刘勰提出,方能相配;二则因为现在开明书店有一本读物,是夏丏尊、叶绍钧编著的,也叫作《文心》,不如把刘氏的书名全写出来。”素秋听了,立刻改好。子寿又道:“你这篇文章已把姚、曾二氏选文分类的不同都说明了,可是只述说他们的不同,而不曾推究他们的所以不同。曾氏对姚氏所分之类,有所增删并合,固已说出来了;何以要删,何以要增,何以要并合,却没有推究出来。你的研习,仍没有深入啊!”素秋听了道:“对呀!我这篇文章,只说了个表面。爸爸,应当怎样改呢?”子寿道:“不必改了。尹老师自然会替你详加批改的。今晚天气凉,我们上楼去睡吧!”父女俩上了楼,子寿又把承辉的信给素秋看。看完了信,各自就寝。
星期日,刚吃过早饭,素秋拿着她的作文,径到尹家来。黎明带着两个孩子出去散步了;秋氏婆媳在收拾厨房,洗衣服;莘耜一个人坐在书室里看书。素秋走上去,叫了声“太先生”,把那篇作文送了过去,并且说:“爸爸批评我只能举出姚、曾二氏分类不同之点,而不能推究其所以然;我很想自己改过,重做一篇,可是无从下手。所以今早特地过来请教。”莘耜叫她坐下,接过那篇文章来,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道:“你这篇作文,已做到文从字顺的地步了。你在初中,只肄业了两年,能做这样清顺的语体文,已很难得。第一段,你把那天在窗外听到我们所谈的意思简括地写了下来,做得很不错。《文心雕龙》简略作《文心》,本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现在有一种以故事体写国文学习方法的书,夏丏尊和叶绍钧作的,开明书店出版的,也叫作《文心》,所以还是用原名,不省略好。”素秋道:“爸爸也这样说,所以加了‘萧统的’、‘刘勰的’和‘雕龙’几个字。”莘耜道:“上句既已改了,那么下面‘《文选》《文心》二书’一句,也得加‘雕龙’二字了。”素秋笑道:“我怎么如此粗心?”
莘耜道:“你这篇文章,第一段算是总冒,以下分作平列的四节,是不是?”素秋道:“是的。”莘耜道:“下面这四节,形式上似乎可以平列,实际上却并不平列:因为(一)可以说又是一段总冒,(四)又似乎是补充和余波,和(二)(三)两节提出曾氏对姚氏的分类有所增删、有所并合的两大差异之点,是不相称的。而且第一节依次列举姚曾二氏所列之类,第四节又说到他们所列的次序不同,如再依次列举一遍则嫌重复,不列举又欠明显,所以末了几句,很难措辞了。——你在做第四节时,必已感到这种困难吧?”素秋道:“正是。太先生,您怎么猜得这样准?那么,怎样改呢?”莘耜笑道:“只要把两节并作一节,改成全篇的结论就是了。”素秋点点头。
莘耜又继续说道:“那四节里,(二)(三)两节,是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一段,可以说是全篇的中心。姚氏特立‘赠序’一类,曾氏为什么要删?姚氏没有‘叙记’‘典志’二类,曾氏为什么要增?姚氏分作‘箴铭’‘颂赞’‘辞赋’三类,‘传状’‘碑志’两类,曾氏为什么要合?你得就我在讲习会上所提示的几点,仔细去推究一番,这就是令尊所说的进而推求其所以然了!”素秋道:“我真是所谓‘学一隅不能以三隅反’了!好,我再去试试看,重做一篇吧!”莘耜道:“你肯如此努力,我觉得很满意。前星期所讲习的,你曾笔记下来吗?”素秋道:“也曾笔记,怕不完全。——不错,曾涤生那篇《书归震川文集后》,我还没有看过呢!”莘耜道:“你们爸爸的书箱里有《曾文正全集》,你可找了去细看一遍。”素秋照着莘耜的指点,在书箱里找到了《曾文正全集》。翻着了那篇书后,重新拿了她的作文,告辞回去了。
她走出门外,正碰着黎明领了两个孩子散步回来。黎明招呼道:“素秋妹,今天是星期日,坐坐再去吧!”素秋道:“我这篇习作,还得重做过,想趁星期例假把它写成,不能久坐了。”说罢,点点头,匆匆地走了。黎明走进书室,见了莘耜,问道:“爸爸,素秋妹第一次作文,你为什么要她重做?不把她习作的兴趣压了下去?”莘耜笑道:“这是她自己的意思。做好了,不怕重做的麻烦,这正是学不厌的精神!素秋这女孩子,很肯用心,比他的弟弟强得多了!”
素秋回到家里,一个人躲在厢房里,关起门来,先把那篇《书归震川文集后》仔细看了一遍,又把姚、曾二氏的序翻出来细细推究,《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二书,更是前翻到后,后翻到前,看个不了。她翻阅了许多时候,忽然如有所悟,拿起笔,在一张文稿纸上洋洋洒洒地写个不休。午饭的时间到了,振福和子寿父子在对酌。子寿谈起五天后就要和黎明动身到碧湖去。承良也从山石庵回来了,和他妈妈并肩坐下吃饭。振福道:“素秋呢?半天没有看见她了!”承良道:“她一定在尹家坐久了,也许在尹家吃午饭了。”子寿道:“她昨天已把那篇作文抄好了,一定到尹老师那里去交卷了。”振福道:“阿良,你吃了饭,去找找她吧!尹家如果没有吃中饭,不如叫她回来吃。”承良吃了饭,跳呀跳地去了。
子寿先吃完了,洗了脸,踱到厢房里去歇午觉。推进门去,见素秋一个人拿着一张稿子咿咿唔唔地在读,书桌上摊满了书。子寿笑道:“素秋,弟弟到尹家找你去了,你却一个人躲在这里做文章。——你的文章不是昨天已抄好了吗?”素秋道:“今天早晨,我把昨天做的那篇文章拿去请教太先生。他指出我许多缺点,并教给我改做的方法;我觉得昨天那一篇,做得太不成样子了,所以拿回来重做。我怕弟弟来打搅,所以把门关上了。我,八点多钟,就回来开始工作了。今天的中饭怎么提得这样早?已经吃好了吗?爸爸。”子寿笑道:“好孩子,你真是发愤忘食了!中饭我们大家都吃过了,快去吃了饭再来誊清吧!”素秋把稿子递给她爸爸,自去吃饭了。
素秋匆匆地吃了饭,又回厢房里去时,子寿已在那张客铺上睡着了,把素秋的那张稿子丢在里床。素秋把稿子轻轻地取了出来,重新关上门,把那篇文章抄好。看看壁上挂着的钟,已是两点多了;爸爸仍没有醒,便虚掩着厢房门,又到尹家去了。她一走进去,见莘耜躺在那大竹榻上,午睡未醒;黎明却坐在书桌旁写信。她搭讪着道:“太师母他们呢?弟弟妹妹呢?”黎明道:“都在后面厨房里吧!——妹妹的大作又做好了吗?让我先拜读一下!”素秋红着脸道:“第一次做得太不成样子了,第二次虽然重做了,还是个不成样子。我真是不可雕的朽木!”黎明道:“不要客气,爸爸在称赞妹妹不怕重做的麻烦,有学不厌的精神哩!”
“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好昼眠。”莘耜说了这几句话,从竹榻上坐了起来,向素秋道:“老夫懒散惯了,每天总得打个中觉;如在孔老夫子门下,不是和昼寝的宰予同成为不可圬的粪土之墙,不可雕的朽木了吗?”素秋想,刚才的话被太先生听到了,觉得脸上一阵热烘烘地,连脖子都红了,呆呆地站着。莘耜趿着一双木屐,站了起来。黎明忙到灶间里去舀一盆脸水来。莘耜揩了脸,在书位上坐下,叫素秋在对面的竹靠椅上坐了,问道:“你那篇文章,想已改造好了,拿来我看。”素秋只得递了过去。莘耜接过去,在书桌上摊开,看了一段,道:“这第一段,本来可以不必改。”再看下去,已和第一次的完全两样了。她这样写着:
曾氏《经史百家杂钞自序》首举姚氏所分之十三类,与彼所分之十一类,做一比较。赠序一类,姚氏所有,曾氏删之;叙记、典志二类,姚氏所无,曾氏增之;颂赞、箴铭二类,姚氏所分,曾氏附之词赋之下编;传状、碑志二类,亦姚氏所分,曾氏合之为传志一类:这些是姚、曾二氏选文分类最不相同之点,也是我们现在所当注意讨论之点。我们不但要知道它们的不同,并且应该推求它们的所以不同。
姚氏《古文辞类纂自序》,于赠序一类,引老子“君子赠人以言”的话,引颜渊、子路相违时各以言相赠处和梁王觞诸侯、鲁君择言而进的两个故事,以为“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并且说:“唐初赠人,始以序名,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可见姚氏对于赠序一种文体看得很重,尤其是韩昌黎的作品。曾氏则认为,古人赠别,系以诗歌;为赠别的许多诗歌作序,乃谓之“赠序”,所以赠序实在仍是序跋一体;即退一步说,也不过是序跋的变体而已。曾氏删去赠序一类,而于序跋类中选了四篇赠序——韩愈《赠郑尚书序》《送李愿归盘谷序》《送王秀才埙序》,欧阳修《送徐无党南归序》——便是这个缘故。至于那些本无赠别的诗歌,而空空洞洞送人一篇赠序的,以及做寿送寿序,有喜事送贺序,曾氏认为都是些骈拇枝指,可以不存。——这就是姚氏特立“赠序”类,而曾氏把它删去的理由吧!
姚氏之《古文辞类纂》,不采经传子史之文。故《自序》于论辨云“今悉以子家不录”,于序跋类云“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于奏议类云“其载《春秋内外传》者不录”。曾氏则以为言孝者不当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不可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故每类必以六经冠之,此犹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又曰:“余今所论次,采辑史传稍多。”且于论著,选庄、荀、韩非诸子之文,至十二篇之多。他的选文范围,较姚氏广大得多了。曾氏《自序》,于叙记类,举了许多经史上的例,而曰“后世古文,如《平淮西碑》是,然不多见”;于典志类,也举了许多经史上的例,又曰“后世古文,如《越州赵公救菑记》是,然不多见”。姚氏既不选经史,则后世古文家虽然间或有几篇可以归入叙记、典志二类的文章,也是寥寥可数,怎么能分立为两类呢?所以韩愈的《平淮西碑》只得选入“碑志”类去,曾巩的《越州赵公救菑记》只得选入“杂记”类去了。曾氏既选经史之文,则此二类文章可选者就多了,所以特地添立了这两类。——这就是姚氏无叙记、典志二类,而曾氏增设起来的理由吧!
姚氏于传状类外,别立碑志一类;《自序》中说:“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之金石。”故上编所录,如秦刻石诸文,以及班固《封燕然山铭》、元结《大唐中兴颂》、韩愈《平淮西碑》、苏轼《表忠观碑》诸文,都不是记个人之事的;而记个人的墓志之文则别录之为下编。曾氏则合传状、碑志二类为传志类,而释之曰“所以记人者”。故如韩愈《平淮西碑》,则列入叙记类;如韩愈《南海神庙碑》、苏轼《表忠观碑》之类,则列入杂记类。所以他并入传志类的,只是墓表、墓志之类的文章。姚氏认辞赋类为《风》《雅》之变体,义在托讽,大抵设辞无事实;故与自警自戒、辞质意深的箴铭类,源出《诗》《颂》、不施金石的颂赞类,不能混为一谈。曾氏则以为这两类也大都有韵,故以附于词赋之下编,而释之曰“著作之有韵者”。——这就是姚氏分列传状、碑志二类,箴铭、颂赞、辞赋三类,而曾氏把前二者合成传志类,后三者合成词赋类的理由吧!
总之,姚氏所列的十三类,曰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哀祭、辞赋。曾氏所列十一类,曰论著、词赋、序跋,为著述门;曰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为告语门;曰传志、叙记、典志、杂记,为记载门。虽除上文所说的增删分合的异点外,还有所列次序的不同,所用名称之略异(例如姚曰论辨,曾曰论著;姚曰书说,曾曰书牍;姚曰辞赋,曾曰词赋)。而其文章体类,则多数相同。这真如曾氏《自序》所说的“论次微有不同,大体不甚相远”了。
莘耜一口气把这篇文章看完,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来。这时候,恰巧子寿一脚跨进书房,莘耜竟站了起来,向子寿拱拱手道:“恭喜,恭喜!老弟可谓有女了!”素秋见她爸爸来了,刚从竹靠椅上站起,见莘耜这般夸奖她,倒有些害羞起来,低下头在一边站着。子寿笑道:“小女还肯用功,得老师指教,颇有斐然成章之望!”莘耜想拿那篇作文给子寿看时,已被黎明拿去,摊在那张方桌上,两夫妻在共同欣赏了。子寿晓得莘耜的用意,便道:“小女重新做过的那篇作文,我已把稿子看过了。阿良做的,有没有交上来呢?”莘耜道:“我限他们下星期日缴卷,素秋是缴的头卷,而且很有第一的希望哩!”子寿道:“素秋,你们一共有十多个同学,我想,一定有做得比你好的。即使这次你侥幸得了个第一,万万不可自满,下次仍当一样努力!”素秋连声应道:“是,是!”黎明看完了这篇作文,也觉得很满意。富氏携了素秋的手道:“好妹妹,倘使我也加入补习,要对你退避三舍了!你今天太劳苦了,我陪你玩玩去。我们屋后新种的两缸荷花,还开着呢!婆婆和我们两个孩子都在那里,我们同去散散吧!”说罢,两人径自去了。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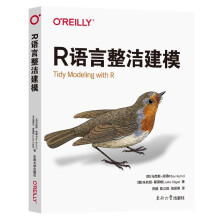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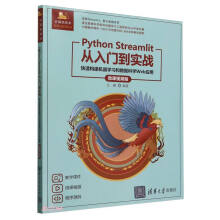


“这三本书都是用小说的体裁写的。书中对教师与学生之间融洽的关系有很好的描写,对书中人物的家庭生活和社交活动以及他们对社会、时局的议论也写得很真切。在周伯臧和尹莘耜的身上,可以看到作者蒋伯潜的影子。这些都是研究民国时期教育史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蒋绍愚(蔣祖怡之子、蒋伯潜之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