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与词》试读
21归途
寒假开始的一天,周叔文带了宗武、宗基和康宗诚,六点半钟就从涌金门直街周宅动身,到江干趁轮船回去。在轮船公司里,碰到了孔乐三和章载之等许多熟人。这天,因为杭州各校都放寒假,教师、学生,凡是严州以下杭州以上沿江一带地方的人,都是趁这路轮船的,早班船上非常拥挤。幸而杭江铁路已经通车,旧金华府属的人,都去趁火车了。那轮船公司又加开了一班,所以早班开出之后,第二班客人就少了许多。叔文的表哥王逖先是轮船公司的会计,劝他们不要性急,等下一班再去,他们就在公司的会客室里闲谈。载之因为梅东高桥离江干很远,没有吃早饭就动身了。乐三、宗诚等四个孩子归心如箭,有的不吃早饭,有的没有吃饱,这时候,都想趁空去买些点心吃。逖先看到这情形,便去叫了一大锅汤面来请他们吃。八点多了,他们便辞了逖先,同上轮船。逖先替他们设法包了一个小房舱,六个人一间,虽然并不宽敞,倒也觉得清静。船开了,不到二十分钟,便在闸口靠岸。这里也有许多客人上船。他们站在房舱门口的栏杆边,叔文眼快,早看见梅占先先生提着包裹阳伞,跨上船来,忙招呼他到房舱里坐。孩子们是好动的,都在房舱外面甲板上东立西望,房舱里只有梅先生和载之、叔文三人。
冬日的晴天是静穆的。江北岸的秦望山虽然一起一伏地带着奔腾之势向杭州而来,似乎被那座六和塔镇住了。钱塘江的怒气似乎也消沉了,黄澄澄地平静地躺在那里,只在轮船旁边激起了些浪花,两道白沫,斜向后去。水鸟们却没有理会这些,远远地贴着水缓缓飞翔。天上的白云一块一块地堆着,不动,也不散。帆船虽然扬着帆,看去似乎浮在水面上并没有动。孩子们站在甲板上,凭栏远眺,觉得一切都是静。只见北岸的山、田、秃了头的树、披着发的茅屋,迎着他们的轮船,慢慢走来。轮船机器的震动声似乎也并没有比他们自己恬静的心房搏动声来得更强烈。孔乐三道:“这真是所谓‘水送山迎,一川如画’了!——我今天才领略到动中之静的妙趣。”宗诚道:“这轮船好像是不动的。我巴不得立刻就到家哩!”宗基道:“我们在中埠上岸,乐三兄在富阳城上岸。第一个上岸的是你,何必这般性急呢?”
孩子们正在闲谈,忽然房舱里那三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宗武正回到房舱里去喝了茶出来,把嘴里含着的一口茶笑得从鼻子里喷出了。他们忙问他:“什么事这样好笑?”他道:“梅先生的家住在诸暨,本来是走杭江铁路的,因为接到他的堂房侄儿的一封信,邀他到富阳去,所以今天改趁轮船了。”宗诚道:“这有什么好笑呢?”宗武道:“你老是这般性急,我的话还没说完哩!——他老先生的字,不是叫占先吗?他侄儿给他的信,开首就称他‘先叔’……”宗诚插嘴道:“这并没有错呀!”宗武也不理他,继续说:“他的侄儿单名叫作梅贤,竟自称‘贤侄’。梅老先生说,现在的青年们不知道注意写信的称呼,所以闹出‘先叔’‘贤侄’的笑话来。”乐三、宗基也都笑了。
宗诚仍是听不懂。乐三道:“凡是比我们大的人,死了之后,称呼上都当加一‘先’字,如先严、先兄等;凡是比我们小的人,称呼他,都加一‘贤’字,以表客气,如贤弟、贤侄等。梅老先生的侄儿没有注意到这些字的用法,所以对活着的叔父称作‘先叔’,自称‘贤侄’,闹了个大笑话。”宗诚听了,才恍然大悟道:“我是个粗心的人,写起信来,也很容易闹这类笑话的。”
乐三道:“我们这几个人的名字,写信时也容易闹笑话的。譬如称我作‘三兄’,称你们几位中的一位作‘宗兄’或‘宗弟’,便闹笑话了。因为我是独子,并不是行三。宗兄、宗弟,同姓的人才有这类称呼。又如你们的大哥宗贻先生是名号一致的。写信给他,称作‘宗师’,也是不妥的。”宗诚道:“那么和我同姓的先生应当称‘宗师’了?”乐三道:“不是的。宗师是大众所共仰的大师,汉代称博士官为宗师,清代称学政为宗师。宗师的宗,和‘宗匠’的‘宗’字同义,而且你们的名字都是以‘宗’字为排行的。写信时,当采用你们名字的下一个不同的字,不当采取上一个相同的字原书为繁体字竖排版。若按本横排版,则“下”“上”二字在这里应分别理解为“右”“左”二字。——编者注。。又如许多人的字,上一个用‘伯’‘仲’‘叔’‘季’等字,这是表示他们弟兄辈中的行次的。通信时,不当称他们作伯兄、仲兄,或伯师、仲师。还有叫作‘子某’‘家某’的,叫作‘某轩’‘某斋’的,叫作‘某如’‘某甫’的,也不当称他们为‘子侄’‘家叔’‘轩伯’‘斋师’‘如兄’‘甫弟’的。”宗基道:“我又记起一件故事来了。我们的历史教员是卢姜斋先生。他说,暑假时接到许多学生的信,有称他‘斋师’的,有称他‘姜师’的,有称他‘卢师’的。称斋师固然不对,称姜师又和‘僵尸’的声音相近,称卢师又和‘螺蛳’的声音相近。他这姓字真太尴尬了。”宗武道:“写给先生的信的称呼倒不难,只要用‘夫子大人函丈’好了。”宗基道:“这是旧式的称呼,不如老老实实地称他先生,自称学生。”
叔文这时候正站在房舱门口听他们谈话,插嘴道:“先生和学生,是普泛的称呼。如其是亲受业的老师,不如称他‘夫子’,自称‘受业’好。不过‘夫子’这个名词,古代是妇女对她丈夫的称呼,例如《孟子》上说,女子出嫁时,母亲嘱咐她‘无违夫子’,便指她的丈夫而言。所以女学生称男教师作‘夫子’,似乎也有些不妥当。”宗诚道:“我们现在称教师都叫作‘先生’,怎么四舅舅说它太普泛?”叔文道:“‘先生’两字,在古代也不是专指教师的。如《论语》说的‘有酒食,先生馔。’马融注:‘先生,谓父兄。’《至元辨伪录》说的‘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言儒门第一。’注云:‘元人称道士为先生。’这两种意义,现在是不用的了。又如《战国策·卫策》说:‘乃见梧下先生。’注云:‘先生,长者有德之称。’现在对人通称的‘先生’,就是这一类。《礼记·曲礼》:‘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注云:‘先生,老人教学者。’今人称教师为先生,便是这一类。——最奇怪的,古人有单称‘先’的,也有单称‘生’的。如《汉书》说:‘夫叔孙先非不忠也。’叔孙先,就是叔孙先生。汉人称董仲舒为董生,贾谊为贾生,其实,就是董先生、贾先生。至于学生,本指在学校中肄业的人,《后汉书》上说,灵帝时,始置鸿都门学生。其后,后辈对前辈也自称学生,《留青日札》载宋陈省华见客,子尧叟等侍立,客不安。省华曰:‘学生列侍,常也。’明、清时,翰林见前辈,名帖上自称侍生,相见时自称学生,见《称谓录》。所以称人先生,自称学生,是一种普通后辈对前辈的称呼。”
乐三道:“今天在轮船上得到许多新知识,真是料想不到的。——叔文先生,那么,自称‘弟子’、‘门人’或‘门生’怎么样呢?”叔文道:“你是读过《论语》的。‘有酒食,先生馔’的上句,不是‘有事,弟子服其劳’吗?弟子本是对于父兄而言的。学生所以对师称弟子者,《仪礼·士相见礼》的疏里说:‘学生事师,有父子之恩,故称弟子。’至于门人,也可用以称学生,如《论语》说,‘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就指孔子的门下弟子。《战国策·齐策》所说孟尝君门人公孙戍,那是指孟尝君门下的食客的。门生和弟子似乎没有什么大分别。不过从前科举时代,及第的人对他的座主都称门生。五代时裴皞称他所举的进士桑维翰为门生,可见那时已有这种称呼了。”
这时,梅先生从房舱里走了出来,笑道:“你们在轮船里谈考据吗?——据我所知,门生和弟子是有分别的。《后汉书·贾逵传》说‘拜逵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郑玄传》说‘康成没,门生相与撰其与诸弟子问答之词,依《论语》作《郑志》’,都是弟子和门生分别说的。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后汉孔宙碑阴题名》云:‘其亲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今宙碑残缺……其称弟子者十人,门生者四十三人。’我们对亲授业的老师,还以自称弟子为妥当。而且门下客也可以称门生。从前官场中趋炎附势的人往往投靠在达官贵人门下,自称门生。而守门的人也可以称门人,如《榖梁传》说:‘吴子谒伐楚,至巢,入其门,门人射吴子。’便是一个实例。”叔文道:“经梅老先生一说,格外明白了。我们阅书不多,记性又坏,所以分别不出来了。”载之也出来笑道:“弟子这名称,也不见得高明吧?——元曲里不是有这样一句吗:‘恋着那送旧迎新泼弟子。’可见倡妓也可以称弟子了。”梅先生也笑道:“上海土话,妓女不也叫先生吗?——倡妓之所以称弟子,我想,是从戏子转来的。唐玄宗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这是戏子称弟子的起源。”载之道:“梅先生说得不错,宋朝程大昌《演繁露》里说宋人称女优为弟子,便是因此。到了元朝,便称妓女为弟子了。”
乐三道:“梅先生,章先生,我们对老师自称受业,大概是传授学业的意思了。这称呼有无所本?”载之道:“《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的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此‘受业’二字所本。业是大板。古代没有纸,以竹简、木板代纸用,所以有‘学业’‘受业’‘卒业’等语。”
宗武道:“章老师,我们写信给老师,为什么用‘函丈’二字?”载之道:“这是出于《礼记》的。《曲礼》云:‘席间函丈。’注云:‘函,犹容也。讲问宜相对容丈,足以指画也。’‘函丈’就是‘讲席’的意思。照古人写信的格式,开首往往说:‘某某再拜,奉书于某某师函丈。’现在把‘某某再拜,奉书于’几个字省去了,所以但称‘某某师函丈’,或‘夫子大人函丈’了。”
乐三道:“文言文的信,往往称‘大人’,怕也有限制的吧?”叔文道:“‘大人’,以用于尊长为宜,《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此以‘大人’称其父。《汉书·淮阳宪王传》:‘王遇大人益懈。’此以‘大人’称其母。又《疏广传》:‘受叩头曰,从大人议。’此以‘大人’称其叔。柳宗元谓刘禹锡母,‘无辞以白其大人’,此以‘大人’称其友之母。以此类推,则对尊长及业师当称‘大人’了。至于平辈,从前虽有‘仁兄大人’等称呼,我却认为不必如此客气。”
宗武又道:“我们写信给父母,称‘膝下’。这称呼有无所本?”梅先生道:“《孝经》说:‘故亲生之膝下。’注云:‘膝下,谓孩幼之时也。’‘膝下’二字本此。《唐书·高宗本纪》言太宗命高宗游观习射,高宗云‘愿得奉至尊,居膝下’,此对父称‘膝下’。《称谓录》引宋洪皓使金上母书云:‘皓远违膝下。’此对母称‘膝下’。所以这二字只限于对父母用。对其余的尊长,可称‘尊前’。”宗诚道:“那么‘阁下’‘足下’呢?”载之道:‘阁,亦作‘’,古时候,三公开阁。郡守比古之诸侯,也有阁。书函中不敢直指其人,故称‘阁下’以表敬意。这二字本专用于尊贵,后来朋友中也通用了。至于‘足下’,《异苑》以为起于春秋时晋文公,因功臣介之推返国后隐于绵山,文公求之,不出,乃烧其山。不料介之推竟抱树焚死。文公遂伐此木为屐,每值思念,必顿足曰:‘悲乎足下。’我想,这是附会的。下拜,则伏于足下,所以书函开首说再拜奉书于某某足下。这称呼,战国时苏代、乐毅给燕王的信上已用着它了。”
宗诚道:“我看见别人写信,也有用什么鉴,什么览的,这些又有什么讲究呢?”叔文道:“大概对比我大的或平辈,用‘鉴’;对比我小的,用‘览’。上面那一个字,也因人而异。如‘勋鉴’,用于做官的;‘道鉴’,用于有学问修养的;‘钧鉴’,用于掌权的;‘文览’,用于文人;‘英览’,用于年轻的人。还有,对于有学问的人,用‘史席’;对于教书的人,用‘讲席’;对于著述的人,用‘撰席’;对于有父母丧的人,用‘苫次’;对于有修养道德的人,又可用‘有道’;对于文人,用‘文几’;对于武人,用‘麾下’;对于女人,用‘妆右’。花样是很多的。写语体文的信,这些花样便都可省去。但是‘亲爱的’三字,用的时候也得小心。你们现在是男女同学的,男女同学之间通信,这三字便不能用了。”说得他们都大笑起来。
叔文又道:“文言文的信,末了还得请安祝好,这也有种种的花样。如对父母尊亲,多用‘金安’‘福安’;对老师,多用‘诲安’‘铎安’;对做官的人,多用‘勋安’‘勋祺’‘勋绥’;对直接的上司,多用‘钧安’;对有学问修养的人,多用‘道安’‘撰祺’‘著祺’;对做生意的人,多用‘筹安’;对行医的人,多用‘壶安’。而且下用‘安’字,则上云‘此请’;下用‘祺’字、‘绥’字,则上云‘此颂’。至于比对我们小的,也可以用‘此问近好’‘顺祝学行孟晋’等语。又有因时令而异的,如春曰春安,夏曰箑褀,秋曰秋绥,冬曰炉安;过年的时候曰年禧,曰新禧;当日可以接到的曰日社,曰刻安。还有信中指对方而言的字,都应当抬写,从另一行写起,或脱开一格写。指自己讲的,都应当偏写在右边。你们写语体文的信,写到末了,多用‘祝你好’‘祝你康健’一类的话,如其抬头写,便当从‘你’字起抬头,不当从‘祝’字起抬头了。”见本书按第207页、206页即先右后左之显示顺序排印的影印原书的文字和书信格式的样式。——编者注。
载之道:“写信闹笑话,不但在信中首尾的花样,信封外面的写法也得注意。我常常看见许多明信片,在收信人姓名之下写‘台启’,发信人姓名下写‘缄’字,便是笑话了。邮片并不用封套的,怎么说‘缄’呢?叫他怎样‘启’呢?信封上对收信人的称呼,是送信人对他的称呼,不是发信人对他的称呼;所以虽然是父亲写给儿子的信,老师写给学生的信,也都用‘先生’。但是如果这封信是交给熟人带交的,带信人是和收信人有关系的,应当写‘敬烦某某兄(此处用发信人对带信人的称呼)吉便交某某兄(此处用带信人对收信人的称呼)了。例如,我托宗诚带封信去给仲良先生,便当写‘敬烦宗诚弟吉便带呈尊大人台启’,下款写‘章某某拜托’。但也可以变化,如我托梅先生带一信给伯臧老师,也可以写‘敬烦梅老先生吉便带交周老师台启’,那是仍用发信人对收信人的称呼的。如果我们托人带信,写‘送呈某某老爷’,带信的人不是要生气了吗?”宗武道:“我看见托人带的信,写‘敬烦某某先生锦旋吉便饬交’,下款写‘拜干’的,是什么道理?”叔文道:“‘锦旋’是回去的意思,用的衣锦归故乡的典故;‘饬交’是命令仆役送去的意思,表示不敢劳他自己的驾;‘干’就是求,和‘拜托’一样的。”梅先生道:“大人、老爷、少爷、小姐、太太等,就是邮寄的信,也还是不用好。尤其是寄到乡间去的信,往往要从店家托人转递的。乡下人最讲平等,你要他们叫大人、老爷,他们是不愿意的。”
宗基道:“信封上的启,也有几种不同的写法吗?”载之道:“是的。如‘勋启’‘钧启’之类,往往用于官场;‘安启’,往往用于家信;普通则以用‘台启’二字为多。单用一个‘启’字也可以。”宗诚道:“还有用一个‘升’字的哩。”梅先生道:“这是老式的写法,最俗不过的。”宗武道:“信背后还有写‘金人’、‘如瓶’或‘露申’的,这是什么意思?”叔文道:“用‘金人’的,是用金人三缄其口的成语;用‘如瓶’的,是用守口如瓶的成语;都是和盖‘护封’图书一样。‘露申’是不封口的意思。”宗诚道:“信,怎么会不封口的?”叔文道 :“譬如我托你带一封信给你的爸爸,就不必封口了。”
他们谈得太起劲了,轮船经过东江嘴、闻家堰等埠,放了三次汽笛,盘了一次船,拢了雨次埠,他们都没有注意到。里山到了,八角山也绕过去了。汽笛一声,小驳船已慢慢地靠拢来。荼房来替宗诚拿东西,方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宗诚匆匆地告别,跟茶房下去。驳船上已有工人在接他。里山过去,就是富阳。叔文等也忙着付茶钱,整东西。不多时,已到富阳。梅先生和载之、乐三向他们作别,匆匆地上岸去了。再上去,就是中埠,他们也挤下驳船上岸。自有叔文家的工人接着。工人挑了行李,他们大小三人跟在后面,戴着和暖可爱的冬日正午的阳光,缓步归去。对面的苍山,一步步地迎面而来。走到山边,似乎路已穷了,转了一个弯,弯过山嘴去,又豁然开朗,另是一个田野,另见一座村落。村旁各有几株古老的乔木,一条小溪,溪上架着板桥。还有连绵数里的竹园,苍翠依然。人在竹荫中走,太阳从竹丛中射出来,洒到他们的身上、他们面前的石子路上。前面,有他们的故里,他们久别了的甜蜜的家。家,使他们把两只脚的辛苦都忘了。路走得越多,离家越近,脚上也似乎越有劲,越走得快。一进他们的村子,宗武和宗基竟拿出学校里赛跑的本领,拔步飞跑,赶过了挑担子的工人。走到家门口,只见他们白发苍苍的曾祖母正颤巍巍地倚门而望。他们俩赶上前叫了一声,扶着她,欢天喜地地走进他们所渴望的家里去。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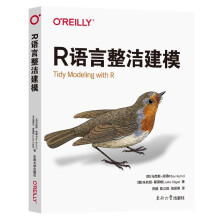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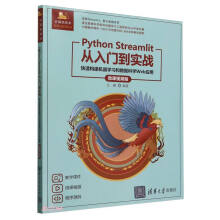


“这三本书都是用小说的体裁写的。书中对教师与学生之间融洽的关系有很好的描写,对书中人物的家庭生活和社交活动以及他们对社会、时局的议论也写得很真切。在周伯臧和尹莘耜的身上,可以看到作者蒋伯潜的影子。这些都是研究民国时期教育史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蒋绍愚(蔣祖怡之子、蒋伯潜之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