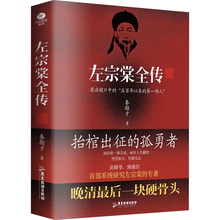《文化怪杰·李贽:告别中庸》:
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
明神宗朱翊钧统治下的万历三十年三月初。
农历三月(这年有闰二月)的北京,天气已不那么令人瑟缩。御河桥下的冰凌化了,棋盘街旁的杨柳青了。可是,天宇京畿的百官万民却一点生机也感觉不到,心头重压的冻云不开。胸中拥塞的冰块难融。
从庙堂大臣到市井小民,人们抹不去一个不忠不孝的念头,暗暗祈祷着,焦躁地盼望着:如果这位“酒色财气”四病缠身的皇上快快蹬腿,新皇登基照例来一番“与民更始”,大家兴许能喘一口气!本来,二月里已有确凿消息传遍皇城内外,皇帝早晚工夫就要死了。
二月十六日,朱翊钧忽然感至0病势沉重,将不得不撒手人间,急忙宣召诸大臣到仁德门候旨,并命首辅大学士沈一贯人启祥宫后殿西暖阁安排后事,说:“朕病甚,勉辅太子。这些年因为修建三大殿而征收矿税,本是权宜之计。现在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停勿征,所遣内监,都撤回京师。镇抚司和刑部关押的罪人可以开释;过去进谏得罪降谪的官员,都给他们复官吧。”说罢,便躺下来等着断气。这个晚上,内阁大学士们及三公九卿都非同寻常地在朝房守夜,以应大变。沈一贯按朱翊钧的意思拟好的圣旨,也已由太监送朱翊钧认可,交诸大臣传阅;大臣们如获至宝,期望即刻执行。
可是,第二天朱翊钧的病情好转,他反悔了,接连派出二十多批太监到内阁办事房索缴圣旨。沈一贯奏称:“臣等昨夜值宿朝房时已将谕旨传出,顷刻间已播扬四海,不宜出尔反尔。”但是,朱翊钧不管这些。司礼监太监田义侍候在旁,也力争道:“圣谕已颁行,皇上岂可反汗食言!”朱翊钧怒不可遏,拔刀要杀田义;田义不为所动,谏诤愈力。但首辅沈一贯害怕了,赶紧缴出前谕。过了两天,朱翊钧传谕内阁,说是前两天由于眩晕云云,一切“著照旧行”。
人们空喜欢了一场.说到矿税等等,是怎么回事呢?这位万历皇帝长于深宫,自幼挥霍成性。冲龄践位,前十年有张居正夹辅难称心愿;待到成年,世间已无张居正,便纵性肆欲,哪管它天塌地陷。万历二十四年起,便向全国各地派遣大量宦官充任矿监税使,搜刮钱财供他挥霍。这些狐假虎威的钦差,所到之处树旗建厂,广招流氓地痞为爪牙,专以敲诈勒索为能事,侵害的不止一个阶层。富户不是被诬以盗矿,就是良田美宅或祖茔先墓被指下有矿脉,逼其献款;不论有无矿藏或矿脉贫富,皆强逼富户为承包矿税的“矿头”,抓来贫户为矿役。地方官员也不在这帮皇使的眼里。州县芝麻官固然不敢阻挠中使,藩司巡院等方面大员也不敢稍加钤束。此外,还有查收商税、店税、鱼课、盐税的特使满天飞,举凡舟车庐舍、五谷六畜、农工官吏,无不是纳税的对象。“遂使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如此穷凶极恶的折腾,闹得正如刑部侍郎吕坤所形容的:“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矣。”万历二十六年,宦官陈增监山东矿税,凿山民夫多死,并逮及代纳税款稍缓的吏民。民众大哗。
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变,聚众三四千,驱逐税监马堂,毙其爪牙三十七人;沙市和黄州团风镇民众驱逐税监陈奉的徒党。
万历二十八年,京畿兵民苦于连年旱灾和矿税,起而为盗;浙人赵一平召集流民结党,拟举义兵造反。
万历二十九年,武昌民众聚集数万人围攻税监陈奉官舍,陈奉脱逃,投其党徒十六人于长江;苏州织工葛贤带领市民聚众包围税监衙门,乱石打死税使孙隆的参随黄建节,放火焚毁帮凶汤莘的住房,并捆住六七名爪牙扔进河流。
就在朱翊钧食言而肥的当日,江西又发生民变,景德镇民众烧毁了税使厂房,儒生们怒殴矿监潘相……尽管民怨鼎沸,报警的羽檄联翩而至,朱翊钧却无动于衷。坚持照既定方略办。
朝野士大夫忧心如焚。那些不怕丢官杀头的便前赴后继上疏劝谏。万历二十五年,吕坤上疏陈天下安危,请缓催科撤苛税,以收人心,防止人民“悉为寇仇”。
内阁首辅大学士沈一贯也与六部九卿大臣会疏纠劾宦官酿乱,毒害天下,请召还中使,罢除矿税。
但对这些意见,朱翊钧全当耳旁风。进言,或留中不发让它自生自灭,或下诏切责;行阻,轻则罚俸、撤职,重则打入锦衣卫北镇抚司监狱。诏狱中因建言及忤矿监税使的犯官,滞留未及时发遣的常有一二百名。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