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回避情感,自暴自弃,玛利亚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许这就是她拒绝见任何人的原因,即使现在,在医院病房这生命的最后一站。
她宁愿盯着玛丽娜送给她的百合花束,百合是她最喜欢的花。它们试图以面对一切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那种司空见惯的英雄般的姿势在盛有水的花瓶中生存。每一天,它们脆弱的闪着彩虹般色彩的花瓣都在凋谢,但仍带有谨慎的优雅。
玛利亚喜欢试想她也正在像那样死去:谨慎地,优雅地,无声地。但是,在床边坐着她的父亲,像石化的幽灵一样,日复一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除了看着她,提醒着她一切都不会那么容易,就这样死去并不会是一切的终结。只需轻轻推开门,你就能看到身穿警服的警察驻守在过道上监视着她的病房,你会理解过去数月发生的一切并不能轻易抹去,即使医生拔掉维系她生命的机器上的插头。
那天清晨,负责她案子的侦探一早就来了。他是一个友善的但在某种情况下坚强不屈的男人。如果他同情她的处境,他不会显露出来。玛利亚被怀疑牵涉几起谋杀案,帮助一个囚犯越狱,这就是侦探看她的样子:一个嫌疑人。
“我们的朋友与你联系上了吗?”他问她,带着恭敬的冷淡。马尔臣带来了当天的报纸,并把它们放在床头柜上。
玛利亚闭上了眼睛。
“他怎么会?”
警察抱臂倚靠在墙壁上,他的夹克没系扣子,他脸色苍白,显得很疲乏。
“因为这是他唯一能为你做的,考虑到你的处境。”
“我的处境不会变了,侦探先生。我猜测塞萨尔知道这一点。只有傻瓜才会不惜一切代价看望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
马尔臣摇了摇头,凝视着那个严肃、高深莫测的坐在窗边的老男人。
“你父亲今天怎样?”
玛利亚耸耸肩膀,一块石头的感觉是无从知晓的。
“他一直不说话,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有时我认为他的眼睛正在枯竭,他就这样一直在那儿盯着我。”
警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研究着她,这个女人曾经一定很有吸引力,在她的头发被剃掉之前,在一切束缚降临、在她依附于充满亮灯和体征数据图的监测仪器之前。与她相处让马尔臣感觉自己像一个矿工,用尽一切力气试图劈开一堵石墙,但仍然只是勉强削去些许碎屑。
“好吧,随便你……但是口供呢?你的父亲将要做供述吗?”
玛利亚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她父亲身上。这个老男人现在正看向窗外,街上的亮光照亮了他苍老面庞的一部分。他的下嘴唇下垂着,顺流而下的一小串口水弄脏了他的衬衫。玛利亚感受到一种愤怒和同情的混合情感。为什么他执意以这种无声的斥责方式待在她的身边?
“我的父亲帮不了你,侦探。他几乎再也认不出任何人。”
“那你呢?你能告诉我你所知道的吗?”
“当然,但是这并不容易。我需要理清思路。”玛利亚?本戈切亚向侦探保证她会简练叙述,坚持事实,不捏造,不回避,避免糟糕的报纸连载小说中的那种无用修饰。
开始她认为这会很简单,她想象这只是一个备忘录,而那是她的专长:简明扼要陈述事实;剩下的对她毫无意义。然而,结果证明远比她想象的复杂。她正在谈论她的生活,她自己的生活,所以她不由自主地主观起来,模糊了事实与印象、渴望与现实。最后,本该是一篇简单的诊断性短文变成了精神科医生的诊察台。
“不着急,慢慢来。”警察说着,留意到她床头柜上的笔记本,纸页的上方有一些字迹,“我得走了,但我会回来看你的。”
玛利亚在他离开后拿起笔记本,努力忽略父亲幽灵般的存在。她开始以一种假装的静谧神态书写,她发觉自己多次思索生命的意义和死亡的神秘。当她意识到这一点时,随即微微羞愧地画掉了那些段落。让她尴尬的并不是警察将要读到的内容,因为那些在那个节点无关紧要;让她感到羞愧的是那个纯粹的事实,她身上竟然发生这种事。
“那是我现在的样子吗?那是直到几周前我还感觉可以胜任的样子吗?”
然后她抛弃了猜想的世界回归了实际,回到了现实。如果她想写完过去数月发生的事情就不得不在生命结束之前迫使自己遵守纪律。他们会再次为她的肿瘤做手术,但是从医生的表情推测,她知道他们已经放弃了希望。她的疾病在某些方面是通往过去的一条路,快速倒回她的成年和童年。她将会无能为力地结束她的日子,不仅不会书写,甚至讲不出自己的名字;她将会像孩子一样结巴着表述不清;她将会带着纸尿片睡觉以防弄脏床单。她看向坐在轮椅上颤抖着的老男人。
“看来最后我们终将相互理解,爸爸。”她自言自语,带着一种只能伤害到自己的讽刺语气。她想知道,是否无罪会伴随那个不可避免的遗忘而至。她可以想象的最糟的事情莫过于变成她的父亲:她的思想仍然是一个女人的,却困在了一个孩子的身躯中。
她很惊奇她那么容易就忘掉了花那么长时间学到的一切,把她带到生命中我们称之为成年的那个节点的一切:敏感,安定,结婚,负责任,有孩子。玛利亚一个都不是,她从未有过,她从未成为她期望的那种女人。这与她的病无关,更多的是某些遗传的东西。她三十五岁,一个有名望的律师,离异,无子,与另一个女人玛丽娜一同生活。玛丽娜也已经离开她了,因为对玛利亚不能真正爱任何人这个事实感到绝望。现在她正面临一场谋杀数人的审判,一场永远不会举行的审判,因为上帝,或者掌控命运的任何什么人,已经制定下了一个不能上诉的有罪判决。
基本上,那些就是可能让人感兴趣的所有生平资料。她的资料可以填满数页:她的社会保险号,她的驾驶证号,身份证号,电话,出生日期,学历,硕士学位,从事的工作,甚至是她最喜欢的颜色,幸运数字,胸围和鞋码,甚至可以包括护照照片,从照片上你可从个人角度认定她是美丽还是丑陋,头发染的金色还是自然色,是否体重过轻,是否矮小等。那些有眼光的人,或是浪漫主义者,会说她有一种忧郁的气质,他们可以毫无根据地推断,她的爱情生活曾是一场灾难……但是最后他们仍然对她一无所知。
她依靠助步车的帮助走去浴室。她打开灯,日光灯带来长久不确定的闪烁光亮,瞬间显示出她的边缘,随即将她的后背投进黑暗之中。短暂的光辉让她瞥见了一个赤裸身体的轮廓,以及一张充满令人不安的阴影的面庞。
她很害怕她身体中的那个陌生人,她几乎不认识她。一个苍白的身体,松垮的肌肉,脆弱的四肢,以及一个凸显出血管的胸口,血管都会聚到下垂的乳头处。她的腋下和阴部鲜有毛发。她的性欲苍白、无力。她的手指像水母冲刷一块岩石一样触摸着她的大腿,她感觉不到它们。而她的脸……上帝啊,她的脸怎么了?她的颧骨像尖尖的小丘一样突出在她紧绷的面颊上;她的皮肤像贫瘠的田地一样开裂,充满黑暗的憔悴的沟壑;她的鹰钩鼻子挺立,鼻孔干涩。她的一头漂亮长发没留下任何痕迹。光秃秃的头骨的右半边有十四针的缝针痕迹。而她的眼睛是最糟的。
“它们在哪里?它们在看什么?它们看见了什么?”晦暗发蓝的眼袋及下垂的眼睑,无限的筋疲力尽,完全的魂不守舍,这是某个已经放弃了一切希望的人的双眼,某个走向生命尽头的人的双眼,行尸走肉的双眼。但是不管怎样,在衰老和疾病之下,她仍然是她。她仍然能认出她自己。她强挤出一丝微笑,几乎是啜泣的一个微笑,一个无能的姿态,天真的姿态。
她并没有死,她仍是剩下的那个她的主人。
“这仍然是我,玛利亚,我三十五岁。”她大声说道,好像是想吓走从另一边探出来的那个幽灵的踌躇阴影。很少有人能经受得住他们自己的镜中影像,因为在镜前总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你看着你看见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挖掘得稍微深一些,超越其表面,你就会被一种不适的感觉压制,那是个正在蛮横无理地注视着你的镜像。你问自己你是谁,就好像那个镜像是个陌生人一样。
她趿拉着拖鞋回到床上。她的身体很沉重,尽管它漂浮在白色的病号服之中。她打开电视,新闻使她困惑。它们是残酷的,好像没有人可以阻止那些事件接连不断地揭开,好像那些事件本身在主演它们的那些演员之上。记者皮拉尔?厄尔班正在国会进行报道,那是二月份政变的发生地。那里有特赫罗、米兰斯?德尔?博什、阿尔马达,以及其他共谋者的照片,所有人都傲慢自大、自恋。
普布里奥不在他们之中,他的照片和名字都不在,对莫拉家族也同样只字未提。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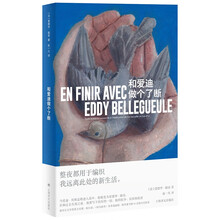
——《时间裁缝师》作者杜埃尼亚斯
★精巧完美地融悬念叙事和文学描述于一炉……精妙绝伦的创作……一部引人入胜的经典作品。
——《柯克斯评论》星号书评
★一本充满爱欲纠葛、背叛与权谋的迷人小说,书中融合了悬疑、推理、心理分析、政治、家族秘密和历史小说等元素,峰回路转的剧情和错综复杂的架构,让人一读便难以罢手。
——《图书馆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