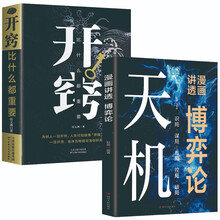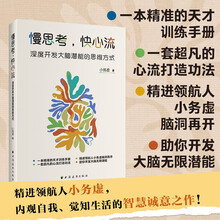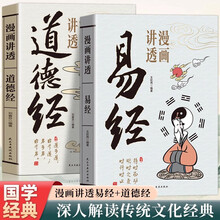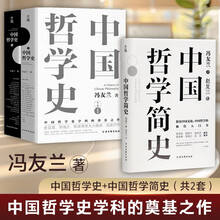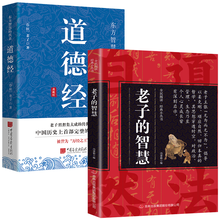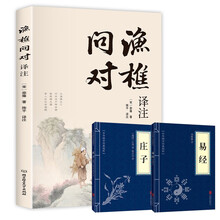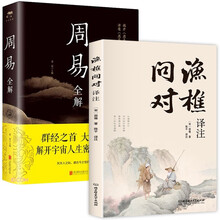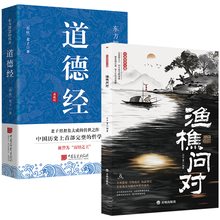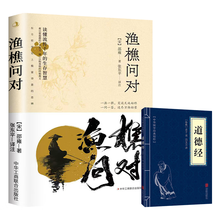《切磋五集:四川大学哲学系儒家哲学合集》:
梁:下面由回應人發言。
張帆:我先大概闡釋一下,在讀高老師這篇文章的時候所看到的一些東西,之後是我提出的問題。初見高老師文章時,題目中的“貫通”二字很吸引我的注意,我會想知道老師在文章中,會如何述說天命之仁貫通天人,我會把重點放在此處。高老師在文章的第一部分講到天人貫通,並且直接講到義理之仁落實到人心的貫通,以及第二部分所講的,就人來說,仁是貫通於修齊治平當中,無一不在的。在講到勇、能、忠、清這些品質,它們若沒有仁作用其中的話,也是有可能成為惡的,這句話對我來說比較有觸動感。關於“貫通”的部分,老師還會在後面提及,仁亦是貫通于天地萬物之中的。至此老師的行文立下了一個主線,即是由天文到人文以仁一以貫之。題目之中還有一個“讓”字也很關鍵。如何講到這個“讓”呢?這個地方就涉及到第二部分的後半截,將人與物相區別。在人文回溯於天文,由人文走向天文的這樣一個階梯上,人相對於物來說是具有更高起點的,但這衹是人之為人而已,要想從人文回溯到天文,還有一大段的距離。那如何縮短這個距離?第一步就是人對自己的內心之德有一個自覺,即高老師在文章當中所提到的,“要人先自覺人之所以成為人之內心之德,使人自身先堪為禮樂之儀文所依之質地”。除此自覺之外,還需要老師在內容提要中所說的“以仁義為核心、《四書》為根基、《六經》為擴充的人文教育的完備體系”,“讓”字在此將這樣一個完備的人文教育體系的必要性體現了出來。至此,“讓”與之前所談及的“貫通”形成了一個由天文到人文,再由人文到天文的完整表述。我的問題是:高老師在文章中會有將“仁”與“性”并談的傾向,那麼我對於二者的區分就會有一定的疑惑。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問題,不一定是完全針對高老師,您的文章會從以儒家為衡準的現代人文學之批判著眼,那麼儒化現代人文學到底是怎樣一個概念,什麼叫儒化現代人文學?怎樣實現儒化現代人文學?這中間可能會面臨各種現代性的問題,它會如何應對?這是我的兩個問題。
柯勝:我還剩多少時間?那我衹能揀重要的向高老師請教了。因為整個文章從“天文”“人文”然後直接進入到“天道”和“人道”,這個轉折是在第二頁第一段開始的那個地方,這個轉折比較快了一些,所以我就在這一點上花了一些時間來琢磨。高老師文中的論述“若說人文源於天文,而天文即帛書《要》所謂天道與地道,統言之即天道;人文即人道”,這個地方就直接用“天道”對應上了“天文”,用“人道”對應上了“人文”。高老師剛才說他這篇文章主要從脈絡上一氣呵成,其中精微之處就有些費我的思慮。我不知道現在可不可以說把這個理解通了,因為這個地方的“人文”和後面的一個“人之文”是否是同一個東西,這是我在閱讀這篇文章中間比較注重的問題。我現在提一下自己對此的理解,以請高老師來指正。從上一次廖恒老師對“文”字的解釋上,我們可以看出,“文”字本身指的是一種相錯,如金屬的紋路,一種交叉錯雜。從這種相錯中,可以體會出天之道表現在陰陽般的類似。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