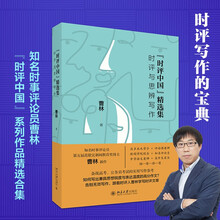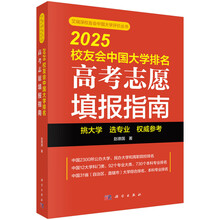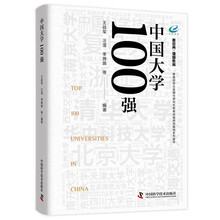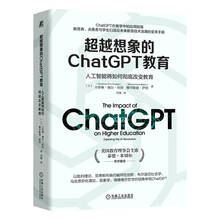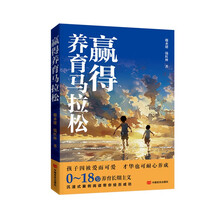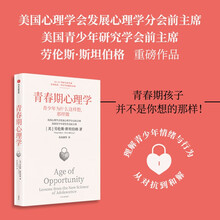《课程政策与课程史研究丛书 颠覆与重构:现代学校德育课程变革》:
在孔子看来,“仁”有两层含义:一是克己;二是爱人。所谓“克己”,就是以“礼”约身,一切行为都遵守“礼”的法则,克制不合礼义的欲望。由此孔子提出了“义利之辨”的道德评价标准。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义”和“利”的不同追求,既体现了君子和小人的道德价值取向的差别,也反映了君子和小人追求的不同学习结果。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仁”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不忍之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对于同类生命的基本的同情和关怀。缺少对生命和人性的同情与关怀,就叫做“麻木不仁”。儒家认为“仁”是为人的根本,是人的精神家园,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人之安宅”。提倡“仁”的道德,就是要以人为本,把人当作人来对待,就是在确认自己是人的同时也承认他人是人,因为人与人在天命之性和生命价值上是平等的。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态度友好相待,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救世”立场互相提携。
“仁”的精神也就是人性与人道的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儒家以“仁”为道德之源,这对当代社会道德文明建设有两点重要的启示:其一是说明就人的本质的、永恒的存在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谐、合作,较之于人与人之间有时难以避免的竞争来说,是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方面,具有更高的价值。其二是说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道与人性的价值,都是终极的最高的价值。任何科学技术的发明与运用,政治制度的设计与经济体制的建构与实施,都不能违背人道与人性的原则,都不能以牺牲人的性命为代价,否则就是不道德的。因此,科学技术与竞争机制只有更好地为人道与人性的根本目的服务才符合“仁”的价值原则和道德精神。正因如此,通过“内求诸己”达至仁的境界是个人修身或学习的主要途径。
儒家一致认为,“修身”与“养性”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儒家的“修身”标准,主要是忠恕之道和三纲五常,实质上是脱离社会实践的修身原则。“养性”主要是从个人修养即私德的角度思考的。比如儒家的“温良恭俭让”、“忠信笃敬”、“寡尤寡悔”、“刚毅木讷”、“存心养性”、“慎独”、“自戒”、“知耻”、“克己”、“反身”、“强恕”等等,都是对私德的注解。这些私德主要是用来调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关系,即“五伦”。其中君臣伦理不等于国家伦理,朋友伦理不等于社会伦理,这样,社会伦理、国家伦理就被忽视了,剩下的父子、兄弟和夫妇之间的关系全部属于家庭伦理调节的范畴。由此可见,中国的传统道德历来重私德修养轻公德意识。
儒家认为修身的过程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其中格物致知是修身之手段,诚意正心是修身的本质,修身的目的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性的本质是“正心”,其宏大的人生目标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可见,“内圣外王”是儒家修身思想的最高境界。无以“正心”,难以达至“内圣”,则无以“外王”的可能;同时,“外王”的威信和众服正是长期“正心”修身的结果。虽然这种个人私德修养看上去似乎与利群、利国或利天下的公德接近,但是在家姓王朝中,所谓的“国”就是“朝廷”,忠于国,就是忠于朝廷和君王,这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就变成了君臣的关系,使得天下也成为一个十分空泛和空幻的概念想象。于是,在公德与私德的权衡与博弈中,如何消解以讲求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和回报的传统私德与主张权利与义务制衡、弘扬公共精神的现代社会公德之间的紧张成为晚清知识分子的道德叩问、知识探求和精神焦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