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象灰色
当我在巴士上手拿麦克风,向来自德语地区的游客介绍佛罗伦萨的时候,人们会以为我是一个攻读罗曼语语言文学的大学生,只是想给自己赚些零花钱而已。他们觉得我讨人喜欢。有一对老夫妇看着我的脸说,如果有我这样的女孩做他们的女儿该多好。他们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很有可能表里不一。
游客们通常在这里开始他们的托斯卡纳之旅,对末几位数为零的意大利大面额货币里拉无法马上换算清楚,人们可能因此误以为他们会给出很高的小费,可遗憾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为了让他们至少还能够想到我的费用问题,我在环城旅行快要结束时,会提醒我那些被保护人谨防被抢被盗事件的发生,并以一位来自莱比锡的退休老妇的故事为例,让他们引以为戒。她的所有亲戚为了了却她多年来的心愿,在她七十岁生日之际赠送给她一次意大利欢乐游。但就在几天前她被洗劫一空,身无分文。我只好拿上一只香烟盒让人依次传递,给这位退休老妇募捐。绝大多数人都会慷慨解囊,因为左邻右座都在眼睁睁地看着呢。
旅行结束,我和汽车司机塞萨尔私吞捐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算是给他的封口费,让他保持沉默,别到旅游公司那里告发我。
塞萨尔背地里说我有恃无恐。当然,我之所以拥有这样的坏毛病,起源于我的童年时代。我的童年是一个心情忧郁、沉闷失落的时期,仿佛灰色的铅块压在心头。直至认识柯内丽娅之后,我的情况才慢慢好转,装病请假的坏分子这样的字眼也和我无缘了。
小时候我从未得到过自己想要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事到如今我才明白,我想要的原来就是温暖和快乐。我和每个人一样,希望被爱,希望自己有一点儿幽默感和冒险意识。我喜欢风趣、机灵的朋友,他们还不能缺乏一些教养。这一切在我家里是没有的。痛苦是我的基本状态。后来我干脆一股脑儿地将自己缺乏的一切据为己有。或许偶尔地,为了达到目的,我可以不择手段。
我的母亲要么寡言少语,要么恶语相加。无疑这也是我没完没了怒不可遏的一个原因,有时候还得发泄个痛快才行。
年幼时,如果我在午饭期间大胆说起一个幼稚或者冲动的消息,讨厌的哥哥和母亲彼此就会在瞬息之间交换会意的眼神,我无法对他们的眼神视而不见。那种眼神告诉我,他们经常谈论我,谈论我的天真单纯,他们以后还会乐此不疲地做同样的事。然后我就习惯于沉默无言好几周。我的怒火一旦压抑久了,人也变得诡计多端起来。
我十岁的时候,哥哥卡罗十四岁,我当时拿走了他悄悄买来的香烟,扔进上学路上的垃圾桶里。他认为我又是胆小鬼又是笨蛋,再说也知道我无所谓他抽不抽烟,因此从没有怀疑过我。他认为是母亲识破了他的诡计,私下里担心他弄垮自己的身体才这么做的。
逐渐地,我变成了小偷。人们从没有指控过我,因为被偷窃者都认为小偷想要他的东西。一个小女孩拿香烟干嘛呢?既然每个人都能立马闻到那种昂贵的香水芳香,那么她阿姨的香水对她又有什么用呢?我当时偷过大门钥匙、证件和老师的眼镜,将它们随便一扔了事。“为艺术而艺术”嘛。直到多年以后,我才会把偷来的物品保存起来。
假如父亲没有过早离开我,或许我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可以确切地说,他是离开我而不是离开我们这个家,我有这种感觉。之前我一直是他的公主,事发那年我才七岁。
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出喜剧一样,我们家有两对情侣:一对是地位高贵的主人——国王和公主,另一对是仆人——母亲和哥哥。国王叫我“玛雅公主”,他有个年历,上面是一幅西班牙宫女图,宫女们在伺候一位公主。虽说我那一头浅棕色稀发完全不同于那位公主的金发,但父亲坚持说,我和她长得很像。我喜欢这幅画。
前不久,我买了这幅画的复制品,挂在我的镜子旁边。画作中央站着那位迷人可爱的玛格丽特公主。她那张一本正经的脸蛋,被丝绸般柔软的头发围绕着。和成年妇女一样,她穿着一条硬邦邦的有衬架支撑的女裙,或许被迫保持着伸展四肢的姿态。玛格丽特似乎知道得一清二楚:一切都在围绕她转动。画的左侧,那位画家在以工作的姿势为自己画像,那是一个英俊而自信的男子。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画的右侧,站着一个女侏儒,忧郁而浮肿的面孔紧绷着。在她旁边,站着一个小孩,或许也是一个侏儒,企图用自己的小脚吓跑那只正在打盹的小狗,可是并没有如愿。在这张美丽绝伦的油画上,小狗表现出宁静和尊严。画上还可以看到其他人物,同样具有历史意义,但我对他们并不感兴趣。背景中的颜色呈灰色、淡绿色、红褐色。在图画的前景中,占据上风的是一只轻巧的象牙,还有一些精致的丁香红圆点。所有的光线似乎都聚焦到了公主身上。
父亲和那幅油画背景里的那名男子一样是画家,很久以前他给自己的公主画过画。他离开我时,创作的所有画作消失得无影无踪。西班牙公主那张画我是在抽屉柜下面找到的,当时已经皱皱巴巴的有破损了,我把它藏在迪尔克世界地图册里,后来被哥哥撕成碎片。
哥哥从未做过王子,而妹妹一直在抢他的风头,想必他为此受尽煎熬,于是想尽办法伺机报复。
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必须在饭前将餐具摆好。有一次,我跌跌撞撞地绊倒在一条地毯上,三只杯子、茶托和盘子被打碎了。“就像是瓷器商店里的大象,”母亲说道。“公主变成了母象,”卡罗说。母亲顺势笑了起来。“真是幸灾乐祸,不过说得对。”
此刻我成了母象。我哥哥使用这个名字长达数年之久。母亲虽然在不得已时才使用“玛雅”称呼我,但我进门时偶尔会听到她跟卡罗说:“母象要进来了。”
灰姑娘变成王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我的梦想就是成为名人,世界就在我的象脚下。十五岁时我发誓成为一名歌唱家,成为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斯第二。从那时开始,母亲和卡罗必须始终忍受《卡门》里的同一首咏叹调。我唱起歌来声音高亢,热情活泼。我的嗓音没有天赋,我也并不是特别具有音乐才华,可我的脾气很可能会发作。“她又在唱大象歌了,”母亲总是这么说。
有一个女同学有次听到我哥哥这么称呼过我。第二天,我在班上受到震耳欲聋般吼叫的问候。即便在学校里,我也成了大象这样的厚皮动物。
我长得像一头大象吗?我的尺寸、重量和人的标准相符,我的脚细小,我的鼻子完全不像象鼻,我走起路来既没有不相协调的地方,也没有笨手笨脚的时候。唯有我的耳朵并没有完全符合标准,尽管大小位居平均水准,却是一对招风耳,凸出于滑爽的头发之上。在我长到足够大之前,母亲习惯在我洗完头之后给我残酷无情地梳头,梳子便会停留在耳朵上,然后顺流而下。我长大之后,女理发师给我理发,同样的厄运依然会发生在我身上。碰到这样的情况,一想起我的母亲,我立马会起一身的鸡皮疙瘩,她在做其他事情时也常常令我产生身体的不适感:她的手指尖在我肩胛骨之间游移,双手交叉发出响亮的咔嚓声,擦窗时制造出毛骨悚然的尖锐刺耳的声音。
母亲担心我这种大象的品性也会从外形上暴露出来。我需要一件冬大衣,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件火红色大衣。据说家里已经没有余钱购置一件新大衣了。母亲请人用家里祖传下来的一件驼毛披风缝制成一件灰色披肩,事实上穿在身上使我感觉稍稍有些臃肿。我的鞋子也是灰色的,而且选择了一双尺寸大一码的鞋,这样就可以和披肩相配了,还可以留到下一年继续穿。
一个女教师听到有同学叫我“大象”的雅号,看到我悲伤至极、脚步蹒跚地走过来,便安慰我道:“玛雅?韦斯特曼,这种玩笑你慢慢就会适应的!另外,你可不要低估大象的力量,做一个强壮女人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
可我不希望自己成为强壮女人。我恋爱了,在我的脑海里只给爱情留下了位置。当然这已经不是头一次恋爱。就我的记忆所及,这事开始得很早,而我的第一个恋爱对象就是我的父亲。他离开我时,我坚持为他“服丧”一年。
最近,我以前的地理老师携妻子一起乘坐我带团的旅游大巴。那是复活节假期,他把这一假期变成了一次小小的意大利教育之旅。我高中毕业已有三年,彼此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我们马上认出了对方,相互热情地问候致意,最后在友好的祝福声中话别。他没料到,有好几个月他成了我幻想的中心。唯有贝克先生和歌剧明星的职业梦想,才避免使我陷入抑郁之中,我的求学时代和我的家庭生活就是如此灰暗而阴森。在这两个未来的梦想中,第一个不现实,另一个更不现实。顺便说一句,我还拥有我这位老师的一把梳子,这是我唯一一次去他家做客时作为纪念品带走的。
他当时三十岁左右,我早就担心自己是否有恋母情结。一夜之间,我成了地理明星。
地理课上常常要让人思考历史、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是令贝克先生恼火的是,大部分学生只是在看报纸上的体育消息和电影广告,却恰恰忽视了那些政治和经济版面。每天早上我都要和卡罗发生争执,他毫无顾忌地抢走我的日报。我们在课堂上谈论乍得、尼日尔和苏丹的旱灾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时,我是班上唯一举手的学生。还没等到贝克先生叫我回答问题,有人吼叫道:“怪不得她知道答案,非洲本来就是她的家乡呀!”
“你是在非洲出生的吗?”贝克先生饶有兴趣地问道,他确是事先毫无所知。在同学们的大声嚷嚷中,我就像一只真正的大象,一头冲出教室,不小心撞倒了两只凳子。在健身房前面,我躺倒在一道矮墙上,用光了身上的纸巾。我心里抱有老师会来找我的希望。或许我可以向他说明,我是一个没有成见的女人。可没有人过来。后来一个女同学说:“我要为非洲话题向你说声抱歉,谁会知道你长得像印度人种呢。”
尽管有时我真希望母亲到月亮上去,但我从没有偷过她的东西。我们的钱很少。虽说母亲从未提起,可我从哥哥那里知道,父亲尽管偶尔汇些钱来,但并非定期,也估计不到何时会寄钱过来。母亲是为老人做护理工作的,这无疑是最不适合她的职业。她参加过老人护理课程,因为这种培训所需时间很短。其实,凭她的聪明才智和敏捷的反应能力,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学会办公室里的所有事务性工作。可她依然用自己强壮的双手和一颗难以接近的心护理那些老年人,仿佛他们就是一根木头一样。
不仅是因为我们家穷,我才不偷母亲的东西。真正的原因是我怀着不幸而令人煎熬的热情爱她。我年龄越大,看得就越清楚:她是受伤者,而她的伤口是无法愈合的。我们俩各自为失去国王而伤心,却无法给彼此以帮助。其时我当然没有预料到,我同样对父亲的无情有多么失望。不过母亲尽管将我哥哥视为对丈夫的爱情补偿,但她似乎也有点依恋我了。尽管常常口出恶言,拒绝满足我的愿望和需求,但她还是坚决反对我弃学的打算。
“将来有一天你会感到可惜的,”这是她反对我厌学的主要理由。我们班上最漂亮的女孩想离校到一家卫生用品商店当学徒。我因而想到,那该有多棒呀,自己可以挣钱,不用经年累月地在空气浑浊的教室里受尽折磨。可我也不是很清楚,是否当学徒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学校是一个宁静的港湾。我没有过多违抗母亲就被说服继续上学了。今天想来,她之所以这么做,不仅是因为她的雄心壮志,也是她的爱心所致。我真要是赚钱的话,母亲的日子就会好过许多。这是我对她作出肯定评价的不多的几件事情之一。
顺便提一下,我到头来还是要感谢她给我的大象衣服。如果说在此之前我竭力避免穿这件驼毛披肩(唯有冰天雪地的冬天才迫使我穿上这件保暖毛衣),那么现在,即便在温暖的春日里,我也不会把它脱下身来。
贝克先生说,在操场上举办的时装秀中,尽管所有的夹克衫和大衣都很时髦,但他最喜欢的还是我那套灰色茶壶保暖装。
“你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玛雅。我和你完全一样,我讨厌和大家毫无二致。”
他以为我是自愿选择了那套大象装,但正因为如此,现在我的衣服却由于他的一句话而显得高贵起来。我感到高兴的是,他认为我们的内心具有共同点。我对他嫣然一笑。
我对爱情的知识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全部来自于书本: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我从中看到女人或者沉溺于爱情,或者爱上了一个不该爱上的人。可在我的梦里,我是一个名扬世界的歌唱家,而贝克先生能够和我交好,应该感激我才是。
当我最近发现这个勤勉然而带着小市民习气的老师和他老实巴交的妻子坐在我的大巴上时,我只能对我曾经的天真无邪摇摇头。顺便说一句,我完全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地将手伸进善良的贝克太太的手提包里,因为当她听从我的劝告交出善款之后,她的坤包始终敞开着没拉上。可塞萨尔在后视镜里看着我,不赞成地摇摇头。
我十六岁认识柯内丽娅的时候,已经成为过去的是贝克先生,而不是这件灰色的披肩。我慢慢喜欢上了它。母亲将那件红大衣送给我作为圣诞礼物,那是我一年前希望得到的,她现在买到了减价货。她大概认识到,到了第二年我会像大象一样到处乱跑,现在要提出一些优雅的要求了。可惜为时已晚。让我母亲十分痛苦的是,我从不穿红大衣,我想穿那件灰色衣服。
在我的大巴上,我不再以灰老鼠的形象,而是以乘务员的身份出现在游客面前,深绿色套装、白色衬衣和红色丝巾,全是意大利味儿的颜色。我的鞋子也是红色的。我必须反反复复地告诉游客我买那双时髦鞋子的鞋店的名字。另外我在坤包里放着一位会说德语的医生和一位牧师的地址,尽管后者迄今才用到过一次。他们起劲地记下了往德国打电话如何拨号、节假日注意事项和商店关门时间、邮资,就连我悄悄提示过的通常的小费标准他们也没有放过。
可是,在三小时的行程、参观和连续不断的拍照之后,我善意的劝告早被他们忘得精光,他们又一次惶恐不安地面对尾数很多零的里拉发呆。不过也有一些过分较真的人,拿出计算器来算个明白。我恰恰不会把这些人放在心上,因为他们对捐助缺乏任何自发行动,他们既不会幸灾乐祸,也不会流下热泪。
塞萨尔心情不错时,会直接开着大巴送我回家。这个当然是明令禁止的行为。起先他从没有跑过这种额外的路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慢慢消除了他的顾虑。他从不下车到粉红色别墅里喝上一杯浓咖啡,似乎担心罪恶说不定就躲藏在门后面呢。
我不用向他解释,我一个人住还是和别人一起住,是否还有亲戚朋友。我动荡不安的过去和他毫不相干。此外我相信,我的过去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和假设。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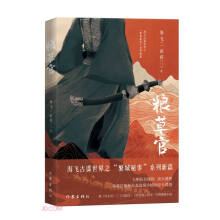



——英格丽特·诺尔
★这部作品让我看到了“闺蜜”这枚硬币的两面。
——中国悬疑教父蔡骏倾情推荐
★英格丽特·诺尔的小说以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大量的黑色幽默著称,那些看似完全正常的女人由于得不到人生的幸福而成了罪犯。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
★诺尔属于德国最好的小说家。
——德国《明镜》周刊
★叙述绝对逼真,充满黑色幽默。
——德国女性杂志《布丽吉特》
★诺尔是德国的派翠西亚·海史密斯。
——德国《萨尔茨堡新闻报》